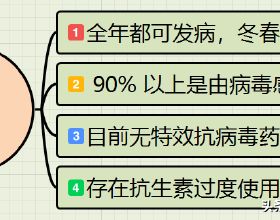草枯葉黃谷上場,陣陣秋風催人忙。正是根據地軍民緊張秋收的時候,日軍要對我晉察冀北嶽區進行“大掃蕩”的訊息傳來了。
這是一九四三年的八月末,我原在邊區黨校學習。有一天,區黨委組織部長林鐵同志找我去,一見面就說:“現在情況你清楚,決定調你去阜平縣擔任武裝部長,領導那裡的民兵堅持鬥爭,配合主力部隊作戰,粉碎敵人的‘大掃蕩’。”這是緊急的戰鬥任務,我當然馬上就答應了。
林部長又親切地囑咐說:“敵人這次‘掃蕩’可能更殘酷,時間也可能更長,你精神上要作足夠的準備。 阜平是你的家鄉,你在那裡群眾關係很好,遇事只要和群眾多商量,相信你一定會勝利完成任務的。”
遵照上級指示,我決心深入到基層民兵中去,和群眾在一起參加這次殘酷的反“掃蕩” 鬥爭。
九月中的一天下午,我到了城廂民兵中隊部。中隊長李尚忠見了面就拉住我說:“楊部長,去參加我們的演習吧,看看我們埋地雷的技術練得怎樣啦,給我們提提意見。”
我點頭說:“好!”
“楊生採!擂鼓集合!”
嗖!從屋裡蹦出來一個頭戴圓氈帽的小鬼,向我眨了眨那雙機靈的大眼,掄起纏著紅綢子的鼓錘,一邊敲一邊唱:
地雷是個大鐵瓜——咚咚咚
漫山遍野埋上它——咚咚咚
大吼一聲震天地——咚咚咚
鬼子腦袋開了花——咚咚咚
民兵們在鼓聲中從四面八方跑來。有的扛著步槍,有的則在身上斜挎著手提式或“馬來匣”;有的抱著地雷,有的還拿著鐵銑、鐵絲和褡褳等東西。
看著這個既威武、又勢派的場面,看著每個人雄赳赳氣昂昂的樣子,我在心裡不禁欽佩地說:“打了六年日本鬼子,這些鄉親們鍛鍊得勁頭越來越大了。”
跟著這百多人的隊伍,我們到了東門外的河灘裡。每次鬼子進城前,總是先在這裡會合,然後像把鉗子包抄阜平。
李尚忠出了演習的“課題”,分配了任務,劃分了佈雷區域。他先假設讓婦女自衛隊長帶老人小孩進山隱蔽;又讓遊擊小隊長侯起清帶人佔了玉皇廟制高點和把守城北要道,壓制敵人,掩護埋雷組和撤退的群眾;然後命令爆炸隊長張俊魯帶人奔向河灘,進行埋雷。
這些同志我很熟識,他們原來都是正經的莊稼漢,但現在一個個都成為足智多謀的指揮員了。
一切佈置停當,只聽張俊魯向隊員們喊道:“用連環雷,擺成梅花陣!”幾個隊員挖的挖,埋的埋,動作非常熟練。
張俊魯這個人,看去濃眉大眼,黑臉膛、絡腮鬍,一上戰場猛打猛衝,所以外號叫“猛張飛”。可是他埋起雷來卻非常心細精緻。隊員們埋好之後,他從褡褳裡掏出牛蹄子、羊蹄子,印上蹄印;又掏出小孩鞋底、婦女鞋底,印上鞋印;另外還撒上牲口糞,做得真是毫無痕跡。我看了不禁十分讚賞地說:“小夥子們真有兩下子,保險鬼子發覺不了!”我的話剛說完,誰知這個“猛張飛”還有絕技,只見他用黑帶子把眼睛矇住跑到城北一條小道上。
我想在這樣的小道上埋雷,要作好偽裝已很不簡單,再把眼睛矇住,更不容易!真是會者不難,張俊魯三下兩下很快地就摸著把雷埋好,而且偽裝得也很嚴密。他作完站起身來,喊了一聲:“請楊部長、李隊長檢查吧!”沒等我們說話,那些來參觀的婦女們早已鼓起掌來,嘰嘰喳喳的說開了:“咱們張飛,真是打仗像猛虎,埋雷像繡花!李尚忠這時也向我介紹說:“
張俊魯去年春天到邊區爆炸訓練班學習過,還聽過聶司令員講的地雷戰術課哩。”我接著說:“他學得很不壞,在反‘掃蕩’中一定會發揮很大的作用。”
埋雷進入城廂街道,由侯起清領著爆炸第二組表演。他們埋到大路兩旁,不埋在路中間;埋在水井周圍,不埋在打水的道上;埋在門檻裡邊,炕沿下面……我問侯起清:“這是為什麼?”他說:“這叫敵變我也變。鬼子挨一回炸,多一個心眼,咱給他們來個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出其不意,炸其不備。”
聽了侯起清的話,給了我很大啟發,從今天的演習中,看出他們在技術上是有很大提高,但雷在什麼地方埋,確實還應該多加研究。
地雷需要埋在什麼地方,這可以說是個戰術思想問題,要解決它也只有透過群眾來解決。
等演習完了之後,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當眾宣佈:“咱們再來開個諸葛亮會,俗話說:一人不如二人計,三人出個好主意。同志們今天埋雷埋得很好,但埋一顆就要有一顆的根據,要講出個道理來。大家現在都來獻獻計,看地雷都該在哪裡埋?誰的辦法高,主意強,咱們打起仗來就依誰的辦。”
第一個發言的是侯起清,他叭嗒著小菸袋鍋,慢條斯理地說:“報告!我說一條,大家評評行不?叫我說咱們在東門裡第一家門板底下埋一個!”
“為什麼?講講你的理由。”
“為什麼?你們想,咱先在街上挖條溝潑上水,鬼子大隊人馬進了城,路不好走,就得找個門板搭一下,他如果去摘門板,還不乾淨利索的炸倒他倆仨的?”
“好,侯起清同志講得有理,就照你說的辦!李尚忠同志一表揚,人群裡更加活躍起來!
緊接著就有人喊:“我提議——”隨著喊聲,又看見那纏著紅綢子的鼓錘,在我面前晃了一下,這是楊生採小鬼站起來了,他說:“我提議在咱們中隊部的鼓底下埋一個。鬼子看見鼓,一生氣,一腳……”
沒等小楊說完,旁邊有人問道:“你咋保證讓鬼子見了鼓,就準生氣?”
“這,這好辦!”小楊把紅綢子鼓錘在腦袋上輕輕敲著說:“他不惱,咱給加把火嘛!我已經編好了,要在鼓上寫:‘英雄鼓,英雄用,鬼子動,要狗命,旁邊再寫上‘民兵中隊部用’,看他們生氣不生氣?”
這時又有人給小楊開玩笑說:“計謀好是好,往後要是敲不上鼓,可不要再像過去哭鼻子。”
“只要炸死鬼子,不敲就不敲!”小楊紅著臉,口氣堅決地作了宣告。他這話,贏得全場一陣掌聲。
張俊魯還是抱著他那把銀光閃閃的鐵銑,看別人已提了不少,他才甕聲甕氣地說:“讓咱提上一條,把街上搭棚子的木杆,拆了綁成捆放在牆根下,給底下埋它幾顆。鬼子捱了炸,要抬傷兵沒擔架,他去拿杆子要抬人的時候,保險鬼子和杆子一齊飛起來。”
人們的發言,你一條,他一條,越來越多,像決了堤的河。這千百條河流,匯成了一個智慧浩瀚的海洋。
我最後向大家說:“咱們阜平在對敵鬥爭中曾得過‘鋼鐵模範縣’的紅旗。這次反‘掃蕩’中一定還要保持光榮,把咱們的地雷陣布好。鬼子他要來,頭先進,先炸掉他的頭,腳先進,先炸掉他的腳,來多少,炸多少,把咱們的血海仇炸平,把咱們的心頭恨炸消。”
日軍這次“大掃蕩”,出動了日偽軍四萬餘人,企圖徹底摧毀我晉察冀北嶽區根據地。阜平是北嶽區的中心,是邊區的首府;邊區領導機關一直在這一帶居住和活動,所以就成為敵人最主要的合擊目標。“掃蕩”一開始,日寇各路大軍的進攻矛頭,就都指向阜平而來。
雖然邊區的山川平原十分廣闊,“皇軍”的行動卻無自由。他們走大道,大道炸;走小道,小道也炸;莊稼地、渠道、沙灘等等,無處不炸;炸得鬼子不敢貿然前進,只好繞繞轉轉,走走停停,隊伍零零散散的沒個隊形,一個個耷拉著腦袋像送葬;慢得簡直就像烏龜爬。足足費了半個月,才爬到阜平城關附近。
這時,軍區主力部隊已插到外線打擊敵人去了。我們縣委和縣政府的幹部,也都分頭深入基層,帶領民兵武裝“區不離區、縣不離縣”的堅持內線對敵鬥爭。
我從那天參加城廂民兵演習之後,已清楚看到全縣各區村都有了一支組織堅強的武裝力量,這些力量也都有了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特別是他們都掌握了一套用地雷戰殺傷敵人的有力武器。我堅信依靠著這個人民的銅牆鐵壁,一定可以戰勝敵人的。
鬼子進阜平城的那天,我還是和城廂民兵在一起。那是十月二日的上午,城東玉皇廟頂上的“訊息樹”向西倒下,這是報告敵人從東邊來了。城裡的老鄉們,在自衛隊的掩護下,安全地轉移到大白山裡去了。
爆炸組按照演習過的方案布好了雷陣,我和李尚忠作了檢查,最後到離城一里多地的山頭上。我們要親眼看看鬼子如何走進民兵們為他佈置好的天羅地網。真是“種瓜得瓜,種豆收豆”:鬼子在我們根據地裡種滿了仇恨,他現在就要用頭顱和鮮血來加倍償還;民兵們在邊區的土地上種滿了地雷,我們馬上就看到它開的花結的果。
鬼子一到城門口,當然迎面會先看見張俊魯他們扎的那個草人,草人手裡舉著一塊大標語牌,牌上寫著:“城裡地雷五百三,看你小鬼哪裡鑽!”兩行紅字。這兩行字是給敵人的警告,也是給敵人精神上最強烈的打擊。
據說鬼子到草人跟前生氣地瞪了半天,也沒敢動它,怕它下面埋著地雷。因為他們在別處已吃過不少這樣的苦頭了。
前幾年反“掃蕩”中,敵人進村後我們在山上所聽到的,首先是殺豬宰羊、燒火做飯的聲音;而現在卻絕然不同。敵人硬著頭皮進了阜平城,不斷傳來的卻是雷聲隆隆的巨響。遠遠望去,城裡真是火光閃閃,煙塵滾滾。這每一個光閃,都會有鬼子的血肉橫飛,這每一個聲響,都會有鬼子的屍體倒地。高興得民兵們在山上止不住地連聲叫好。
天快中午時,侯起清帶領的遊擊小隊從穀子地裡鑽出去,在隔城不遠的地方抓來一名偽軍俘虜。聽俘虜講:鬼子進了阜平城,走路,腳底下的地雷炸了;挖窖,窖口裡的地雷炸了;推門,門框上吊的地雷炸了;抓雞,雞窠裡拴的地雷炸了。還有的鬼子到菜地裡伸手去拔蘿蔔,蘿蔔下面的地雷也爆炸了。
那俘虜還講鬼子在摘門板時和綁擔架時挨的地雷炸特別厲害。直炸得鬼子嚇破了膽,他們行不敢走路,住不敢進屋;好像他們的性命是個用細線吊起來的雞蛋,說不定哪會線斷蛋打,一命歸陰。
當人們正聚精會神地聽俘虜講鬼子挨炸的時候,忽然楊生採小鬼機警地喊道:
“別吵——別吵,你們聽,城裡有人敲鼓啦!”
大概小楊一直注意著他在大鼓下面埋的地雷,這時他一聽到鼓聲就特別留神。等大家急忙轉過身來,還沒有聽清楚鼓聲的方向,緊接著從城裡傳來一陣“轟壟轟滷的地雷爆炸響聲。這一下可把小楊樂壞了,他樂得在那裡一蹦幾尺高,嘴裡還不停地喊:
“這一炸是我的!這一炸是我的!”最後他還興致勃勃地向大家說:“同志們,我又編了一段,你們聽聽。
我的大鼓是英雄,開花爆炸顯威風,
鬼子敲響我的鼓,仰面朝天回東京。”
就這樣,敵人在阜平城裡一夜也沒有敢住,當天下午,就夾著尾巴溜走了。
鬼子逃出阜平城,但卻佔了城西城東的法華、王快等地方,還是要進行“清剿”。
李尚忠一見我就說:“楊部長,鬼子蹲在咱阜平不走,往後這仗怎麼打呢?”我回答說:“上級早指示過,敵人這次‘掃蕩’的時間會很長,你們千萬不能急躁輕敵。還要告訴大家,今後不是呼呼啦啦地埋一頓、炸一陣就算了;要想辦法對付鬼子的長期‘清剿’。”
“敵人到哪裡,地雷響到哪裡!”民兵們提出了新的戰鬥口號。各民兵中隊都加強了飛行爆炸組的活動。一旦發現敵情,就抓住敵人不放,把地雷埋到敵人前面去。
同時,還大力開展了“槍雷結合”的殺敵運動,就是遊擊組和爆炸組密切結合起來,用步槍和地雷協同殺傷敵人,互相牽制,互相配合,逼得敵人防不勝防。
這時,城廂民兵中隊就經常出發遠征。侯起清帶著遊擊組,跟著敵人繞轉轉;張俊魯帶著爆炸組,瞅空子就給敵人擺地雷陣,他們配合得非常靈活自如。
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們在槍雷結合的戰術中不斷出現新的創造,層出不窮,什麼“引誘爆炸”、“駐地封鎖”、 “迎頭爆炸”、 “尾追爆炸”等,在埋雷技術上也是花樣日益翻新,什麼“連環套”、“迷魂陣”、“梅花群”、“空中跳”,還有那“仙人脫衣”、“金蟬脫殼”等等,真是越來越加神妙。
有一次,李尚忠他們中隊打一小股敵人就是非常巧妙的:他們讓楊生採在山頭上指揮幾個人唱歌子,激怒得鬼子飛步來追;正好,侯起清埋伏在對面用步槍點名,山半腰張俊魯埋的“追命雷”也炸了,追上來的敵人就沒有跑回去幾個。
敵人也在煞費苦心地想辦法:抓幾隻羊在前邊替他們趟雷,但羊總得有人趕著,地雷炸了羊人也跑不脫;弄來探雷器讓工兵在前面掃雷,但民兵到處埋下些廢銅爛鐵片子,真假難分,倒連人和探雷器一塊給炸飛了。鬼子沒辦法,還是隻好用刺刀逼著偽軍在前面領路。
一天,侯起清忽然拿了個字條來遞給我說:“這是從路邊揀來的,你看可笑不可笑?”我接過一看,字條上寫著:
“民兵大叔,請高抬貴手給小侄們指條生路,炸鬼子儘管炸,千萬別炸我們,我們是被逼得無法才吃這碗飯的。”
很明顯,這是偽軍向民兵寫的哀告求饒書。說明我們的地雷,把鬼子和偽軍間的裂縫炸得更深了。縣委很重視這個問題,當即專門作了研究,向各村民兵佈置展開“攻心戰”;要把這個裂縫給他們炸得更寬更大。讓地雷和政治宣傳一齊爆炸,一齊開花。
民兵們馬上行動起來,埋上真雷再埋上假雷,然後寫上標語傳單警告偽軍,並規定暗號給偽軍指出路線。所以在各地的牆壁上,就出現了很多這樣的詩傳單:
要想過河先搭橋,要想成佛扔屠刀,
進了邊區別作孽,地雷饒你命一條!
只饒你們小命,不讓鬼子逃生。
倘不遵守規定,地雷決不留情!
此後,有些偽軍果然搜山領著鬼子繞圈;發現糧窖向鬼子作假報告;走路按照我們的暗號,指東不敢西。
十月底,我們接到這個訊息,說王快敵人槍斃了三名偽軍,罪名是懷疑他們勾通八路,證據是地雷為什麼不炸偽軍,單炸“皇軍”?不過,鬼子槍斃偽軍也是無濟於事的,就在他槍斃人的當天夜裡,有兩名偽軍帶了兩支三八槍,跑到四區,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向民兵投誠,還拿出民兵寫的標語,……
敵人為了維持運輸和準備逃走,在阜平城西八里的法華村修了個臨時飛機常日寇的矛律師團長還駐過這裡。民兵們當然不能讓這群強盜們安安生生地駐著,經常乘機襲擾敵人。
有一次,他們在夜間鑽進飛機場裡埋設了大量地雷,把第二天早上集合出操的鬼子炸倒了一大片。在執行這次任務中還有一段插曲,也是特有意思的:這天去埋雷是由中隊長李尚忠帶著,法華村的民兵也參加了。當他們摸到飛機場邊上時,心靈眼快的楊生採小鬼,忽然發現旁邊站著一個鬼子哨兵。
李尚忠機警地摸到跟前一看,卻原來是個頭戴鋼盔的橡皮人。楊生採把這橡皮人扛回來,逢人便說:“鬼子弄壞了我的牛皮鼓,我繳來了鬼子的橡皮人。這玩意也是個很好的宣傳工具哩!”他還就這事編了一段歌:
日本鬼子真稀鬆,
擺了個橡皮人當哨兵,
假哨兵擋不住真地雷,
“毛驢”(矛律)師團快送終。
由於邊區各地民兵爆炸運動的開展,對我外線出擊的主力部隊起了很大的配合作用;日寇所謂的“毀滅大掃蕩”,終於在我邊區軍民協力打擊之下被徹底粉碎了。
在追擊逃出邊區的敵人時,途中繳獲敵獨立第三旅團第六大隊代理大隊長菊池重雄的日記,他在日記裡寫道:“地雷戰使我將官精神上受威脅,使士兵成為殘廢。尤其是要搬運傷員,如果有五人受傷,那麼就有六十個士兵失去戰鬥力。”
他還寫道:“地雷效力很大,當遇到爆炸時,多數要拆骨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
從敵人口中,也足以看出我邊區地雷爆炸運動的成果了。
楊福隆(1913—1976),河北省阜平縣人。 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參加革命。參加過當地群眾的抗捐運動和砸鹽店鬥爭。 1937年後,歷任中共阜平區委委員、副書記、書記,縣委軍事部部長。 1941年後,歷任縣大隊政治委員,縣武裝部部長。 解放戰爭時期,任察北軍分割槽武裝部副部長,軍分割槽參謀長,副政治委員。 1949年任察哈爾省察南軍分割槽司令員。 1952年12月至1956年5月任河北省張家口軍分割槽司令員。 1957年6月至1965年4月任河北省石家莊軍分割槽司令員。 1965年4月至1970年12月任河北省軍區副參謀長。 1970年12月至1976年4月任河北省軍區副司令員。 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軍銜。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 1976年逝世,終年6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