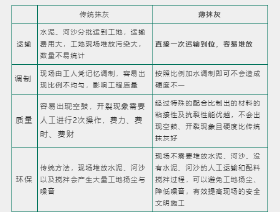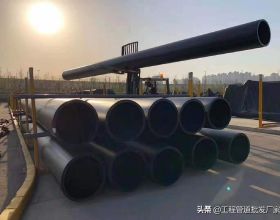中國文化是一條奔流不息的大江,而不是江邊的枯藤、老樹、昏鴉!坐在餘秋雨中國文化必修課的講堂上,品味中國文化的潤物無聲和磅礴生機。
“能登上金字塔的生物只有兩種:鷹和蝸牛”——古埃及諺語
請免我悲,免我苦,免我無枝可依,免我流離失所。——古埃及《亡靈書》
我們前面說了排第一名的巴比倫文化,今天該說說第二名埃及文化了。
我到埃及的時候,到處軍警如林、荷槍實彈。因為1997年11月,恐怖分子一下子殺害了64名外國遊客,埃及的旅遊業一敗塗地,直接威脅著整個國家的經濟。因為旅遊業在埃及國民經濟中佔據極大比例,其他經濟專案也依附著它。
請注意,所謂埃及的旅遊業,也就是憑藉著幾千年前埃及古文化,來吸引別人的眼光、來養活後代。人家拿得出手的就是古文化的遺蹟了,還不讓,那就什麼也拿不出來了。這真讓人同情。我想那些躲在雕塑裡、躺在陵墓裡邊的古代巨人,看到自己的後代,除了折騰自己之外已經無意謀生,受到了暴徒的阻攔也不知道如何對付,真不知會如何感嘆。
遺蹟是一種曾經有過的力量造型,卻不是現實的力量。當力量已經消失,遺蹟所負載的文化其實也不存在了。而且古代的力量越是巨大,這種失落也就更加讓人傷心。你看,金字塔的力量大到了難以想象,因此後代的微弱更不可容忍。
埃及文化的失落最讓人震撼的,是人種的失落、血緣的失落,也就是說建造金字塔、女王殿、帝王谷、太陽神廟的英才們,他們的後代都到哪裡去了?首都開羅和其他城市主要是阿拉伯人的世界,那是公元七世紀以後征服的結果;第二大城市亞歷山大有那麼多白人,是歐洲人征服的結果。
這些人走在金字塔下,其實也和我們一樣是外來人,只不過他們來得比我們早一點。我們對埃及的古代文化陌生,他們也陌生。
法老的後代
問題是,法老的後代究竟在何處?我們能找到他們嗎?這就是從血緣意義上尋找古代文化了,或者說從人類意義上尋找古代文化了。經過多方打聽,才知道在盧克索這座城市的尼羅河西岸,有一個法老村。據當地人類學家研究,那個村子裡邊的人在外貌身材上確實餘留著法老時代的諸多特徵,我和妻子趕了過去,果然看到了他們。
她們大多數人所從事的是手工刻石,許多古籍的修復與他們有關,這倒是不錯,修復到自己祖先的家產,像是後代。仔細一看,他們高高的個子,黝黑的臉,鼻子尖尖,滿臉滿手都是磨石的粉塵,活像一尊尊會動的的古代雕塑。
他們在漫長的歲月裡,把自己封存在緊靠撒哈拉大沙漠的尼羅河流域,拒絕遠地嫁娶,因此血緣穩定。但是,卻也正因為血緣太近,造成了體力和智力上的衰退。他們的生活非常簡樸,他們的思維非常單純。
突然,兩個都在地上的法老人,像是聽到有人在說我們是中國人,就抬起頭來朝我一笑,露出潔白的牙齒,用比較生硬的英語說:“你可以和我們一起照相。”我立即蹲在他們中間拍了照,他們又從地上撿起兩塊刻石的材料送給我,我想這應該付點錢,但他們拒絕了。
其中一位靦腆地說,如果有那種中國的小禮物——他指的是清涼油,在中國到處都有又極其便宜,但在他們那裡卻是寶貝。法老的後代不在乎錢,只在乎那股清涼的氣息。記得在開羅,一箇中國餐館老闆告訴我,他說清涼油在這兒很重要,而且他還送了我幾盒,我就順手從口袋裡掏出來給了法老人,他們深表感謝。走出屋外,我發現他們簡陋的住房的牆壁上,全都畫著他們去麥加朝聖的一路風景,可見法老的後代並沒有信奉法老的聖言。
我在前面講述文化的定義的時候,已經說得很清楚,文化的最終成果是集體人格,也就是人群。這也就是說,法老的文化遺產並不僅僅表現在那些巨石和殿闕,更重要的是血緣人群。在埃及,這個話題比較淒涼。
古埃及的無解
從法老村回來以後,我長時間地在太陽神廟的大樹下徘徊、思考,平心而論,埃及古文化的遺蹟實在太偉大了,在形態的壯觀上堪稱四大古文明之首。也許與撒哈拉大沙漠帶來的乾燥的氣候有關,沒有發生古蹟的黴變。我想,即使是中國最極端的國粹主義者到了埃及,也不能不稍稍謙虛一點。
在地理環境上,埃及文化也遠比巴比倫文化安全,大沙漠變成了一個大屏嶂,不容易遭到外來的侵略,而尼羅河又水勢平緩,與常常發生水災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很不一樣。這看來都是好條件,但是長久的安定使埃及文明越來越保守,越來越封閉,越來越不在乎與多方溝通,包括極權統治者和臣民的理性溝通。
這樣,埃及雖然可以集中驚人的力量營造金字塔這樣的雄偉建築,似乎也沒有發生過太多的衝突。因此,不必像巴比倫文化那樣早早地制定法典,因為法老的話就是法律。這一切加在一起,造成了埃及文化非常偉大,但又有非常多的不可理解性。而這種不可理解性,恰恰正是統治者為了維持神聖的光環刻意追求出來的。
我身邊太陽神廟那些廊柱上的象形文字,一直沒有什麼人能讀懂。當然也會有一些檔案和文稿,但是等到能夠寫、能夠讀的少數祭司一走,也就立刻變成了無解天書。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文化和它構成了巨大的區別。
中國文化歷來不追求故弄玄虛的神秘,所有的文字都是通識密碼,力求廣為傳播。連甲骨文即使在幾千年後發現時,也很快被基本讀懂,更不必說後來秦始皇在全國統一文字了。這種企圖與廣大臣民溝通的思維,使中國文化不可能枯萎在一個冷僻的高處。
正是在與古埃及文化的這種對比當中,我更深入地領悟了中國文化的這個優點。那番希望人們理解的誠懇,那番易解易讀的文字語言,成了中國文化貼地流傳、生生不息的基礎。更重要的是,與埃及文化現在已經很難找到血緣後代的特點相比,中國文化恰恰把祖先崇拜、傳宗接代,當作重要的精神價值。
兩大古文明的對比
與古埃及的社會結構不同,中國的姓氏宗親是很難動搖的社會基座。孔子甚至希望朝廷能夠從家庭當中學習一些東西,以家庭為範本。因此,中國的血緣文化永遠都在,處處都在,並由此形成了中國文化的生命後裔——那就是一大批不可能最終背棄中國文化的中國人。很多在世界各地生活的中國人,未必讀得懂咬文嚼字的那種小文化,但是卻都是整體意義上中國文化的生命體。
從開羅到盧克索,我一連穿行了七個農業省,在那麼長的路途上,我沒有看到一處表現出像中國農民一樣的勤奮。他們種的很粗疏、很隨意,收的也很粗疏、很隨意。在田頭勞動的人很少——幾乎看不到,但這又顯然不是因為實現了機械化。
這個對比又讓我想到了中國作為農業文明聚族而居、緊追時令的特點。這也就是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說的,叫做精耕細作型的農業生態。正是這種生態決定了多數中國人勤勞、刻苦、固執、順天、守序的共同習慣,這又與文化有關了。
在穿行尼羅河邊七個農業省的長途上,我又一直思考著埃及文化最終中斷,而且中斷得非常徹底的原因。我判斷一個長期穩定的集權王朝,必然會積累起龐大的世襲官僚集團。當這些世襲官僚集團分頭統治一段段尼羅河沿岸的時候,時間一長,又會形成一個個有錢有勢的地方政權。
這些地方政權遲早會與法老對抗,但是法老半神半人的神秘光環以及缺少溝通能力的傲慢,又必然無力處置地方政權。因此,分裂頻頻發生,外敵乘機而入,於是平靜的尼羅河終於見證了一次次激烈的戰爭。由於撒哈拉沙漠很難深入,因此尼羅河邊上的戰場往往縮得又緊又窄,其間的殘酷程度也就非比尋常了。
本來尼羅河邊上的歌聲,應該比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河邊的歌聲歡快一些,然而漸漸,憂傷的調子越來越重。我妻子多次在尼羅河邊的蘆葦叢中,聽到遠處傳來的男低音的宗教吟唱,總是覺得攝魂奪魄。
她說,這好像是人類遇到最大災難時的最後歌聲,卻怎麼還是那麼單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