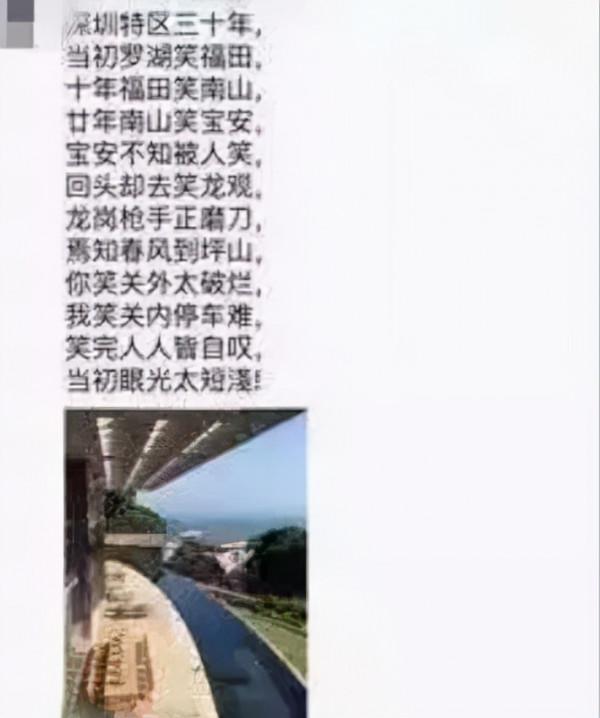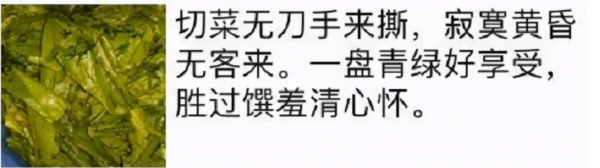孕育詩人的是歲月,而終結詩人的是青春。
小年輕註定醞釀不出什麼令人肝腸寸斷的七言絕句,但每一箇中年人都是潛在的詩人,只要給他們一個朋友圈,那麼他們就能寫詩。
年輕人經常能看見那些平凡而瑣碎的長輩在朋友圈寫詩。
詩中那些錯亂的意象與拗口難懂的生僻字,無不透出一股看破紅塵的無奈與悵然,這超凡脫俗的氣息與經常去KTV打屁股的乾爹顯得格格不入,且那淡泊名利的字句,似乎也與報名元宇宙講解課的舅舅毫無關聯。
你試圖用朋友圈分組來回避他們這表裡不一的情感釋放,但他們依然在每一次與交管所的領導喝得伶仃大醉後,開始在朋友圈寫詩。
沒有經歷過大風大浪的後輩,將永遠不會明白在朋友圈寫詩究竟意味著什麼。
只有當一個人見識過了車來車往,體會過了人情冷暖,眼睜睜看見樓下的一剪梅髮廊變為梅潤夜總會,又數十年如一日在富橋足浴與狂想舞廳宣洩了多餘的念想,並多次因為債務糾葛而收到法院傳票後,他才能夠真正拾起在朋友圈寫詩的渴望。
人這一輩子遲早會成為詩人,但這需要時間,跟文化程度沒關係。
你年輕氣盛時是洶湧的潮汐,總想著翻山越嶺,想著每天都要溫酒斬一個華雄,幻想在陌生的城市殺下一片自己的天空。你那時鮮衣怒馬,將史玉柱與黃光裕視作自己的前行方向,甚至對鋌而走險的車匪路霸心懷嚮往,你說物競天擇,勝者為王,然後十年不回家,一心要將自己的事業做大做強。那時候的你可不會寫詩。
只有在你英雄遲暮,漸生白髮,自覺打下的基業都是夢幻泡影,身上只剩下十八年的房貸,家裡只有搞大別人肚皮的敗家兒子時,你才會回望逝去的時光,開始不顧一切地寫詩。
中年人寫詩必須發表在朋友圈,正如無家可歸的流浪泰迪總是要在路燈旁留下自己的氣息。但中年人寫詩是被動的,是無意識的,就像風滾草隨風而動,就像去個廁所的時間,才買的小牛電瓶車就被城管拖走。
很多情況下,中年人並不知道自己在朋友圈留下了詩篇。他在切菜時寫詩,在開車時寫詩,也在多次聯絡舊情人無果之後寫詩。
彷彿詩原本就在那裡,他只是偶然尋得了挖掘詩歌的路徑而已,大概就跟星期三下午去茶樓打業務牌一樣簡單。
中年寫詩,有時是在失去一切之後。
我的生物老師,十年前下海入股了縣裡的私人專科醫院,專門替走投無路的少年與少女排憂解難,有時候也為傷風敗俗的邂逅處理後事。後來因為一場失敗的包皮手術吃了官司,賠了多年積蓄不說,老婆也因此跟他離婚,又禍不單行,離婚那天他家的狗還死了,就被人打死在破敗黑暗的樓道里。
自此之後他就開始寫詩,他寫梅花與溪流,寫濁酒與寒冬,數十年來,他從未像如今這樣熱衷於文藝創作,漂泊半生之後,他終於成為了一名詩人。
中年寫詩,有時也在報名桂林山水三日遊,或是去農家樂的小山坡上曬了太陽之後。
實際上,中年人很少寫有關於詠人的詩。他們記憶中的小紅與倩倩,其實都早已隨著前列腺的逐步腫大而消弭在熹微的晨光中,但那千百年不變的山水和朝陽卻依然與童年時期中的模樣別無二致。
到頭來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他們管這叫做入定。
可更多的時間裡,中年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寫詩。
“我第一次在朋友圈寫詩,是在四十歲生日的那一瞬間。”
我們公司樓下的保安對我講到。
“當我看見時鐘指向十二點鐘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必須開始做點什麼了,於是我開始寫詩,”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