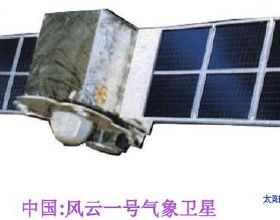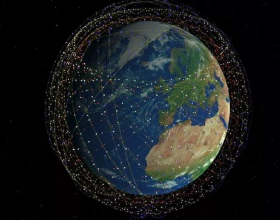許超雄(上海師範大學)
安史之亂後,江淮地區成為唐朝廷財賦的重心,“軍儲國計仰給江淮”,唐朝廷對江淮地區的管理也以保障財賦供應為首要目的。藩鎮體制下,江淮藩鎮被認為是財賦型,典型特點是駐兵少,軍事力量弱,對於江淮地區的探討也主要圍繞這個特點展開,側重於中央與地方關係。相比較而言,對於江淮地方社會的考察就顯得較為薄弱。蔡帆的《朝廷、藩鎮、土豪:唐後期江淮地域政治與社會秩序》則是打通了從朝廷到江淮地方基層社會多個層次,從帝國各權力結構考察了江淮地區的政治與社會秩序。
本書的三個關鍵詞“朝廷、藩鎮、土豪”精確概括了構成江淮政治社會秩序的幾個核心角色。按照作者的說法,本書是以“江淮藩鎮和土豪兩者為中心,以唐朝廷與兩者間的關係為重點展開”。本書共四個章節,第一章介紹了安史之亂後朝廷對江淮地區的藩鎮政策,第二章則討論江淮地區的土豪群體,第三、四章則考察了唐末江淮地區藩鎮與土豪權力交織,推動江淮地方權力結構更替的過程。

蔡帆著《朝廷、藩鎮、土豪:唐後期江淮地域政治與社會秩序》,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4月
江淮維穩機制下的“豪吏化”
安史之亂以後江淮地區的財源型格局經歷了唐廷多項政策及多年的經營、調適、改革才最終定型。由於藩鎮體制的建立,唐廷在京西北、河南河北、劍南地區無法獲得穩定的供賦,僅剩下江淮地區尚能提供穩定的財賦。在唐後期兩稅法體制下,稅賦分上供中央、留使、留州部分。從財賦上供的角度來看,由於養兵費用高,限制江淮兵力就能保證江淮地區“不會因藩鎮擁兵割據而拒不貢賦,或因軍費支出龐大而影響財賦上供”。於是,我們看到唐代後期江淮地區保持了最低限度的軍事力量。當發生叛亂時,江淮地區短時間內增加軍事力量,或調動中原藩鎮軍事力量參與平叛,但當叛亂平息則“賊平而罷”,使得江淮地區沒有長時間維持大規模的軍事力量。在江淮藩帥的選任上,採取選用與唐朝廷中央有密切關係者,“同時最好具備‘文武兼資’”。
作者將上述策略歸結為“江淮維穩機制”,這一機制的維繫有三個關鍵點:唐朝廷要在兵力上提供大規模支援;在軍費上提供保障;統兵將領的平穩置換。在這種思路指導下,經過德宗、憲宗改革後的江淮地區形成了兵力寡弱、上供豐贍、恭順文臣統鎮的特點。
“土豪”是本書的另一個重要研究物件。本書討論的南方土豪有蠻族土豪、宗族土豪、富民土豪。土豪代表了南方的地方勢力,漢魏六朝以來江淮地區的土豪經歷了從蠻族土豪到宗族土豪為主的脈絡發展,其中伴隨著南方蠻族“華夏化”的過程,土著蠻族向著宗族化轉變。當然,隨著大土地及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出現了由富農、商人等富民發展而來,影響地方社會的富民土豪。漢魏六朝以來,“真正控制南方地方鄉里社會的,乃是大大小小的土豪宗帥;其控制鄉里社會的權力,卻並非源於王朝國家的制度規定,而是建基於財富、武力之上的各種社會關係”,宗族土豪成為鄉里社會的實際組織者和控制者。這就難免與王朝國家發生衝突。隨著隋王朝統一南方,對南方的宗族土豪採取了離散宗族政策,尤其是江淮宗族土豪的反隋叛亂被平定後,隋王朝對宗族土豪進行了沉重打擊,從此宗族土豪開始走向消亡。當然,宗族土豪的消亡與其脆弱的內部文化凝聚有關,他們無法憑藉自身的文化優勢或宗族文化秩序復興宗族。
於是,富民土豪就成了江淮地方的主要力量。這種依靠土地的佔有、財富的積累為基礎而發展的力量,與南方的土地制度與商業發展密切聯絡。在唐代前期,均田制是否在南方得以推行還無法定論,但南方商品經濟的某些因素比之北方發達,唐長孺先生甚至有“南朝化”的論述,至少表明南方地區商品經濟的水平較高,這就給了富民土豪發展的沃土。
安史之亂後,隨著南方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土地兼併及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富民土豪進一步壯大。同時,唐朝廷對江淮地區的財賦需求增大,他們與國家力量產生的交集越來越多。作者將其稱之為“責任強化”,集中表現在稅賦職役的爭奪。這種“責任強化”六朝以來便已存在。唐代後期,“江淮富民土豪在承擔唐朝廷交付的職役時面臨破產甚至身死的風險”。肅代德之際的江淮叛亂即與此有關,富民與農民相結合,富民土豪首次以武裝集團的形式登上舞臺。與此同時,唐廷又利用富民土豪以強化江淮的鄉治,富民在縣鄉職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於是出現了縣鄉吏治的“豪吏化”,縣鄉胥吏層由土豪人群構成,土豪層與胥吏層的分野仍相對比較模糊。“王朝國家利用土豪層實現對鄉里社會控制的同時,土豪層也藉此對王朝國家的鄉里社會行政機構進行滲透”,“豪吏化”也是土豪對王朝國家行政機構進行反向滲透的產物。
土豪與唐末江淮割據
這種相互滲透的關係再輔之以“江淮維穩機制”,使得江淮地區保持了一個半世紀的穩定。到了唐末,江淮地區的政治穩定被打破,藩鎮與土豪層面的變動,迎來了江淮權力結構的改變。唐末的裘甫起義雖然在“江淮維穩機制”下得以平定,但隨著黃巢之亂破壞了這一機制維繫的關鍵因素,如唐廷的支援,北方軍事力量的參與,出於軍事需要,江淮地區迅速走上了軍事化。土團、鄉兵等江淮地區新興武裝力量在平叛過程中有了長足發展,這些勢力多是以土豪為核心的武裝集團,同時北方武人集團也構成了此後爭奪江淮的重要力量,當然還有黃巢降將勢力。各種勢力的交錯,構成唐末江淮新的權力結構。
比較典型且具有重要影響的,當數高駢的淮南鎮。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後,“淮南形成了軍府—高駢部隊、支州—降將勢力、基層—自衛武裝組成的頗具層次的軍政格局”。高駢利用唐朝廷授予的職權,對江淮的地區財政與軍政進行了地方化改造。首先,從財政來說,高駢兼有鹽鐵轉運使之職,改革鹽鐵轉運機構,其親信掌握了巡院執掌,侵奪了唐廷在江淮地區的利權,實現了淮南財政的地方化轉型。其次,高駢兼有諸道都統,具有墨敕授官的權力,這就為高駢招納黃巢降將、統領並吸納諸道軍隊,約束至支州將領提供了正當性和便利。
但高駢的淮南軍府源於朝廷所給予的正當性,當高駢忠於朝廷,與朝廷的立場相一致的時候,這種機制可以維持,因為這種機制維持需依賴於兩個重要條件:“一是唐朝廷及諸藩鎮在軍政運作上的保障;二是高駢與唐朝廷、諸藩鎮及依附他的將士在政治立場和利益上的一致。”高駢的軍隊中有部分源自高駢曾任職的西川及天平、昭義等鎮,他們名義上仍隸屬於原鎮,軍資錢糧仍由原鎮調撥,且其家屬還在原地鎮。當高駢與唐廷的矛盾激化,其諸道都統、鹽鐵轉運使等職被罷免後,維繫這些將領的兩個條件就不再存在。就淮南的支州而言,高駢在江淮支州安置了黃巢降將及江淮本地勢力,這些地方勢力多有不同程度上的自主性,高駢對屬州的控制也頗為勉強,隨著地方各勢力混戰,高駢逐漸無法控制支州。更為關鍵的是,淮南軍府內部矛盾重重,呂用之黨逐漸部分褫奪了高駢的軍政、財政大權,形成了高駢舊將與呂用之黨的矛盾、高駢與呂用之黨的矛盾。高駢也正是在內外矛盾中,死於軍亂。
順便一提,作者對高駢鎮撫江淮兩次出兵事件及對朝廷的離心事件進行了詳細考證,對高駢與唐朝廷間關係的變化具有新的推動。高駢任職淮南後,最初積極進剿黃巢軍隊,但高駢將領張璘兵敗後,高駢就消極應戰,導致黃巢軍隊順利透過江淮,一路北上。作者認為,張璘應該是高駢手下最具戰鬥力同時也是對黃巢軍隊最為熟悉的一支力量,張璘戰敗後,高駢恐怕難以短時間內組織起一支“中堅力量”抵禦黃巢。也就是說,高駢縱巢入淮,實際上是力不能制情況下的避戰自保策略。另一方面,高駢在黃巢北上後,曾兩次聲言出兵,作者亦有詳細考證,認為兩次出兵高駢並沒有北上之心,第一次或許有圖謀鄰鎮之嫌,第二次則是徐泗揚爭兵背景下,爭取朝廷支援和政治主動的一次政治作秀。但高駢在朝中的奧援宰相盧攜及宦官田令孜在政治鬥爭中失敗,加之高駢縱巢入淮,兩次出兵,引發了朝廷的猜忌,最終導致了高駢離心事件的發生。應該說,本書對高駢與朝廷關係分析,具有不少新的創見。
高駢的失敗,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朝廷對江淮支配的結束,江淮地區形成了以土豪為核心的割據局面。江淮地區普遍存在著臨時招募的“土團”,其雖有官方組織的統領,但更具民間性質。隨著江淮戰事的擴大,土團由“官籌官辦”變成了“官籌民辦”,土豪成為這一地方武裝力量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江淮地區的鄉里社會形成了普遍的土豪武裝力量。在唐朝廷的控制力下降後,他們紛紛奪取了地方的控制權,控制了道、州、縣、鄉各級。
不過,江淮內部不同區域的土豪力量對地方的控制又有所不同。作者分別對江淮各州割據勢力進行了統計性考察。總體而言,江淮地區的割據普遍以土豪武裝為主,但在州級層面,各鎮又有不同表現。淮南、浙西及鄂嶽等鎮,由於處於南北交接地帶,其州級割據多呈現出多樣化的傾向,主要有黃巢降將、江淮本地集團、北下軍人集團等勢力。而在浙東、宣歙、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則基本上由本地土豪割據,偶有零星外來軍人集團。其中宣歙在州以下呈現出細碎化的土豪割據,江西以本地土豪割據為主,實現了較大區域的跨州割據,湖南本地割據土豪的蠻族背景比較突出,福建則是建州土豪割據。
可以說,在唐末,江淮地區縣鄉社會基本上被土豪所控制,部分地區的土豪則開始佔據州一級。無論是本地勢力,還是外來的軍事力量,要想實現對江淮地區的控制,就不得不與土豪進行合作,“江淮割據政權建立的普遍基礎仍是土豪層”。不過,從江淮割據的情況看,處於南北交接的淮南、浙西及鄂嶽等鎮,浙東、宣歙等經濟較為發達地區,以及開發較晚的江西等地,具有不同性質的割據土豪。顯然,割據主體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淮區域內部的地緣政治地位、經濟開發程度、“華夏化”程度的不同。
如果我們從江淮割據的基礎來看,雖然最後形成了楊吳、馬楚、王閩、吳越等四大政權,但其割據形成的基礎是本地土豪,且除吳越是由本地土豪直接建立外,其他政權都是建立在與諸多縣鄉土豪合作的基礎上。這就意味著,江淮割據政權的權力基礎來源於地方,且零碎分佈的土豪力量不利於強大中央力量的形成。反之,北方州一級擁有強大的力量,權力較為集中。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何以南方勢力無法北進,實現全國的統一。
江淮地域政治與社會的視角切入
本書的論述主要從較為宏觀的角度,分析江淮地區的變動,但仍不缺案例的探討。如在第二章論述富民土豪與官方關係中,作者指出,“國家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土豪的地方資源網路來進行鹽茶等物資的流通,土豪富商與唐朝廷在官鹽上的合作可以看作土豪獻納自己的地方資源網路來獲取利潤和政治特權”,但由於土豪層為主體的鹽茶私販體系滲透進了地方政府,私販還形成了武裝力量,唐朝廷在打擊鹽茶私販中難以真正有效打壓。
宣州康全泰之亂的分析是透視土豪與政治及社會秩序的典型案例。作者從鄭燻《祭梓華府君神文》入手,考察了康全泰之亂中叛亂的土豪層與藩鎮之間的權力結托關係。由於藩帥鄭燻代表朝廷謀求上供的賦值,剝奪了土豪層的利益,打破了藩鎮與土豪的結托關係,本次叛亂實在是“藩帥與土豪層在對地方財富、地方秩序控制權的爭奪中產生的利益糾紛所致”。但該事件中,鄭燻又得到了宣歙當地土豪層的幫助,汪玕等土豪利用當地的資訊網路,參與了營救鄭燻的行動。作為回報,鄭燻又以官方身份祭祀梓華神,將叛亂平定歸結於梓華神的保佑,“汪玕等土豪透過主動抓住參與政治事件的機會,成功地使其構建的地方文化秩序受到了王朝國家的認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與王朝國家在文化秩序層面上的結合”。
本書邏輯緊密,章節內容層層推進,既有宏觀的分析,也有微觀的考察,同時文筆流暢,可讀性較強。就學術價值而言,本書從國家治理與基層社會角度,分析了唐代江淮地域政治與社會秩序的演變,構建了江淮區域發展的主要脈絡,對於推動唐代江淮區域史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誠如作者所說,“在研究唐後期的江淮地域政治與社會環境時,必須將對這兩股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力量的考察集合起來,才能得出江淮地域政治與社會變遷的全貌”,本書對江淮社會的論述貫徹了這條主線,生動地勾勒出了唐代後期江淮變遷的基本脈絡。
應該說,本書對江淮土豪演變的梳理是準確的,這種演變背後乃是江淮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縮影。不過,仍有部分地方需要注意,即土豪性質的重疊性,宗族土豪雖然退出了江淮地區的主導舞臺,但仍有可能存在宗族土豪兼富民土豪的情況。如本書第112頁引韓滉懲治豪吏中有“縣鄉豪吏,族系相依”的描述,具有宗族土豪的特點。此外,本書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淮南與浙江東西道,對於湖南等地區雖然在第四章有所分析,但仍顯薄弱。
當然,本書的結論多有對唐代江淮地域政治與社會秩序的宏觀性概括,更多的細節仍可以進一步展開。在本書基礎上,可以進行更多細節性的案例分析,以進一步深化本文的結論,同時對於江淮地區內部各藩鎮、各州的差異性,亦可以進一步深入。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