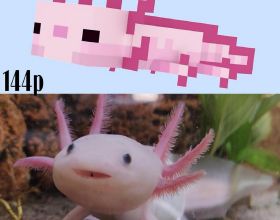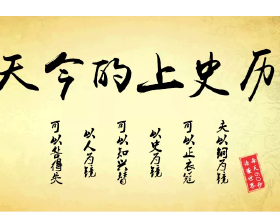趁在北京學習的機會,筆者約馮良聊天。知道我先要去中國美術館看展,她把碰面的地點定在附近的嘉德中心。馮良的先生翟躍飛是畫家,正好一起看拍賣場的比拼,隨後溜到錢糧衚衕西巷,在一家越南菜館午餐,邊吃邊聊,氣氛輕鬆。
我們這是第二次見面,頭一次竟是多年前的火把節時,她從北京回西昌省親。好在現在聯絡方便,她的文學創作、思想觀念、閱讀喜好,以及她編輯的好書,線上時我們討論的話題比較廣泛。
當天,我們談論最多的,顯然 是《西 南邊》。她的新作,也是她的心血之作。寫作時間長達 10年,“有點時間,就會坐到電腦那兒碼字”。完成的稿本40萬字,這個長度已經超過預期,“所以修改又用了兩年,付出的精力真不少”。
《西南邊》是一部厚重之書,後來得獎,是其文學價值的證明。
馮良的本職是編輯 ,2018年從中國藏學出版社副總編輯任上退休。編書以外,她把最多的時間用到文學寫作上,數十年樂此不疲。
《西南邊》寫出大涼山一個時代的蒼茫
2020年8月,馮良的長篇小說《西南邊》榮獲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此作在《收穫》2016秋冬卷推出即頗受關注,幾乎是第一時間,我郵購來先睹為快。我必須承認,一氣呵成的閱讀完全是被氣勢恢宏的時代力量和生龍活虎的人物命運所吸引。稍後,長江文藝出版社將她的這部新作納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7年中國文藝原創精品出版工程專案”正式出版。馮良寄來精裝書,還散發著油墨的清香,我竟讀出不一樣的味道,拿在手上閱讀書籍的感覺就是舒坦。
已經熟悉的人物,精彩的故事奇妙得像電影鏡頭一般,一幕幕連貫而出。三對不同民族的人物的婚姻,本身就蘊含“奇花異果”故事的元素,但絕不是獵奇;看似日常的生活切入大歷史的豐富細節,牽引外部世界與彝族社會、大涼山之間的互動與衝突,寫出了一個時代的蒼茫。西南邊的大涼山莽莽蒼蒼,20世紀50年代,當地一躍進入了現代社會這樣一種高階的文明形態,及至改革開放春風吹拂,半個世紀翻天覆地的變遷,是歷史波瀾壯闊的一頁頁。
小說得到的好評亦如潮水——
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這是一部具有史詩品格的小說,透過小說可以感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到底意味著什麼。對涼山來說,那就意味著現代性前所未有、大規模地在那裡降臨。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艱難地成為一個偉大的現代國家和現代民族。
《人民文學》雜誌主編施戰軍:《西南邊》是這幾年非常罕見的作品,文化感、藝術感、歷史感、價值守護感非常強,綜合起來看是極其優秀的傑作。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作品有一個很大特點,把細節寫得枝繁葉茂,對細節的把握充滿了生活氣息,特別是用豐富的細節構建了當代文學中的彝族社會形象,寫出了彝族人鮮明的典型形象,又寫出了彝族人的群像。
《光明日報》高階編輯彭程:標誌著作品辨識度的語言非常鮮明,形成了一種渾然天成的情調,與作者所要展現和描繪的地域生活內容很匹配,對於塑造人物形象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面對褒揚,馮良感慨良多。正如她在接受“駿馬獎”時的感言:“縱然時空相隔,涼山都不曾離開我哪怕須臾,她是我生命的緣起、情感的依託。歲月流不走的記憶、前行的腳步,那些深懷冷傲、倔強,卻掩不住奔放、幽默的族人,還有他們的人生,帶著大時代鉅變的深遠迴響,那激盪的、傳奇的、英勇的、赫赫聲名的、深情的,還有機智的,甚或狡黠的,何其珍貴,猶如珍珠。”
身居北京,西南邊的涼山,是馮良永遠的情感牽掛。
《彝娘漢老子》讓她初露才華
馮良1963年生於涼山州喜德縣。“17歲,我離開涼山老家,北上讀大學、生活、工作,凡40年。其間,行跡遠至西藏十餘載。”離開拉薩進京,到中國藏學出版社做編輯,直至從副總編輯任上退休。她簡要勾勒的人生軌跡,主要的“節點”都充滿細節。她的文學表達,有西藏題材的小說,還有更多關涉涼山“老家”的小說和散文。
2005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彝娘漢老子》是一本散文集。8篇散文所構成的,是涼山彝族心靈史的幾個片段。這些敘事性散文,每一篇都很長。敘事跌宕起伏,迂迴曲折,描述綿細婉轉,妙趣橫生。作家從容不迫地把握節奏與情緒,聯絡到後來的《西南邊》可以看出,《彝娘漢老子》是鋪墊是起跑是初露才華。
其中一篇《喜德縣》,有她的童年記憶——
我家住的那個宅子,哦,先要澄清一下,不是我們一家住的,我父親的單位,還有一部分職工都包羅在其中。這個宅子在縣城當時的鬧市區。門口有一條丁字形的街道,豎的那一條沿著一個山坡通向政府機關,橫的那一條平行去往市場。郵局呀新華書店什麼都挨在近旁吶。但是它們是用土夯成的,就像我們後院那兩排相向而立的土房子。
小時候我家住在當街的一間裡,地板牆板都是用一尺多寬二十公分厚的木板拼就的。廚房裡還有一架沒有護欄的樓梯可以上到屋頂低低的樓上去。那上面盡是交錯的橫樑和椽子。我哥哥住在上面,也用來放一應雜物。
以正統的歷史觀來分類的話,我家那個處在雲貴高原深山裡的縣只是個化外之地。它和文字史的瓜葛在古時候是由所謂的西南絲綢大道聯絡起來的。說是大道,在我們那裡卻是蜿蜒在山中的羊腸小路。和這條小路最先發生關係的一個歷史名人是西漢時的司馬相如,再一個就是三國時詭計多端的諸葛孔明瞭。
文學評論家張莉長期關注中國女性作家的文學寫作,她在評論馮良作品時談到一個觀點,彝族人對於彝族文化和彝族生活的熟悉是作者的寶庫。馮良時常提及涼山對於她文學創作的意義,用得較多的詞包括“養分”“觸動”“激勵”等等,她坦誠地說,她是在回望、懷想中,展開文學的翅膀的。
馮良進一步分析:“涼山解放,涼山與內地、彝族與漢族等民族密切接觸、互動,涼山彝族社會更加密切地融入國家政治生活,個人的命運、民族的前途因此更加生機勃勃。這也是成長於這光榮年代,包括我在內的邊地人的幸運!”
她找到的,是歷史表述的新可能。
《西藏物語》愛上文學的發軔之作
許多讀者把《西南邊》當歷史看,當民俗看,因為它融進了太多大涼山的歷史,太多彝族特質的東西。
許多讀者喜歡《彝娘漢老子》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細膩,將自己融入故事之中,用帶有濃厚四川方言和彝族特有的語言表達方式,娓娓動聽地講述陌生而新穎的故事。
但西藏時光,才是馮良文學創作的發軔。
一幫詩人、作家、畫家,端著茶杯、拎著酒瓶、曬著太陽,探討的理想話題是文學與藝術。以馬麗華、吳雨初為代表的詩人群,馬原、扎西達娃、劉偉、金志國等作家群,韓書力、裴莊欣、翟躍飛等畫家群,在那個激情燃燒的“1980年代”,成為中國文壇和畫壇耀眼的隊伍。如同馬原的名言“西藏把我點燃”,年齡小一些的馮良也開始提筆寫作,愛上文學。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這裡相遇、相知、相愛、相前行的故事打動了她。《西藏物語》講述的就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包括各行各業的進藏人員在西藏工作、生活的故事。1997年,小說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馮良在拉薩期間的中短篇小說結集為《情緒》。包括她的《西藏物語》和另一部長篇《秦娥》,她講的故事,籠罩在拉薩的某種特定氛圍中:頎長的巷子裡,陽光吞噬了所有的陰影,赤裸裸的顯露,因為什麼都不發生,生出的某種閒蕩,烘托了神秘。馮良的好友、作家皮皮點評說:“小說中鮮有人生指南解惑之類的說教,筆墨都集中在氛圍和敘述上。”皮皮寫道,“馮良在小說的敘述中,總能創造出一種慵懶的氛圍,對其所描繪的一切,她保持一定的距離,不是居高臨下的,也不是身心投入的,而是介於兩者之間。這般拿捏馮良運用得十分到位,作為一個另有職業的作家,馮良保持著自己的小說特色,靠的也許是骨子裡的這股勁兒。”
走出大涼山,馮良擁有了更廣闊的視野。她對彝族人在國家現代化程序中的觀察與書寫,不單是文學性的,還擁有社會學人類學的深刻內涵。這樣的文學某種程度上具有了世界性意義。
如今的馮良,可以說是涼山成就的一位優秀作家了。這塊蒼茫的高原,賦予了她創作的激情,血脈與心靈所在,她徜徉山川江河,揮灑書寫大時代的深刻迴響。
圖/何萬敏
來源:華西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