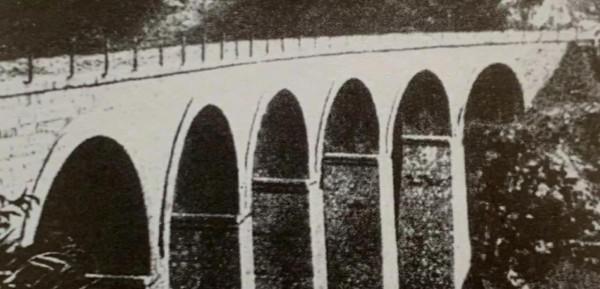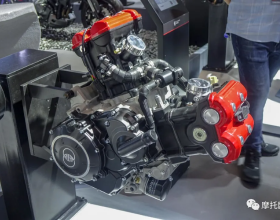1945年3月的某一天,駐守在中越邊境防線上的滇軍第60軍陣前;來了一群衣裳不整計程車兵,觀察之下是一群“畫風”迥異於日軍的隊伍,走近一看是一群白人士兵,其中摻雜著一群越南人,法語、越語聲刮噪著滇軍守軍的耳膜。
在軍官的介紹和帶領下,這群衣帶不整的哥們順利通過了滇軍防區,進入雲南、進入了崇山峻嶺的紅河,開啟了他們的滇南之旅。從這群哥們眼神中可看出他們的喜悅之情,莫非受了小日本的欺負?如今到了幸福彼岸,所以高興。
這是一群駐中南半島的法國殖民軍,小日本稱中南半島為“印度支那”,土著自然成了“支那人”,這不是個什麼好詞好稱謂,如同咱們稱小日本“倭”一樣。
當時,法國與小日本的關係比翻書還快,說實在的小日本還真不把它當盆友看。二戰前,法日也不是好哥們。特別是“黑船事件”後老法甚至還夥同其他列強欺負過小日本;1940年法帝戰敗投降後成立的“維希政權”,成了日本的盆友,成了“軸心國”的合作伙伴。共同簽訂了《共同防禦協定》,兩個同床異夢的合作伙伴,為了“軸心國”的共同利益手牽手走到了一起,手攜手共同管理中南半島一切事務。日軍不費一槍一彈便成法屬印度支那的主人,而且是真正的主人,老法倒成了打工的,但表面還是維護著兩國的外在聲譽,是鐵兄弟,老法還得面戴微笑,默默接受這種關係。
於是從1940年9月至1945年3月,在印度支那(中南半島)呈現出日帝法帝兩帝雙頭統治的局面。對中南半島而言,或周邊國家而言那就更慘了,面對的是兩隻“惡狼”,形勢更加嚴峻。法日狼狽為奸,助紂為虐是常有之事。
本來日軍打算和法弟聯合北上,一路向北,進攻國民政府的後花園~雲南,再一鼓作氣拿下山城。理想是豐滿的,曾幾次在夢中笑醒,夢醒之時一看這法弟蔫不拉幾的,不是那塊料,自己單幹,又逢老對手60軍鎮守中越邊境。在臺爾莊又領教過60軍的厲害,“猛烈衝鋒,實為罕見”,日軍編出了:頭頂滇軍,手捧中央軍,腳踏東北軍的順口溜。60軍一戰成名被日軍稱為“蠻子兵”,若小兒夜啼、喊之“蠻子”即靜矣,日軍聞之心驚、見之膽寒,現在又是家鄉兵守家鄉,幾無勝算、惹不起,咱就劍走偏鋒從南亞次大陸進攻吧!遠是遠了點,但總比無戰打要好一點,所以對侵略成性的人來講,只要能侵略,何管“蜀道難”;遂有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的“遠征軍”。
變化卻來到很快,到1944年,法國“抵抗組織”在戴高樂的領導下,在盟軍的幫助下,解放了法蘭西這隻高盧“雞”,又成了雄雞,成立了新的國家政權。原駐印度支那總督讓.德古和殖民軍司令,採取觀望態度,與新政府暗通款曲,對日軍採取了“非暴力”不合作態度,能拖的一定拖,不能拖的就磨洋工。陽一套、陰一套,引發日軍的不滿。
1944年10月,民國政府與戴高樂的自由法國政府恢復了外交關係。讓駐印度支那的法國殖民軍看到了希望,準備倒戈反日。
1945年初,日軍在菲律賓戰事非常不利,擔心法國殖民軍協助美、中兩軍進入支那,來個背後一刀,又發現殖民軍軍官向盟軍提供情報,為防腹背受敵,日軍決心拆除這顆定時炸彈,毒瘤先去,不做不休,決心已定,等的就是時機,找個藉口,對日軍而言如同囊中取物。大家知道的盧溝橋。
3月9日,下午19點,華燈初上時,日本大使松本在找不出幸福的理由之下,正式向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讓.德古遞交了一份最後宣告(即通牒),套路是相似的,不答應就動手,如珍珠港時的萊西。要求:法國駐印度支那的所有武裝力量接受大日本帝國的指揮;各鐵路線和海上及內河運輸線和國內外交通線,必須置於日軍的直接管理之下。石要過刀,茅要過火,人要換種;此時日軍倒不給你含糊了。同時嚴令殖民總督必須在兩小時內答覆,時間異常的苛刻,這麼大的事就兩個小時,不是整人是什麼?兩個小時考試都不夠。而且答案只有兩個選項:是和否;還是隻能打勾的題,難呀,頭大了。自己養的兒子交給別人指揮,誰都不會答應,所以德古要求延期再議,日方認為這是駁回了通牒,不識時務,給梯子不下。21時20分(多給了20分鐘,還是給機會的),日軍下令佔領西貢(今胡志明市,曾經的越南首都)的所有殖民軍民辦公地,並逮捕在西貢的所有殖民軍官員。法國殖民軍除了在河內、諒山、河陽等地有一些零星抵抗外,到10日止大多數法軍成了俘虜。那時法國殖民軍在越人數有1.7萬人左右(白人),日軍達6.5萬人,碾壓式的存在。這些殖民軍看著厲害,在日軍眼裡只是把鈍刀。
然而,在寮國北部及越南西北的殘餘殖民軍在日軍追擊下,用生命在競速,沿中方西南邊境潰散,生命自由天定,大部退入雲南境內,在諒山的殖民軍退入廣西十萬大山之中。這一路向北,卻是那樣的真真切切,成了他們生命祈求的地方,此刻是真情的嚮往。
在“三九”政變(日軍稱為“明號作戰”這個更確切)中,被法國殖民軍裹脅而來的幾萬法國外籍軍團和安南籍紅帶兵,紛紛瓦解。“互毆”結果是“體虛”的法國籍官兵被斃1662人,餘下的除潰逃外,官員進入牢房(一時人滿),一般工作人員留下為日軍服務,有時做個普通人也不錯。再說那些潰逃的成了:捱打不還手,滇南走一走。也算逃過一劫,搖身一變由軸心國變成了同盟國;享受“地主”盧漢同志給予的:同盟軍般的待遇。吃喝用度全由雲南承包了。
據說在駐滇期間,法國殖民軍與當地居民打成一片,有了感情。餘不敢苟同,說好者說壞者,是立於自身的需要而已。但可肯定在二戰中這些殖民軍是幸運的,剛開戰就投降加入了軸心國,戰爭結束前又成了同盟軍,可說在戰爭中兩面吃糖,很是得利,很少遭罪。
3月11日,日軍扶持阮朝末代皇帝保大帝上臺,成立“越南帝國”。4月17日,由陳仲金出任越南政府總理,由日軍操縱,提線木偶形成。日本正式取代法國,對印度支那進行殖民統治,印度支那開姓“”。這個操作到今天都存在,只是花樣翻新而已,是強者(有個國家)最喜歡玩的遊戲。
法國人對於雲南人來說是非常熟悉的,那時的昆明多有法式建築,即所謂的“法國黃”。火車站一律是這個色調,世家大院、軍閥毫宅都是,慨無例外。大的工程譬如:滇越鐵路、個碧石鐵路、昆明第一個自來水廠、照明公司…都有法國人的身影,這些總是伴隨著譭譽參半的評價。
那時軍閥世家都喜歡讓兒女去法國留學,譬如唐會澤的姨侄女施莉俠,還成了雲南第一個留法女生,據云在法國時還與周公成了勤工儉學的同學,或者認識;龍志舟的大公子繩武和三公子繩曾都畢業於法國西爾斯軍校(世界三大軍校);大數學家的女兒成了新中國第一個留法女生。
1964年1月27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法國和我們正式建交。法國是西方陣營裡第一個和我們建交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啟了中法友誼的旅程。
今天的草壩人或石屏人絕大多數都不知道曾經有一支殖民軍來過,偶爾知道的也是幾個愛好歷史的傢伙,是從故紙堆中零星扒出的。那時,蒙自及滇越鐵路、個碧石鐵路沿線上多有這些“老洋眯”。在開遠“解化廠”過去還有兩百多座近三百座的白人墳冢,據云是修鐵路的法國工人和少部分殖民軍墳冢,成了異國魂,現已無存,只是“曾經”有過,即“洋人墳”。那時石屏也有過,不多二、三十人,這個是修鐵路的,當時他們住在大瑞城(大水城)的“海潮寺”,現在已蕩然無存矣,不存於史,存於口傳。海潮寺,傳為當年觀世音觀海聽濤得道的典故,當地人故名之。餘生晚矣,此乃前輩口傳而已,時前輩們曾在滇越、個碧石鐵路和60軍及第14航空隊工作服務過,閒聊之間略知一二。
滇越鐵路,後為中越兩國人民的連心路,友誼路。成了雲南十八怪之一“火車不通國內通國外”“火車沒有汽車快”的來源處;此鐵路為抗日、抗法、抗美作了巨大貢獻,意義非凡。
其實在“三九”政變前法國與中方也有聯絡,政變後更是熱絡起來,法國要求中方給這支敗退的殖民軍“給予兄弟般的款待”。這個我們向來如此,量中華之物力熱情款待是我們的傳統,大明時的厚往薄來,農村中的省嘴待客,是一定會照顧好盆友客人的。據說同意了法方的要求,還讓不解武裝進入國境。殖民軍所經路途有專人接待安排,讓法軍省心不少。這些殖民軍算是被國軍收編了,隸屬於陸軍總司令部指揮,被演繹成了常凱申的“法國軍團”。
到了地方,實際是由盧漢第一集團(方面)軍負責,凱申也是責成盧漢負責這臺事的,而且是全權負責,盧漢轄60軍和54軍兩個軍。60軍軍部在蒙自新安所,軍長安恩溥(鎮雄人)。安恩溥任軍長期間抽調士兵到草壩“屯墾”,在開遠廣植木棉,種甘蔗、辦了撥溪糖廠,還辦了戰地服務團發展經濟,改善官兵生活,草壩成了60軍的“南泥灣”。殖民軍入滇後被安置在了草壩,受60軍節制,時任60軍軍長為萬保邦(屏邊人),安軍長於43年底離職,萬升軍長。這些殖民軍倒是成了60軍手下的白人士兵,不敢興風作浪的。
這些殖民軍在蒙自過的很是滋潤,但總不能白吃白喝不幹活,出點工也是應該滴。1945年7月,有任務了,為迫使日軍早日投降,第60軍搞了一次越境襲擊。由182師組建一個加強營,師部又組建一個工兵加強排共同作戰;嚮導是有了,現成的,那些殖民軍不就是當地的“老地主”嗎?能文能武,相當合格,OK,就是他們,挑選了幾個中意的配合行動。就是現在的特種部隊了,那時叫“別動隊”意思是去了別回來,大家都懂的,對於軍人來說,最高榮譽就是戰死沙場為國捐軀,勳章就是馬革裹屍,道道傷痕。別動隊就是“敢死隊”,敢於犧牲,敢於擔當。
7月初的某一天,別動隊從芷村出發,夜幕之下秘密向中越邊境挺進。時值雨節,細雨濛濛,更增加了它的神密,戰士們鬥志昂揚,毅志堅定,跋山涉水到了南屏,稍微休整,檢查武器,趁著夜色泅過紅河。千百年來,中越兩國只隔著這淺淺的河,中越人民共浴一河,親如兄弟。夜色之中別動隊迅速潛入越南者蘭附近大山中,佔領有利地勢準備強攻壩灑,天降神兵,日軍慌了神,連忙扔了重灌武器,輕裝向老街逃去。日軍眼看緊追不捨的國軍,又退到府留,在越偽軍的友好支援下,日偽兩軍憑藉府留一帶堅固的工事及險要地形,負隅頑抗,雙方激戰四小時,國軍殲滅日軍幾十名,斃其一小隊長,這股小日軍見勢不妙,撒開丫子、乘車而遁。國軍經安沛、越池,抵達昭陽,才停止追擊,凱旋而還。
以上是法國殖民軍在雲南的一些情況。他們是徒步開啟這“茶馬之旅”,沒坐滇越火車,沒有坐船而是沿紅河而上。那時這一帶制空權還在日軍手裡,徒步是最安全的旅行。
其中,一支殖民軍是由紅河河谷左岸一直順江而上,到達紅河州的石屏,在石屏稍著休整後又乘坐個碧石火車到達蒙自壩草與先期到達的殖民軍匯合,圓滿收關。
這一支殖民軍最早是3月中旬開始由越南入境河口。最後一批殖民軍接到的命令是由紅河河谷順江而上,沿途彙集從金平、元綠等邊境潰入的殖民軍,最遠一支是從寮國朗勃拉邦入境,經景洪入思茅(今普洱),部分過元綠到南沙、紅河迤薩(原為石屏)與到石屏的殖民軍最終匯合。
當時紅河州人走西頭謀生大多數經今紅河縣,下元江而去。一部可從元陽到綠春,就到普洱的墨江了,走西頭出國是比較短的線路。
當時石屏人也是過小河底江(紅河支流)上的“百年鐵索橋”西行過元江的窪垤(原為石屏)向下走到普洱、景洪即為“走西頭”了。石屏人有“窮走夷方,急走廠”之說,夷方指“西頭”就是經商去;走廠就是到箇舊挖礦去,這個暴富的土豪多,改革開放後更是造就了許多的“土豪”階級。“走西頭”即石屏馬幫(商幫)進行磨黑鍋底鹽(井鹽)易武茶葉的販賣,即現如今的“茶馬古道”(南方絲綢之路),茶馬古道很熱門的,有關茶馬古道的延伸很多,什麼“茶馬花街”“花街茶馬”“茶馬巷”…。去老廠(箇舊)重重辛勞,走西頭辛勞重重。人生的旅途就是一部奮鬥史,在茶馬古道上辛苦掙扎,抒寫了石屏商幫的發家史,現在應稱為“致富經”。
從寮國北上的法國殖民軍大概就是走這兩條線路,在迤薩匯合後過小河底鐵索橋進入石屏。有人會問這些地方那時瘴氣瘧疾肆虐,殖民軍安能無事?真的無事,他們早十八年就習慣了這種氣候環境。
到石屏的殖民軍從茨壩頭門洞進入縣立中學,可看到當時地標建築“企鶴樓”,樓下即為“噴珠泉”為當地一景,還上過央視。那時接待大規模人員一般都是學校或廟宇(現在好像也是),殖民軍在此清點人員,檢查裝備,補充補給;短暫休整後,再出發。經石屏縣城寶雲鎮(今異龍鎮)今之珠泉街,當時還有圍觀的群眾和小孩,殖民軍從小巷進入石屏火車站,是個碧石鐵路上的一等站。這是最後一批抵達草壩安置地的殖民軍。
這條鐵路叫“個碧石”鐵路,全長177千米,沿途有23座法式建築,從石屏到草壩(蒙自)有132千米,是當時唯一軌距僅60釐米的寸軌鐵路。
為什麼要修這條個碧石鐵路呢?首先是滇越鐵路的通車,給鐵路沿線帶來了效益,大宗物資透過鐵路可出口海外。蒙自正因有了滇越鐵路,遂有了跨越式的發展,那時在蒙自的外國人多達21個國家,雲南第一家。有效益就有動力,給紅河州人帶來了希望,山的那一邊絕對是大海。
清末民初,箇舊礦山人員猛增,開採面積成倍擴大,大錫出口幾何遞增。在到箇舊挖礦去的召喚下,許多周邊縣份的勞苦大眾懷揣著夢想,奔向這個有“礦”的地方,箇舊成了他們的詩和遠方,去實現自己的“致富夢”。那時出口大錫最經濟的就是水路,從箇舊蠻耗碼船運到越南海防,再到香港,但這條水路用時甚長,需七、八天,若從蒙自出發一天就到,節約了成本,又變捷,唯快不破,“時間就是生命,效益就是金錢”。
迫切需要建一條從箇舊到蒙自的鐵路,第一段“個碧”鐵路橫空出世。由於山高路險,山闊溝深,決定修一條寸軌鐵路,當地稱之曰:小火車。50歲以上的人應該坐過這小火車。“個碧石”鐵路也是一路三建。
“個碧”鐵路,1912年3月開始有動議,1915年動工;到1921年11月9日通車,這段鐵路的設計者是法國工程師尼復禮士,一看這名字就是個講禮貌的紳士。家裡有礦,通車邁小康也快。
雞街到臨安(建水)“雞臨”段,於1918年動工,1928年10月通車。這段鐵路設計工程師是福建人薩少銘,他力排眾議,使用寸軌的機車,卻打下了米軌的路基、橋樑和隧道,一但將來有變就有機會改成米軌與滇越鐵路連成一片;事實證明這是遠見卓識,高瞻遠矚的妙招。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從碧色寨到石屏全線改為米軌,只有個碧段保留了寸軌鐵路,在雞街要換成小火車進箇舊。現在看寸軌只有到箇舊了,當然遺留下的,不一定你能看到。
臨屏段於1929年動工,工程設計師是浙江人吳澄還和李慶榮。1936年10月10日國慶日通車,也標誌著耗時21年零5個月的“個碧石”鐵路全線通車。一條鐵路至少創了三個第一:第一條(唯一)的寸軌鐵路,第一全國民營鐵,耗時最長的鐵路。
這是條黃金鐵路,不知賺了多少¥,省府三番五次要收歸國有(省有),逼地方就範,因為有錢或善使錢、善公關都沒有收成。這些現在都是曾經的輝煌了,該謝幕的自然要謝幕,一切都淹沒於這崇山峻嶺之中;正如從蠻耗到海防的那條黃金水道。正是:我輕輕的來,正如我輕輕的走,不帶走一絲的白雲。下一個“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誰也說不準。但你存在,我深深的腦海裡。
1936年10月10日這一天是個大喜的日子,機車的轟鳴聲和人們的歡呼聲響徹了石屏寶雲鎮,歡笑聲在乾陽山異龍湖上久久盤旋。通車的主會場設在了石屏,龍志舟小姨妹顧映芬代表省府致詞,法國領事講話,駐滇外國領事列席慶典。縣府還特意搭起了四柱三門的牌坊,扎滿了柏枝和鮮花。縣立中學、文廟、玉屏書院、諸天寺擺滿了宴席,隨到隨吃,從白天到晚上,吃個“螞蟻上樹”。顧映芬還帶來了體操表演隊,還有籃球賽。“個碧石鐵路公司”正式掛牌,先前為“個碧鐵路公司”後改為“個碧臨屏鐵路公司”。今夜無眠,整個異龍湖都閃耀。
這群殖民軍是分別從那發、金平、猛平、卡房、龍膊、河口、紅河等地匯合,在石屏集中,一起乘火車到了蒙自草壩,他們看到了原生態的自然風光,並開啟了半年多管吃管喝又安全的生活,草壩倒成了殖民軍鋪滿童話的地方,吃著紅河州的美食,吃起來嘎嘣脆,連騾馬都嘴饞;告別了昨天的無奈和苦澀,一切傷痛已被時間擠走,留下的是回憶,昨天已走,敞開胸懷懷抱今天。1946年1月27日,這群5363人的“孤兒”,其中白人士兵2140人,殖民地土著士兵3223人。乘坐滇越鐵路返回“家鄉”,其中許多殖民軍的最後歸宿便是~奠邊府。但1月27日,卻永遠銘記在了中法兩國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