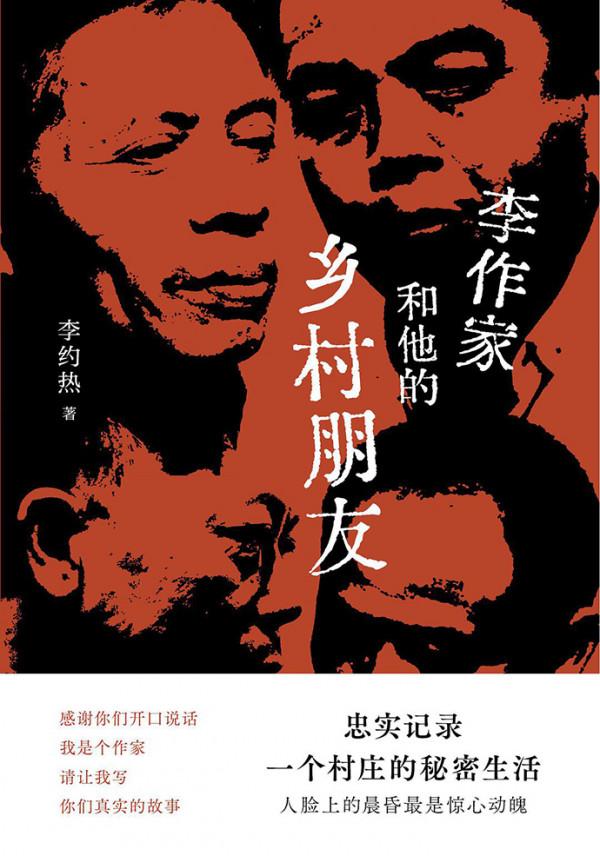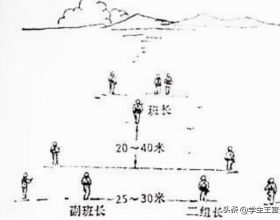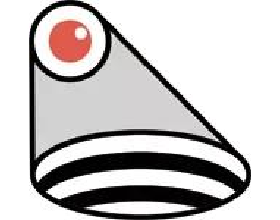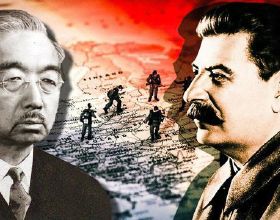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實習生 鄧倩倩
作家、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阿來有著二十年的文學編輯生涯,地方文學刊物《草地》、單期最高發行量達40萬份的《科幻世界》都曾留下他的足跡。對於“什麼樣的文學刊物是好刊物”“什麼樣的文學編輯是好編輯”,阿來有著深深的體會。在他看來,一個刊物的思想與內容表面上僅與文學有關,實際上也與當下的社會程序、現實生活密不可分。
12月7日,由四川省作家協會、《四川文學》雜誌社、四川省文學期刊聯盟主辦的第四屆全國文學名刊專家論壇暨2021年四川省文學期刊聯盟年會在成都舉行。
在會上,阿來提到:“前十幾年,四川人反省自己過於保守、不夠開放,老用到一個詞——‘盆地意識’。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這個概念深受《青年作家》在1980年代舉辦的一次會議的影響。當時川大的兩位年輕教師,易丹和毛迅,在會上直言四川小說寫得不好,批評四川作家沒有先鋒意識、對於小說的現代性乃至於社會生活的現代性體悟不夠,還是一個鄉下人看自家一畝三分地的狀態。我後來也寫了一篇小文章反省自己。再後來,四川人會從經濟、政治、社會等方方面面檢討自己的‘盆地意識’。”
而今,社會環境比起1980年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阿來希望所有的文學刊物能重拾自身對文化的基本理解、基本責任與基本堅持,讓文學“迴歸本位”。
在這份迴歸中,阿來認為足夠的經費保障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最重要的人的問題。“刊物是有性格的,刊物的性格就是主編的性格。有什麼樣的主編,就有什麼樣的編輯。主編明確的辦刊理念經由編輯傳遞給刊物所聯絡的作家群,如此凝聚而成一本刊物。有時我們翻翻一本刊物,會覺得它不過就是一本湊夠了頁數的東西而已。”
對文學新人的出現與成長,阿來也有很多話想說。他回憶自己做編輯的時候,經常覺得每一篇稿子都四平八穩,既挑不出什麼毛病,也找不到讓人感到振奮與新鮮的東西。
“我們知道,相當一部分青年作家剛開始寫的時候,毛病很突出,但這個毛病裡也有別人沒有的好處。”他說,今天文學刊物想找新人,就該找這樣的新人,“如果他都成熟了,沒毛病了,還要你去找嗎?我們又老抱怨,說小刊物不好辦,寫得好的都給北京、上海投稿去了,這是當然。問題是,在他還不夠好的時候,將要好的時候,你為什麼沒有發現他?為什麼沒有參與他的成長?”
阿來稱,編輯與作家的交往,尤其是對未成名作家的發現、挖掘、幫扶,確實是一個很有難度的工作。而且這份工作的結果還要面向市場,面向公眾,面向廣大讀者的“投票”。“大部分文學編輯在過去不寫東西,現在我們也鼓勵他們試著寫一點,跟周圍的作家亦師亦友,更有好處。寫作最微妙的事往往發生在字詞之間,謀篇佈局之間,然後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思想意義、現實關懷、社會學闡釋等等。它首先是一個文字,需要技藝,如果一個木匠鋸不會鋸,刨不會刨,天天講那些宏觀的東西還有意思嗎?所以我們先得‘心到手到’。今天我們還沒有進入這個層面,大而無當,千人一面,這也是文學刊物要面對的問題。”
書寫鄉村,投入個人命運的寫作
在活動中,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學刊物負責人還從“個人經驗與時代視野”“文學批評的公信力”“鄉村振興的文學表達”等等方面展開深入的交流。第四屆全國文學名刊專家論壇由四川省作協副主席、《四川文學》主編羅偉章主持。《黃河》主編黃風首先對當下“文學批評公信力的下降”展開反思。
第四屆全國文學名刊專家論壇由四川省作協副主席、《四川文學》主編羅偉章主持。
從一個編輯的角度,《廣州文藝》主編張鴻講述了她和一個祁連山下的寫作者之間的故事。這位寫作者是當地文化館的工作人員,一見張鴻就拿出了四篇稿子,但張鴻並不滿意。聽聞對方也是扶貧的工作人員,張鴻便讓他帶著去駐村的地方看一看。“他對口的有十戶人家,對這十戶人家,他講得特別生動。於是我就建議他能不能把每一戶人家的情況都用直白的語言寫出來。”後來交上來的稿子,除去開頭三百字左右的政策引用,張鴻“越看越入迷”,稿子也發於當年的第十期。“我想說的是,對散文這個文體,我們真的要寫自己熟悉的,能把握的東西。”
《廣西文學》副主編馮豔冰提到了社裡編輯李約熱今年新出的一本《李作家和他的鄉村朋友》,它以扶貧工作為全書故事的貫穿線索,構建成一部野氣橫生的鄉村人物誌與風俗志。“李約熱正好是以一個書記的身份到我們點對點的一個扶貧點駐紮了兩年。在寫作中,他把個人的命運放了進去,把人性放了進去。我想,不管你寫什麼主題,如果只是跟著某個主題走,裡面沒有複雜的人性,沒有個人的命運,那麼這樣的作品本身是值得質疑的。”
在《飛天》編輯部主任郭曉琦看來,作家書寫鄉村,一是要主動地克服簡單的描述,二是要注意作品的縱深性,“我們不能光是喊口號,要讓生活中的現實變成文學中的現實。而且在鄉村文學中,我們應該注重地域性,要和鄉村的民俗、風俗習慣、地方文化發生關係。”
“我們是一個文學資源大國,這片大地上真的有非常多東西是可以拿來寫成小說的,但我想,所謂‘個人的經驗’不僅僅是說‘我經歷過什麼’,而是從此處再延伸出去。”站在一個寫作者的立場,《滇池》副主編包倬說,“包括我們把筆下的人物放在心裡,慢慢地滋養他。然後有一天你會發現,你寫這個老張、老李,他可能就是你的親人,也可能就是你自己。你和你的人物之間會產生一種理解,一種感情。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很多作品,似乎還不太能真正地理解人物。”
開啟視野,與時代的脈搏聲聲共振
對於紮根於個人經驗的寫作,《收穫》編輯部副主任吳越想起了發表於《收穫》長篇小說專號2016年秋冬卷的小說《西南邊》。這是四川彝族作家馮良耗時十年寫成的作品。故事透過講述三對彝漢青年相互交織的愛情故事及其家庭生活,呈現了涼山彝族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變遷。小說發表後,做民族誌、社會學研究的彝族青年還專門為此寫了不止於文學批評的文章。
“馮良本人是漢族和彝族結合的後代。對於涼山這片土地的變化,她有很多深入的理解,她的寫作完全紮根於自己所處的身世背景。這樣的作品可以跟時代產生一種共振的關係,我們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忽視它的價值。”吳越說。
《散文選刊》主編葛一敏舉例梁鴻的“梁莊”系列與塞壬的近作《無塵車間》,認為這樣的作品也很好地詮釋了個人經驗與時代視野的關係。梁鴻來自梁莊,她的書寫不僅有關河南梁莊的真實,也有關中國廣大鄉村的真實;去年春,塞壬主動應聘東莞一家電子工廠,並把在一線“臥底”近兩個月的經歷寫成散文《無塵車間》,發表後引發熱議。她們的作品,既與個人的經歷緊密相關,又與時代的脈搏聲聲共振。
“我覺得中國很多作家是沒有時代感的,他們沒有試圖來理解這個時代。這就導致他所反映的時代是一種虛構層面的、想象層面的時代。”《青年作家》副主編盧一萍直言,面對一個時代感強大的國度,如何反映時代確實成為作家應該思考的問題,“但是我們似乎已經缺乏了一種思考的能力。我作為編輯編的這些作品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從我自身的寫作來說,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中篇小說選刊》編輯部主任劉曉閩同樣認為,在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作家的個人經驗如何與當下結合起來去表現這種變化是一個問題。“這兩年,對人類產生最大影響的可能就是疫情,它已經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原來的生活秩序。那麼在未來若干年內,我們能不能產生類似或者接近《失明症漫記》這樣厚重深刻的作品?《失明症漫記》完全是靠作家想象的,寫一個人突然失明瞭,接著一個傳染一個,一群人失明,一個城市都失明瞭。這看起來是很荒誕的事,但人性的善惡在失明的世界裡得到了更直觀地呈現。”劉曉閩說,作為編輯,這兩年她也讀到一些涉及到疫情的小說,但似乎還有些應景,還缺少沉澱,“可能需要作家擁有某種時代的視野,有更深層的思考和表達。”
《山花》特約編輯李晁稱,就時代來說,它的面貌和內容也是龐雜的,且可能帶著遮蔽性,事物浮在淺層的表象之中。如何找到時代中最攸關的部分,這攸關可能並非宏大的題旨,而是與一個個個體切身相關的困擾,就顯得十分重要,“我覺得將焦點對準這一部分進行書寫,找到兩者彼此融合的地方,是可靠的。”
梁鴻《中國在梁莊》
文學寫作,就是面對世界的複雜性
《山西文學》主編魯順民分享了自己對於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文學刊物如何組稿的體會。他總結出了一個關鍵詞:“複雜”。“脫貧攻堅,包括後來的鄉村振興,關鍵詞都是複雜。我期待我們未來有關鄉村振興的組稿,能夠把這種複雜性真正地傳達出來。”
談及文學對世界複雜性的呈現,《當代》副主編石一楓想起了一度火熱的“拆遷文學”。“這些年再看拆遷,我會想到北京最不勞而獲的‘富翁’們,他們很有錢,但也受到反覆的‘精神虐待’。”他說,因為拆遷的緣故,北京有些原來農村地方的鄉民們一躍成為住在北京中關村附近的有錢人,但不斷湧進中關村的IT人士、高學歷人才,讓他們覺得即使身處祖祖輩輩生活過的地方,自己也還是落後人群。
“在有的家長群裡,會有媽媽聽不大懂老師說的話。比如老師說接下來我們要學五言絕句了,但這位媽媽聽不懂什麼是五言絕句,又比如老師說我們要學‘好雨知時節’了,這位媽媽又會問要去哪裡找‘好雨知時節’。”在石一楓的觀察裡,這些鄉民坐擁北大清華學子或許一生都望塵莫及的學區房,但他們依然是最焦慮的人群,“中國社會有政治等級、經濟等級,也有文化等級。所以,同樣看待拆遷,從不同的時間、地點、立場、視角去看,我們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而文學寫作,有時候寫的就是事情的複雜性,“對一個事情,你能不能比別人多想這麼一小步?你只要往前走這麼一小步,可能就是文學的一大步。這個一小步也很難,要自我懷疑,自我批判,但寫作往往也是在這個過程中進步的。”
責任編輯:梁佳 圖片編輯:沈軻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