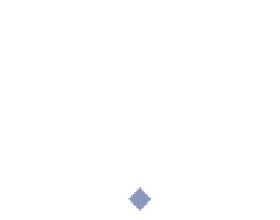孫恩(?—402)字靈秀,琅琊人。盧循(?—411)字於光,小名元龍,范陽涿人(今河北涿縣)。
孫恩起兵於海島
孫恩早年事蹟史無明載,父祖官爵、姓名亦闕如,但知其出自孫秀之族。孫秀出身寒微,因倖幸而見寵於西晉趙王倫,在趙王倫輔政篡權時出謀劃策,助紂為虐,封以大郡,官至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專執朝權。後與趙王倫俱被誅。秀死而族衰,子孫從此仕宦無途,大約在兩晉之際由琅琊移居三吳,世奉五斗米道,社會地位不高。
盧循是西晉司空從事中郎盧湛之曾孫。盧湛雖是“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但卻因中原喪亂“淪陷非所”,“顯於石氏”,在石趙官至侍中、中書監,於石趙末年被冉閔所殺。所以,至早在公元350年,盧循的父祖才投奔東晉,屬於晚渡江者。盧湛仕趙及子孫晚渡,使在西晉時曾是高門甲族的范陽盧氏在東晉淪為“婚宦失類”者,故盧循及其父祖三世無官爵,盧循也不得不娶孫恩妹為妻,與地位較低的琅琊孫氏結成姻親。在婚宦等級界限嚴明的情況下,孫盧兩族的婚宦狀況表明他們均屬於低等士族。
東晉一朝,門閥世族壟斷各級政權,低等士族往往因此仕宦受阻。盧循為人聰敏,“雙眸冏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弈棋之藝”,具有典型計程車人氣質,卻因家族位遇不高而身無一官半職。他對此心懷不滿。時有“鑑裁”的沙門慧遠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
孫恩家族狀況比盧循稍好一些。琅琊孫氏世奉五斗米道。孝武帝時,孫恩權父孫泰,拜有秘術的錢塘富人杜子恭為師。子恭死,孫泰傳其術。他利用五斗米道在浙東廣為流傳的條件,積極擴大家族力量。孫泰“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同時交結太子少傅王雅。他的所作所為引起某些門閥世族的不安。王導子王恂進言於當權的會稽王司馬道子,將孫泰流放到廣州。孫泰在廣州仍傳道惑眾,“南越亦歸之”。後孫泰賴於王雅之助,被孝武帝召回,任為輔國將軍,新安太守。他因“知養性之方”而頗得一些信奉五斗米道的門閥世族的賞識。王雅與其“交厚”,“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秘術”,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孫泰透過傳道,形成了以琅琊孫氏為核心的,上有某些統治階級頭面人物為靠山,下有敬之如神的“百姓”為基礎的地方勢力。
隆安二年(398),王恭起兵叛亂。孫泰在三吳召集義兵數千人以討恭。
在天下兵起,門閥世族之間矛盾激化的形勢下,孫泰認為“晉祚將終”,低等士族出頭之日已到,“遂扇動百姓,私集徒眾,三吳士庶多從之”。以孫泰為代表的三吳地區低等士族的政治動向,引起門閥世族的極大恐慌,“於時朝士皆懼泰為亂”。為維護門閥世族的根本利益,朝廷誘斬了孫泰和他的六個兒子。孫恩幸免於難,逃入海島。
由於孫泰聚兵圖謀反晉仍屬於低等士族反對當權的門閥世族的統治階級內爭,他的被殺並未在東土引起太大的動亂。當時一些五斗米道的信徒不信孫泰真的死了,認為他是“蟬脫登仙”,所以紛紛到海島投奔孫恩,並給孫恩饋贈資財。儘管如此。孫恩也不過在島上聚集了百餘名堅決擁戴自己的五斗米道信徒,只好等待時機,以便舉兵反晉,為叔父孫泰報仇。盧循此時可能也在海島,《晉書·盧循傳》稱及“恩作亂,與循通謀”。盧循是孫恩的主要謀士。
三吳地區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總爆發,為孫恩的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
自東晉初以來,經百餘年的開發,三吳地區成為江南的重要政治中心。
這裡不僅是門閥世族的聚居之地,而且亦是東晉政權的賦稅徭役淵藪。在封建王朝和門閥世族的雙重剝削壓迫下,居住在三吳地區的國家編戶農民生活悲慘,一年“殆無三日休停”。而且隨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加劇,廣大農民肩負的徭役賦稅有增無減。東晉末年,荊揚之爭達到白熱化的程度,王恭、楊佺期、殷仲堪、桓玄佔據上游荊、江、襄、雍、秦、梁、益、寧八州,專擅賦稅,不事朝廷。東晉王朝所能控制的僅有揚州而已。為對付上游的威脅,時操掌朝政的司馬元顯在加重賦稅徵收的同時,有鑑於北府兵不聽指揮的現狀,野心勃勃地想要建立一支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新軍。
但東晉政權兵源枯竭,司馬元顯不得已,只得強制性地徵發浙東諸郡“免奴為客”的壯丁,集中於京師建康,擔任兵役。這些人被稱之為“樂屬”。這一措施引起地主階級中下層以及免奴為客者的強烈不滿。地主階級一般均役使奴婢,這些奴婢即使放免為客,也仍依附於他們。徵發免奴為客者為“樂屬”,等於從他們手中奪走了相當數量的勞動人手;而免奴為客的農民,本已從奴隸地位上升到擁有自己的經濟的半自耕農的地位,卻被徵發為地位低下計程車兵,自然亦不情願。因此這一命令一頒佈,就搞得“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孫恩以此為契機,於隆安三年(399)十月,從海島率百餘眾登陸,攻破上虞(今浙江上虞),殺上虞縣令。又揮軍攻破距上虞縣東南百餘里的會稽郡治山陰。部眾在短期內驟然擴大到幾萬人。於是乎,東土會稽(今浙江紹興)、臨海(今浙江臨海)、永嘉(今浙江永嘉)、東陽(今浙江金華)、新興(今浙江淳安)、吳(今江蘇吳縣)、吳興(今浙江吳興)、義興(今江蘇宜興)等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眾數十萬。由孫恩領導的浙東農民起義正式揭開了戰幕。
義軍兵敗浙東
孫恩以宗教形式發動起義,目的在於報個人私仇。但隨著廣大農民群眾參加到起義之中,起義遂突破了以是否信奉五斗米道劃分敵我的界限,鬥爭的矛頭直指當權的門閥世族和東晉皇朝。會稽內史王凝之,琅琊王氏後嗣,世奉天師道,卻不免與諸子俱被起義軍誅殺。起義軍還誅殺了世族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衝、張琨、中書郎孔道。而對起義軍的強大攻勢,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義興太守魏隱都棄郡逃走,各郡縣兵亦望風奔潰,史稱“八郡皆為恩有”。在建康周圍的王畿諸縣,起義也“處處蜂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整個東晉皇朝為之大震,“人情危懼,常慮竊發”,不得不實行內外戒嚴。孫恩以會稽郡治山陰縣為農民起義軍的指揮活動中心。受其階級侷限和皇權思想的影響,他並沒有建立政權,而是自稱“徵東將軍”,稱其部下為“長生人”。同時上表晉安帝,歷數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之罪,請誅二人以謝天下。對屬於地主階級的所謂“人士”,孫恩或是因他們隨自己起兵而加以重用,如任吳郡陸瑰為吳郡太守,吳興丘尩為吳興太守;或是聽從盧循勸諫,多不誅殺,“人士多賴以濟免”,被任為孫恩的官屬。
由於起義軍成份不一,流品駁雜,紀律鬆弛,無明確的戰略戰術目標。孫恩本人又殘忍酷烈,起義軍向會稽進軍時,軍中因有婦嬰,行動不便,孫恩即命將嬰兒投水溺淹,說什麼“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他又陶醉於一時的勝利,沒有對東晉王朝的軍事反攻進行任何物質和精神準備,認為大功告成,對其部屬說:“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這樣,起義軍只是侷限於進行掠奪財物,焚燒房屋倉廩、毀林塞井一類的破壞性軍事活動,並沒有充分利用勝利局面擴大自己的力量,建立鞏固的根據地,而且也沒有給東晉軍事力量以任何有力的打擊。
東晉皇朝卻沒有對孫恩開啟建康城門。相反,東晉任司馬元顯為中軍將軍,命令世族頭面人物,徐州刺史、衛將軍謝琰(謝安之子)兼督吳興、義興軍事,率軍東征。北府兵著名將領,南徐、南兗二州刺史劉牢之,也從京口發兵。起義軍在無準備的情況下猝然應戰,首戰即告失利,謝琰於隆年三年(399)十二月攻下義興,殺害義軍將領許允之;接著又攻破吳興,起義軍將領丘尩被迫後撤。謝琰與劉牢之步步緊逼,所徵必克。謝琰為穩妥起見,屯兵烏程(今浙江吳興南二十五里),遣司馬高素率兵配合已攻克吳郡的劉牢之,向錢塘江推進。
孫恩聞訊,既不組織反攻,又未積極設防。他寄希望於錢塘江天險,企圖仿效越王勾踐,保有會稽,割據江東。結果劉牢之很快就率軍渡江。孫恩馬上就作出放棄浙東根據地的決定,並用曹操被周瑜擊敗後所說的“孤不羞走”的話為自己的指揮無能開脫。起義軍和家屬二十餘萬人倉促東撤,不得不丟掉大量輜重、寶器和女子。追擊的官軍競相爭奪寶物和女子,孫恩因而倖免於全軍覆滅,率眾登船逃到海島。起義軍卻喪失了浙東地區,留守的義軍將領陸瑰、丘尩、沈穆夫等均遇害。劉牢之縱軍燒殺搶掠,致使東土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者”。這樣,旬日間佔有八郡,人數達數十萬的起義軍,在晉軍的進攻下,幾乎未進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就被擊潰。起義軍所取得的大好局面也幾乎喪失殆盡。究其因,與孫恩的驕傲輕敵,無戰略眼光和指揮失誤不無關係。
孫恩撤回海島,重整軍事,“伺人形便”。東晉王朝擔心他再次登陸,任命謝琰為會稽太守、都督會稽臨海東陽永嘉新安五郡軍事,率徐州文武將吏戍守浙東沿海地區。謝琰憑藉資望,驕奢淫逸,無“綏撫之能”,又“不為武備”(《晉書·謝琰傳》)。因此,隆安四年(400)五月,孫恩率軍從浹口(今浙江鎮海東南)一舉登陸成功,直指餘姚,攻破上虞,進至距山陰縣以北僅三十五里的邢浦。謝琰派參軍劉宣之拒戰,義軍利。數日後,義軍再攻邢浦,打敗上黨太守張虔碩,乘勝向山陰進軍。謝琰親自出戰。在山陰之役中,孫恩首次表現出他的軍事指揮才能。他抓住謝琰驕傲自持、急於求勝的心理,誘敵深入到狹隘的塘路,使官軍不得不魚貫而進,難以發揮步騎優勢。義軍則可充分發揮擅長水戰的特點,在兵艦上發箭猛射,切斷官軍的進退之路,繼而加以圍殲。結果官軍大敗,謝琰和其二子均死於陣中。山陰之戰的勝利,使起義軍士氣大振,沉重地打擊了東晉皇朝的統治。
東晉皇朝為了防止“郡民復應恩”,加緊了對起義軍的鎮壓活動。吳興太守庾桓殘殺男女數千人,以削弱起義軍在吳興的群眾基礎,迫使孫恩轉攻臨海。朝廷派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圍攻堵截。五月至十月,兩軍相峙,不分勝負。十一月孫恩在餘姚擊敗高雅之。高雅之喪眾十之六七,退守山陰。朝廷任命劉牢之為都督會稽等五郡軍事,率軍征討。孫恩避開強敵,又撤回海島。劉牢之屯兵於會稽上虞,派部將劉裕戍守句章(今浙江寧波市南);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滬瀆壘(今上海市),以備孫恩。浙東又重新被官軍所控制。
由於義軍在富庶的浙東地區未有立足之地,不僅人員和物資補充發生困難,而且其影響的範圍也比較有限。孫恩為改變這一局面,於隆安五年(401)二月再次出浹口,攻句章。劉裕帶領守軍拼死抵抗,劉牢之及時增兵解圍,孫恩復撤回海島。三月,孫恩又北上海鹽(今江蘇海鹽)。劉裕亦沿海岸線北上,於海鹽築城。孫恩輕舉攻城,失利,部將孫盛被殺。劉裕寡眾,恐久戰難支,遂空城設伏。孫恩中計,大敗於海鹽,不得不轉攻滬瀆。劉裕也棄海鹽,追蹤北上,與義軍糾纏。孫恩為擺脫劉裕牽制,猛攻裕軍,全殲其先鋒,劉裕所部亦死傷且盡,損失慘重,一時無力再與義軍對抗。
孫恩擺脫劉裕羈絆後,北上攻破滬瀆壘,殺吳國內史袁山松,消滅官軍四千餘人,取得了自山陰之戰以來的又一重大勝利。乘此餘威,六月,孫恩率樓船千餘艘,戰士十餘萬,從滬瀆逆江而上,直逼建康。朝廷駭懼,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遣將戍守石頭城、秦淮河入江口以及南岸和白石等要塞,以備不虞。同時召劉牢之自山陰引兵堵截孫恩。劉牢之大軍行動遲緩,乃派部將劉裕率精銳千人,日夜兼程,與義軍同時到達丹徒(今江蘇鎮江東丹徒鎮)。
孫恩登岸,佔領城西的蒜山。劉裕不顧遠涉疲勞,乘孫恩立足未穩而發起突襲。孫恩軍潰,撤回船上,率船隊繼續向京師進軍。孫恩擅長水戰,途中多次打敗後將軍司馬元顯的東晉水軍。司馬道子在義軍日益逼近的形勢下,惶惶不安,日夜在建康附近的蔣侯廟禱告求靈,無它謀略。
孫恩原打算乘京師兵力分散,各地官軍未能及時增援京師時,攻其不備,迅速佔領建康。但不料因逆水逆風而行,高大的樓船艦隊前進遲緩,從丹徒至白石花費了數日時間。這時,豫州刺史譙王司馬尚之已率精銳步騎到達建康,屯駐積弩堂,劉牢之亦領北府兵赴京,鎮守在建康以西江中的新洲。孫恩見攻其不備的戰略目標已難實現,遂“不敢進而去”。在途中曾派兵攻陷廣陵(今江蘇揚州市),消滅官軍三千人,又親率水軍浮海攻下鬱洲(今江蘇連雲港東雲臺山一帶),生擒東晉將軍高雅之,但並未給東晉皇朝造成致命的打擊。
東晉既解京師之難,派遣鎮壓農民起義有方的劉裕為下邳太守,赴鬱洲討伐。劉裕數戰數捷,孫恩難以在鬱洲立足,沿海南下。劉裕鍥而不捨,率步騎亦南下。隆安五年(401)十一月,劉裕在滬瀆、海鹽地區追及孫恩,大敗起義軍。史稱劉裕“俘斬幾萬數”。孫恩無力扭轉敗局,又登船自浹口退守海島,從此一蹶不振。在以後的四個月中,東晉皇朝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荊揚之爭已兵戈相見。鎮守荊州的桓玄與把持朝權的司馬道子父子發生火併,北府兵也捲入到這場廝殺之中。孫恩隱居海島,坐失官軍無暇東顧的良機,毫無軍事建樹。直至桓玄佔領京師,操持朝權,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已緩和後,在元興元年(402)三月,他才率軍進攻臨海。但時過境遷,東晉皇朝已早有所備。在與臨海太守辛景的作戰中,孫恩失利。隨同他起義的“三吳男女,死亡殆盡”。他在暫時受挫的情況下,完全喪失了繼續鬥爭的信心。“自奔敗之後,徒旅漸散,懼見生獲,乃於臨海投水死。”(《宋書·武帝紀》)他的家屬和部屬受宗教觀念的支配,在孫恩投水自盡後,都認為他變成了水仙,隨同他一起投水者,有一百多人。
從隆安三年(399)十月至元興元年(402)三月,十七個月中,孫恩領導的農民起義席捲整個浙東地區。孫恩利用宗教作為發動起義的手段,但在起義過程中又突破了宗教形式的限制。他雖出身低等士族,但因參加起義的群眾多半是奴婢佃客,所以為滿足起義群眾的要求,他也採取了無情打擊的方式消滅以王謝為首的門閥地主勢力,從而將鬥爭矛頭直指東晉皇朝和當權的門閥世族。在鬥爭中,他開農民戰爭戰略戰術上未有之前例,依靠艦船與敵人進行水戰。但由於階級的侷限,一些燒殺搶掠、殘害無辜、殺戮婦嬰的活動,敗壞了起義軍的聲望,模糊了起義的目標。孫恩為人苛忍而又怯懦,無雄圖大略,非將帥之材,少臨陣決斷;他不注重陸戰,僅滿足於溯回江河湖海之間,而未建立鞏固的根據地。以致於大小數十戰,勝者屈指可數;初起兵時,男女二十餘萬,但最後“裁數千人存”,使浙東農民起義的大好局面喪失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