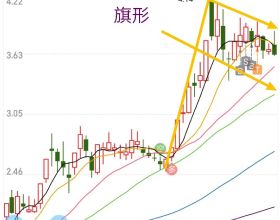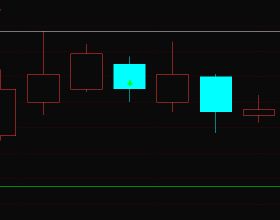隨著時代的發展,神秘的考古學慢慢走出象牙塔,走向普通民眾。曾經遊離在大眾生活之外的考古遺址,如今已成為大家嚮往的旅遊目的地。正是得益於這些遺址的開放以及全方位的宣傳,考古學、考古工作者有機會獲得更多來自“圈外人”的理解和關注。
此次“筆尖上的華北考古之旅”將從北京啟程,向北行至內蒙古元代故都,再遊歷山西、河北眾多考古遺址,最終回到起點,細數京城遺珍。讓我們藉助文字與圖片,遊歷那些散佈在華北大地上的歷史建築和考古遺蹟,與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古蹟親密接觸,領略中華文明的燦爛,感受田野考古的魅力。
大元三都
這次穿越時空的華北考古之旅將從北京啟程。北京,一座有著3000多年建城史、1000多年建都史的古城,早在西周時期就是燕國的腹地。938年,遼太宗耶律德光將這裡定為“南京幽都府”,也稱燕京。隨後不久,金朝的海陵王又將都城從黑龍江遷至此地。經過數千年的建設和發展,北京終於在元代迎來了高光時刻,首次作為大一統王朝的都城走上歷史舞臺。
元大都
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為解決汗位之爭所引發的矛盾,命劉秉忠、郭守敬等人在燕京之地營建一座都城,到至元十三年(1276年),經過近10年的建設,一座新的都城拔地而起,史稱元大都。這座新建的都城規模宏大,根據《元史·地理志》記載,大都“城方六十里”,面積約為50平方千米,元大都道路規劃整齊、經緯分明。考古發掘表明,元大都中軸線上的大街寬約28米,堪比現在的雙向四車道,就連城市中的火巷(衚衕)也有近7米寬,城市輪廓方正,街道筆直。元大都街道的佈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的基本格局。
元朝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在建造元大都時融入了蒙古族“逐水而居”的特色,同時,這座城市還借鑑了中原文化中傳統都城建造的理念,使大都城的佈局別具一格。例如,元代的皇城並非以皇帝辦公、居住的大內宮城為中軸、東西對稱,而是以太液池為中心,宮殿環繞在其周圍,足見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對宮城建造的影響。皇家用於祭祀的太廟和社稷壇分別建在皇城的東面和西面,大都城除北邊城垣外,其餘城垣各開三門,這均符合《周禮·考工記》中“左祖右社”“方九里,旁三門”等相關記載。此外,元代統治者還在大都城建造了孔廟、國子監等禮儀和功能性建築。
說到元大都,不得不提這座城市的水系建設。水是一個城市發展的源泉,自古以來,大都市多建立在大江大河流經的地方,但是北京卻不具備這樣的自然條件。元代水利專家郭守敬以其高超的智慧解決了這一難題。他利用京北和京西眾多泉水,讓其彙集於城內已有的河道,然後透過積水潭、通惠河注入到大運河中。令人驚奇的是,全長約80千米的通惠河連同全部閘壩,僅僅用時一年半便全部完工。自此之後,南方的貨物可以直接運抵元大都城內,而作為終點碼頭的積水潭桅檣如林,熱鬧非凡。
明代初年,明成祖朱棣將都城從南京搬到北京後,以南京故宮為藍本營造了北京故宮,並將北京南城牆向南移1千米,北城牆向南移2.5千米。原來的元代城牆並未拆除,而是任其自行湮滅,到了清代,元大都南城垣消失殆盡,西邊和北邊只剩下幾段。時過境遷,滄海桑田,當年莊嚴雄偉的元大都早已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僅留下一些殘垣斷壁訴說著曾經的輝煌。
如今,每到海棠盛開的季節,北京北土城附近的遊客總是絡繹不絕。沿著小月河綿延千米的海棠競相怒放,或許是海棠花太美,抑或是北京的古蹟太多,來這裡遊玩的人們大多忽略了這裡是一處重要的歷史遺蹟—元大都城垣遺址。河邊那些不起眼的土坡,便是曾經鼎鼎有名的元大都城牆。元代的城牆採用宋代的舊法,先在牆內安裝永定木,然後加上橫向的木頭,在這個基礎上加土夯築。由於元朝初年天下剛剛平定,內無反叛,外無憂患,加之國庫空虛,便沒有包裹城磚。為防止雨水侵襲,元廷專門派軍隊編織蘆葦蓋在土城牆上,老百姓將其戲稱為“蓑衣城牆”。不同於明清兩代,元代的城牆只有夯土沒有城磚,被稱為土城牆,地名北土城因此而來。
元中都
其實,元大都建成之後沒多久,元武宗海山就開始謀求遷都。雖然他在位時間只有短短4年,但卻經常出現在史料中,不僅是因其在位期間元代的疆域達到巔峰,更是因為其大興土木,營造了中都城。1307年,元武宗下令在旺兀查都(今河北張北縣)修建中都城,直到1311年,元武宗駕崩,儲君愛育黎拔力八達(即後來的元仁宗)下令罷建中都。雖然中都城最終沒能完工,但是經過三年多的建設,已經初具規模。令人吃驚的是,從史書中可以推斷出,中都宮城從動議到初步建成只用了短短半年的時間。元人編纂的《經世大典》,已將這座“爛尾都城”與大都和上都並稱,足見其當時的地位。
從遺存的城垣和建築基址來看,元中都由宮城、皇城、外城三重城池相套而成,不同於大都內城以太液池為中心,中都的建築完全按照中原傳統的中軸線佈局。作為帝王辦公場所的一號宮殿基址處於內城的中心位置,與《呂氏春秋》中“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相契合。不過,在考古發掘中,學者們發現宮城內有用於放置氈帳的空地。這樣的安排,巧妙地將草原文化和中原文明融合在一起。
時移事易,元武宗興建中都城的理由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是其好大喜功,效仿元世祖在草原建設一座新的都城,標榜自己的功績;有學者認為這是遼金時期多京制度的延續,是民族交流與和解的必然結果;也有學者認為中都建造完全是出於軍事方面的考慮,有利於政權的統一……雖然建都理由目前尚無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元中都在元武宗執政期間是整個元朝的政治中心。
如同許多歷史遺蹟一樣,元中都也沒能逃過在戰火中覆滅的厄運。1358年,中都城中的建築在紅巾軍的一把大火中化為灰燼,只留下一些殘垣斷壁,從此被世人淡忘,直到1998年才被考古學家發現。元中都是儲存最完好的元代都城遺址,因此也成為探究元代都城制度演變重要的實證。
元上都
除元大都、元中都外,元帝國曆史上還有一個重要都城,那就是元上都。位於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的元上都,距離張北的元中都大約195千米。元上都“北控沙漠,南屏燕薊,山川雄固,迴環千里”,自古以來,就是北方遊牧民族重要的牧場和戰場。那裡原名曷裡滸東川,由於川裡每年都會長滿金蓮花,所以金朝皇帝將其改名為金蓮川。忽必烈當年駐帳於此,“徵天下名士而用之”,建立歷史上有名的“金蓮川幕府”,總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為了讓漢族幕僚適應那裡的生活,忽必烈命劉秉忠在桓州、灤水以北的龍崗營建新城,定名為開平府。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身亡,忽必烈在開平府自行召開會議,在部分蒙古貴族的支援下即位蒙古大汗。1263年,忽必烈將開平府定為上都,為元朝的夏都。
總理漢地事務讓忽必烈對漢文化有了較深刻的認識,這也體現在上都的佈局中。上都由宮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構成,周長約4.5千米。透過對上都的考古發掘可知,上都的宮城和皇城的城牆用磚或石塊包砌,建築構件雕刻精美,城內道路整齊,功能區劃明確,皇城以南為官署、府邸所在地,皇城西北為皇帝的御苑,城外則是居民區、倉廩、市集所在,佈局井然有序。元上都有多麼豪華,從《馬可·波羅遊記》中可以窺探一二:“內有大理石宮殿,甚美,其房舍內皆塗金,繪重重鳥獸花木,工巧之極,技術之佳,見之足以娛樂人心目。”
儘管後來忽必烈遷都至大都,但是上都依然是元帝國的聖地,有元一朝,前後有6位皇帝在此登基。草原上的元上都也是一處避暑勝地。元朝皇帝幾乎每年有半年時間都在這裡,不僅能避暑,還能與蒙古貴族加強聯絡,一舉兩得。1368年,元大都被攻克,元朝最後一個皇帝元惠帝逃回上都,仍以大元為國號,史稱北元。直到1402年北元滅亡,蒙古各部落又回到了爾虞我詐的爭鬥之中。
如今的元上都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華,再也見不到“西關輪輿多似雨,東關賬房亂如雲”的景象。但是,在考古學家的努力下,元上都以另一種姿態展現在世人面前,默默地訴說著一個時代的輝煌。2012年,元上都遺址正式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全人類共同的寶貴遺產。
土木華章
離開茫茫的內蒙古草原,讓我們將目光投向表裡山河的三晉大地—山西。那是一個隱藏著無數傳奇的地方,八百里太行在那裡崛起,五千年文明在那裡沉澱。山西特殊的地理條件和氣候環境,讓無數凝結人類歷史的寶貴財富躲過了戰火和自然災害的侵擾,留存至今。
“地下文物看陝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截至2019年,山西共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32處,穩居全國第一,其中古建築類“國保”多達420多處。元代之前的古建築,山西佔全國的80%以上,我國現存的三座完整唐代木構建築全部在山西。佛光寺東大殿便是三座完整唐代古建築之一,它的發現過程充滿了傳奇色彩。
1937年,侵佔中國東北6年之久的日本侵略者,預謀在華北地區挑起更大事端。與此同時,在沒有硝煙的文化戰線上,幾位年輕的中國學者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打破日本學者關野貞近乎狂妄的宣言:“中國全境內木質遺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實際說來,中國和朝鮮1000歲的木料建造物,一個亦沒有。日本卻有30多個有1000到1300年曆史的建築物。”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炮轟盧溝橋的當天,一封電報從山西五臺縣發往北平(今北京),7月9日,這封電報的內容在《北平晨報》上被披露,題為《營造學社調查組發現唐代建築寺院》。民國時期,建築學家朱啟鈐創辦營造學社,旨在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成員包括留學美國的梁思成(梁啟超之子)、林徽因夫婦,留學日本的劉敦楨等。這一學社在特殊的年代發現並保護了一大批重要古建築,同時為我國培養了眾多古建築研究大家。
▲ 佛光寺
佛光寺東大殿是如何被發現的呢?日本學者的挑釁如同日本侵略者的刺刀,刺痛了中國學者,他們認為中國一定存在唐代建築。法國學者伯希和拍攝的《敦煌圖錄》讓梁思成等人看到了希望,他們發現一幅唐代壁畫上標註的一處“佛光寺”與日本學者先前在山西考察時發現的佛光寺十分相似。不知是過於自信,還是囿於學術水平,日本學者關野貞和常盤大定並未將目光投向這座大殿,僅留下“佛光寺之寺院規模、伽藍並不雄偉”這一簡單的評價。
梁思成、林徽因二人透過比對照片以及佛光寺東大殿前經幢上的銘文,認為這座大殿與當時中國公認最早的建築—遼代獨樂寺觀音閣有很多相似之處,覺得有必要現場探察一番。由於時局動盪,土匪橫行,加上樑啟超兒子、兒媳這樣特殊的身份,讓他們出行十分不便。後來,在警察荷槍實彈的護送下,他們才得以開啟考察之旅。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以梁林二人為代表的中國營造學社考察團,來到了山西省五臺縣的佛光寺。
1937年7月5日,佛光寺遇到了知音。在佛光寺東大殿測繪數日的學者們發現大梁之下有墨書題記,由於大梁距離地面有兩丈多(一丈約3.33米),根本無法辨識。這時,林徽因的遠視眼派上了大用場。她看見題記中有“女弟子寧公遇”之名,正與大殿門口的經幢上刻的“佛殿主寧公遇”相吻合。佛殿主既書寫在大梁上,又刻在經幢上,正好互為印證。即使兩者不是同時完成,也應該是同一時期完成。所以,梁林二人認定這座氣勢雄偉的大殿大約建於唐代大中十一年,也就是857年前後。佛光寺東大殿的發現及準確斷代,一舉打破了日本學者狂妄的氣焰,也彰顯了中國學者紮實的古建築學功底,終結了“中國沒有唐代建築”的荒謬論斷。
佛光寺東大殿造型古樸,出簷深遠,斗拱碩大,遠遠望去給人以蒼勁有力之感。這座大殿的建造年代雖晚於五臺縣的南禪寺大殿,是我國現存第二早的木結構建築,但其因巨大的形制、精美的唐代雕塑以及珍貴的唐代題記壁畫,還是被梁思成譽為“中國第一國寶”。
其實,早在測繪佛光寺東大殿之前,中國營造學社就在山西發現了數量眾多的古建築,如大同的華嚴寺和善化寺,朔州應縣的佛宮寺釋迦塔(應縣木塔)等。與佛光寺東大殿的發現一樣,應縣木塔的發現也是一段傳奇。
當年,梁思成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學習,他的父親梁啟超給他寄去了一本成書於宋代的《營造法式》。梁思成被這本書深深吸引,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歸國後,梁思成加入中國營造學社,尋找散落在全國各地的古建築。不過,該去哪裡尋找明清之前的建築呢?當時流行一句諺語—“滄州獅子應州塔,正定菩薩趙州橋”,這給梁思成帶來了啟發。說來也巧,還是那個前文提到的日本學者關野貞,曾在1918年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北方的考古報告,剛好提到了建於11世紀的“應州塔”。這激發了梁思成的興趣,然而他遍覽古籍也沒找到一張木塔的照片。只有親自跑一趟才能一覽這座塔的真面目。不過,當時條件艱苦,交通不便,如果這座塔是明清時期所建,或者已經被毀,那豈不是白跑一趟嗎?
梁思成靈機一動,決定寫一封信寄到應縣最大的照相館(儘管他不確定應縣是否有照相館),並在信中附上一元錢,讓照相館寄一張應縣木塔的照片。沒想到他竟然收到了回信,信中還真有一張應縣木塔的照片。透過仔細比對照片中的木塔,梁思成認為這座塔應該是一座遼代建築,這讓他喜出望外。1933年6月,經過一番準備,梁思成一行踏上前往晉北重鎮大同和應縣考察的旅程。
當真正見到應縣木塔時,梁思成等人驚呆了!當時,林徽因因故未能與考察隊同行,梁思成在給林徽因的信中寫道:“塔身之大,實在驚人……我第一個感觸,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道你要幾體投地地傾倒……使我愉快得不願意忘記那一剎那人生稀有的由審美本能所觸發的敏銳。”到底是怎樣一座建築,讓見多識廣的梁思成發出如此感慨?
應縣木塔高67.31米,高度相當於現在的20層樓,底層直徑30.27米,純木結構,耗費紅松木料約3000立方米,重約2600多噸。木塔共五層六簷,這是因為第一層是兩層屋簷。每層之間還有一個夾層,實際上是九層,所以應縣木塔有明五暗四的說法。木塔的平面是八邊形,層與層之間的斗拱更是多達三四十種之多。根據營造學社以往的工作效率,一座古建築的測繪大概一兩天就可以完成,但是應縣木塔足足用了梁思成和莫宗江6天的時間,足可見其複雜程度。
我國傳統建築以木結構為主,被譽為“土木華章”。這一建造傳統技藝始於新石器時期,甚至可能更早。新石器時期,中國北方建築以半地穴式為主,南方建築以幹闌式為主,建造技法雖有所不同,但都是以木頭為原材料。木結構建築取材方便,建造週期短,但是容易腐朽,不易儲存。古代文學作品中對建築的描寫,如《詩經·小雅·斯干》中“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阿房宮賦》中“廊腰縵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給了今人無限的想象空間。但是,再生動形象的文字描寫也無法比擬實物給人的衝擊感。正是在這些前輩學者的努力下,今人才得以有機會欣賞古建築造型的精美,領略古建築構造技藝的精湛。
晉國霸業
雖說“地下文物看陝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其實山西不僅地面文物資源豐富,地下文物也令人驚歎。從舊石器時期的丁村遺址到新石器時期被譽為堯都的陶寺遺址;從先秦時期的天馬—曲村遺址、侯馬晉國遺址到西漢時期的大型墓葬遺址;從北魏都城平城遺址到李唐王朝的龍興之地太原城,再到數不清的遼金時期磚石墓,山西黃土之下的寶藏著實給世人帶來了太多的驚喜。
桐葉封弟
山西簡稱“晉”,別稱三晉大地,這是因為山西曾是先秦時期諸侯國晉國的主要勢力範圍,後來韓、魏、趙“三家分晉”,史書將這三國稱為三晉,才有了這些稱謂。傳說,強大的晉國起源於一片小小的桐樹葉。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桐葉封弟”,《呂氏春秋》和《史記》中都有過記載,大概的意思就是,年幼即位的周成王與弟弟叔虞在一起玩耍,少年天子意氣風發,撿起一片桐樹葉剪成玉圭的形狀,對叔虞說:“我將拿這個玉圭封你。”叔虞高興地將這件事告訴叔叔周公。周公請示成王,成王表示自己和弟弟只是開個玩笑,周公表示,君無戲言,成王無奈將唐分封給叔虞。
後來,抵達封地的叔虞,一手抓生產,一手抓國防,把唐國經營得有聲有色。這個唐國其實就是晉國的前身,叔虞的兒子燮父即位後,將都城遷到晉水一帶,並將國號改為晉。當初,叔虞的爵位僅是伯爵,燮父即位後透過一些手段讓周天子下令“命唐伯侯於晉”,其爵位由伯爵升格為侯爵,自此開啟了晉國600餘年的光輝歷史。從西周到春秋時期,晉國一直都是北方最強大的諸侯國之一。特別是在春秋時期,晉國大多數時間裡獨霸中原,湧現了晉文公、晉襄公、晉景公等多位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君主。因此,坊間才會流傳“一部春秋史,半部晉國史”這樣的諺語。
晉國遺址
儘管晉國曾經在歷史上非常輝煌,但是對於現代人來說,這個諸侯國還有很多未解的謎團。例如,叔虞始封的唐地至今仍舊撲朔迷離,很長一段時間內,燮父遷都後的晉地也一直困擾著研究者。直到20世紀80年代,天馬—曲村遺址的發現,才讓困擾已久的學者們看到了揭開謎底的曙光。考古學家透過研究發現,燮父遷都後的晉地應該距離天馬—曲村遺址不太遠,極有可能就在如今的山西翼城縣境內。
天馬—曲村遺址位於晉南臨汾地區曲沃、翼城兩縣交界處,是一處年代與晉國相始終,而以西周及春秋早期為盛的晉國文化遺址。為了探索晉國早期文化的面貌,考古學家從1979年開始對這處遺址進行發掘,時至今日進行了8次大規模的考古勘探工作,共發現晉侯及其夫人墓葬9組19座,可以分為3排,從北往南依次有4組、2組和3組晉侯和夫人墓。每組晉侯和夫人墓葬周圍都有數座陪葬坑和一座車馬坑。透過對出土青銅器上的銘文以及墓葬形制、出土陶器的觀察和研究,已經可以基本確定這9組墓葬的主人就是西周至春秋早期的9代晉侯和夫人墓,即從晉侯燮父開始,一直到春秋早期的晉文侯。
這19座墓葬在形制上並不一樣,有的有兩條墓道,有的只有一條墓道,還有一座晉侯夫人墓甚至一條墓道都沒有。先秦時期,禮法森嚴,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要符合禮法的規定。孔子就曾經說過:“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根據史籍的記載,天子死後的墓葬應該建4條墓道,由於和“亞”字的繁體字“亞”很像,考古學家將這類墓葬稱為“亞”字形大墓;一般等級較高的諸侯、貴族的墓葬會有兩條墓道,形似漢字“中”,所以被稱為“中”字形墓;等級低一些的貴族墓葬只有一條墓道,由於和“甲”相似,這類墓葬被稱為“甲”字形墓。當然,沒有墓道就意味著等級更低。除了墓葬形制之外,墓葬中出土的隨葬品也是識別墓主人身份的有力證據。先秦時期的青銅禮器就有“明貴賤,辨等列”的功能,以青銅鼎、簋的組合為例,天子使用的規制為九鼎八簋,諸侯則是七鼎六簋。
天馬—曲村遺址的墓葬群採用的是西周時期常見的族葬制,整個墓葬區分為公墓區和邦墓區。上文提到的9組19座墓葬就是公墓區,埋葬晉國國君等高階貴族,而邦墓區則埋葬中小貴族及平民,公墓區和邦墓區有著明顯的分割線,足見當時的等級與尊卑。
晉侯珍寶
儘管史書中對晉國的記載比比皆是,然而這些史料只是大致勾勒出晉國的面貌,即使是再細微的描述,也需要靠想象“復原”,不夠真切。但是,考古出土的實物卻不一樣了,它們彷彿可以帶領我們穿越時空,感受那個時代脈搏的跳動。山西博物院的鎮館之寶—晉侯鳥尊就出土於天馬—曲村遺址。整個鳥尊以鳳鳥回眸為主體造型,頭部微微昂起,高冠直立。鳳鳥的身體豐滿,兩翼向上捲起。在鳳鳥的背上,還有一隻靜靜相依的小鳥,做成鳥尊器蓋上的捉手。鳳尾下設一象首,象鼻內捲上揚,與雙腿形成穩定的三點支撐,全身佈滿紋飾。整件器物造型寫實、生動,構思奇特、巧妙。鳥尊的蓋內和腹底鑄有銘文“晉侯作向太室寶尊彝”,可證明這件器物是用作宗廟祭祀的禮器,在某一任晉侯去世後,作為隨葬品帶到墓葬中了。
晉侯鳥尊是幸運的,深埋地下數千年,躲過了無數次盜墓賊的覬覦。然而,現分別藏於上海博物館和山西博物院的晉侯蘇鍾就沒有那麼幸運了。1992年,晉侯墓地8號墓遭到盜掘,大量珍貴的隨葬品被販賣到國外,其中14枚晉侯蘇鍾出現在香港的古玩市場。時任上海博物館館長的馬承源慧眼識珠,花重金將這14枚被人說成贗品的青銅鐘買回國內。後來,晉侯8號墓又出土了兩枚青銅鐘,正好與那些配成一套,它們的價值也得以確認。
西周晉侯蘇鍾共16件,可分為兩組,排編成兩列音階與音律相諧和的編鐘。上面共有銘文355個字,首尾相連刻鑿在16件鐘上,而同時期大多數編鐘上的銘文都是在鑄造時印刻在模範(制器物的模型)上,幾乎沒出現過鑿刻的方式。銘文敘述了周厲王親征東國、南國的一段歷史。西周晉侯蘇鍾銘文記載的這場戰爭,在史籍中無從查考,對研究西周歷史和晉國曆史極為重要。此外,銘文中記錄的多個事件對西周的斷代研究也有重要價值。
晉侯鳥尊和晉侯蘇鍾只是天馬—曲村遺址所有出土文物的縮影。如今,這裡出土的文物大多數儲存在山西博物院、晉國博物館等博物館裡。晉國博物館建立在天馬—曲村遺址之上,在那裡不僅能看到珍貴的文物,還能近距離觀察3000多年前的墓葬。儘管晉國早已滅亡,但是這些遺存卻讓它永遠烙印在歷史中。
天馬—曲村遺址的發掘和一所學校息息相關,那就是我國現代田野考古的發源地之一—北京大學。從1963年起,一個個懷揣夢想的北大考古師生相繼來到這裡,調查、發掘、紮根、生活。如今,時光已悄然流逝將近一個甲子,當年的帶隊老師已經離開,而當年發掘遺址的學生已經扛起考古的大旗,成為我國考古事業的中流砥柱。一代又一代北大考古人,將天馬—曲村遺址的發掘成果和考古故事在課堂上講述、傳承。在這裡,他們寫就了當時中國體量最大、公佈資料最全面的考古發掘報告。2008年,北大考古系1986級本科生在曲村工作站內樹立 “曲村之戀”石碑,以紀念這段緣分與情誼。
當然,除了天馬—曲村遺址之外,三晉大地上還遺存了眾多各個時期的歷史遺蹟,我們可以透過文物或遺址,感受歷史的厚重。
故國雄風
從晉南順著漳河,一路往東便來到了河北邯鄲。相信很多人知道邯鄲,源自成語“邯鄲學步”。《莊子·秋水》中記載了這樣一則小故事,一個燕國人到趙國都城邯鄲,看到邯鄲人走路的姿勢很美,就跟著學起來。結果不但學得不像,還把自己原來的走法也忘了,只好爬著回去。
曹魏鄴城遺址
成為趙國都城,的確是邯鄲的高光時刻,但卻不是這座城市唯一的榮耀瞬間。如今隸屬邯鄲市管轄的臨漳縣,同樣聲名顯赫,多次站在歷史舞臺的“C位”。有著“三國故地,六朝古都”之稱的鄴城遺址就位於此地。從春秋開始,一直到北周,鄴城存續了1200年。曹魏、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和北齊6個國家先後在這裡建都,留下了鬼谷子廟、西門豹祠、銅雀臺、曹操墓、天子冢等眾多歷史遺蹟。大家最熟悉的莫過於銅雀臺,杜牧的“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讓這座高臺建築名揚天下。
作為鄴城三臺之一的銅雀臺位於鄴城西垣北部,始建於曹魏時期。銅雀臺居中,冰井臺居北,金虎臺居南。史籍中記載:“三臺列峙而崢嶸……亢高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附以蘭奇,宿以禁兵。”從這段描述,不難看出鄴城三臺是當時的軍事設施。後來,在文人騷客的演繹之下,才成為才子佳人吟詩作賦的浪漫之地,然而背後卻是無盡的殺戮和陰謀。直到後周武帝下詔毀撤鄴城三臺,它們才化作文化符號。雖然建築被毀,但是三臺的臺基尚存。現在,三臺遺址中儲存最好的是金虎臺,臺南北長120米,東西寬71米,高12米,昔日宮殿的高大雄偉依稀可辨。
雖然銅雀臺的名聲很大,但是鄴城遺址給考古學家帶來的最大的驚喜,卻不是這座高臺建築,而是整個城市的佈局和規劃。毫不誇張地說,鄴城的城建模式開啟了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都城建設的統一格局:單一宮城、三套城垣、整齊劃一的棋盤狀裡坊,堪稱城市規劃史上的“里程碑”。鄴城模式什麼樣?一時間難以想象,如果說後世的隋唐長安城、明清北京城就是在鄴城模式的基礎上進行建設的,或許你就能在腦海中浮現出這座古城的輪廓。
透過田野考古發掘,學者們發現,曹魏鄴城在建設時,以西北為尊,宮城建在城市的北部西側,以三臺作為屏障。全城唯一的東西大道將整個城市一分為二,北部為尊,為皇家和貴族用地;南部為卑,以平民居住的裡坊為主。特別是南邊城門開以單數,從而發展出中軸線的概念。此外,鄴城的建造還運用了古人對於宇宙天象的認知,認為天子居於人間,居所應該模擬天象五官之中宮,將宮城置於都城中央天元處,取象北辰。如《論語》中所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鄴城宮城採用的正是“象法天地,模擬紫微宮,天人合一”,也就是民間流傳的“天上紫微垣,地下紫禁城”。鄴城毀廢后,盡是荒蕪。隋人段君彥在《過故鄴》中曾寫道:“舊國千門廢,荒壘四郊通……雖臨玄武觀,不識紫微宮。”雖然這座都城早已不存,但是考古學家卻用手鏟讓我們看到一座開創先河的都城。
近年來,鄴城還在不斷給世人帶來驚喜,誠如河北省考古所的專家所說:“大音希聲,那些深埋鄴城地下的無聲密語,不斷地誘惑著人們去探索,去發現。”2012年春節,考古學家在鄴城附近發現了2895塊殘損的佛造像,其精美程度和數量都開創了新中國佛教考古之最。這批造像內容豐富,造型生動形象,惟妙惟肖。透過仔細辨認,這些佛像都是有意毀壞然後埋藏地下。根據專家推測,這源於1500年前的一次大規模滅佛運動—周武法難。建德三年(574年),北周武帝詔令廢佛,開始大肆焚燒佛經,砸毀佛像,推倒佛寺,當年的鄴城也沒有逃過此劫,這才有瞭如今的驚天發現。鄴城或許已經被世人遺忘,但是曾經在這裡發生的歷史,卻深深鐫刻在這片土地裡。
滿城漢墓
考古工作充滿著偶然性,很多重要發現就發生在不經意間,大名鼎鼎的滿城漢墓便是如此。1968年5月13日,河北滿城縣(現保定市滿城區)西南1.5千米的陵山上,來了一隊執行任務的解放軍官兵。他們奉命在這裡炸出一條隧道,然而火藥引爆後,卻不見崩塌的石頭,反而聽到一聲沉悶的回聲。這種情況十分罕見,一位膽大的戰士主動請纓,檢視爆炸點周圍的情況。當他走近之後,一個深約數十米的黑洞赫然出現在他的面前。當戰士們拿著火把進入山洞後,他們被眼前的景象鎮住了—無數珍貴的文物散落一地。
“這一定是一座古墓,是一座古墓!”一位老兵首先緩過神來。這次任務的負責人意識到事情的緊急性,命令戰士們保護現場,然後帶了幾件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向上級彙報。此時,執行任務的戰士們還不知道,他們發現的古墓將震驚世界。
河北省相關部門收到訊息後,立即對古墓進行搶救性發掘。從5月29日起至6月24日,河北省文物工作隊會同當地駐軍對一號墓的甬道、耳室等進行清理。6月26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派出專業考古工作者,與當地考古人員合作,清理一號墓的主墓室。在此過程中,他們推斷出二號墓的位置,並展開考古工作。9月19日,經過三個多月緊張細緻的工作,共清理出文物10633件。
這次重大發現,引起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關注,他根據出土器物上的“中山內府”的銘文,推斷出墓主人是西漢時期的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夫人竇綰。後續的研究也證明了郭沫若的判斷。滿城漢墓一號墓為劉勝墓,東西長51.7米,南北寬37.5米,最高處6.8米,容積2700立方米。竇綰墓東西長49.7米,南北寬65米,容積3000立方米。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銅器、陶器、鐵器、金銀器等生活用品。特別是兩個墓葬中都出土了完整的“金縷玉衣”,在此之前,金縷玉衣只出現在古籍中,這是第一次露出廬山真面目。
由於古人認為玉石可以使屍身不腐,所以貴族會用玉石陪葬,到了兩漢時期發展成為穿在墓主人身上的“玉衣”。這樣的葬具一般人自然是用不起的,只有貴族才可以享受。根據連綴玉片所用的金屬不同,可以分為“金縷玉衣”“銀縷玉衣”“銅縷玉衣”。劉勝的玉衣極盡奢華,全長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 金絲約1100克,竇綰的玉衣全長1.72米,共用玉片2160片,金絲約700克。此外,墓葬中還出土了長信宮燈、博山爐等精美文物。
其實,出土文物雖然極為珍貴,但它們並不是滿城漢墓帶給考古工作者的最大驚喜。滿城漢墓的獨特價值在於巨大的陵墓開鑿于山中,並列佔據陵山主峰,符合史籍中“以山為丘”的記載。另外,由於東漢末年諸侯紛爭,漢墓中豐厚的隨葬品成為當時諸侯覬覦的目標。曹操為了籌集軍費,甚至還設定 “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等官方承認的“盜墓官”,造成了漢墓“十室九空”的局面。中山靖王劉勝和竇綰夫婦墓出土遺物儲存完好,未曾被盜掘,全面體現了西漢諸侯王的生活及死後墓葬的規模,是極其難得的實物資料。
中山王墓
歷史上,除了西漢時的中山國,戰國時期也有一箇中山國,其勢力範圍也在河北一帶,被譽為“戰國第八雄”。這個中山國可不簡單,是戰國時期唯一一個由北方少數民族建立而列入《戰國策》的諸侯國。雖然只是一個千乘小國,但它卻能崛起於戰國諸雄之間,屢亡屢興,歷久不衰。閃爍史冊的中山國到底在何處?直到20世紀70年代,真相才逐漸浮出水面。
1977年中山王墓的發掘,把人們尋覓中山國的視線鎖定在滹沱河畔的平山。墓主人是戰國時期中山國第五代國君,他的墓葬未被盜擾,出土了大量前所未見的珍貴文物,特別是“中山三器”—鐵足銅身大鼎、中山王青銅方壺、中山王青銅圓壺。其歷史文獻價值之高、刻制銘篇之長、器物製作之精創下三個世間之最。這三件器物為後人簡單地勾勒出中山國的輪廓。優美流暢、結體獨絕的1123個字,確立了中山國七代君王世系,提到公元前381年以來中山國後期的80年輝煌,卻並未提及鮮虞中山前期的400年篳路藍縷。如果想全面瞭解“戰國第八雄”,可能還需要考古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吧!
北京遺珍
周口店遺址
離開京畿之地河北,一路北上,就回到了我們出發的起點—北京。北京有“3000年建城史,1000年建都史”,但是北京地區的人類文明卻可以追溯到距今70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已經有人類在北京生活,而周口店遺址正是最好的實物見證。
1918年,瑞典人安特生滿懷期待地抵達了位於北京城外50千米的周口店。不久前,他的朋友剛剛在這裡採集了一些碎骨片,這讓身為地質學家、考古學家的安特生興奮不已。周口店果然沒有令他失望,他發現了許多齧齒類動物的化石,豐富的化石資源讓安特生覺察到了這裡可能不簡單。他在日記裡寫道:“我有一種預感,人類祖先的遺骸就躺在那裡,現在唯一的目的,就是找到它。”
在以裴文中、楊鍾健、賈蘭坡、安特生為代表的中外科學家的共同努力下,1926年,周口店出土了古人類牙齒化石和大批脊椎動物的化石,世界第一次為之轟動。其實,更大的驚喜還在後面。1929年12月2日,主持發掘工作的中國考古學家裴文中在猿人洞發現了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1936年,中國考古學家賈蘭坡又在周口店連續發現三個“北京人”頭蓋骨,世界再一次轟動。
可是,當時的中國在歷經帝國主義的掠奪後,已經風雨飄搖。“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更是對我國虎視眈眈,周口店遺址也籠罩在陰霾之下。隨著“七七事變”的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震驚世界的周口店頭蓋骨也被日本人盯上,一些有識之士為了保護這些珍貴的遺產,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1941年,日美關係惡化,為了不讓“北京人”頭蓋骨化石落入日本人手裡,有關方面決定將頭蓋骨化石由美國海軍陸戰隊護送至美國,等待戰爭結束後歸還中國。然而,誰也未曾料想到,駭人聽聞的珍珠港事件爆發,轉移途中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遺失,至今杳無音訊。
儘管“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遺失留下太多的遺憾,但這並不影響周口店遺址在人類進化史研究領域的地位。周口店遺址是目前全世界發現的同時期遺存最為豐富的人類遺址,是數十萬年前的“北京人”、20萬~10萬年前的早期智人以及3萬年前山頂洞人生活的地方。
經過100餘年的考古勘探,周口店遺址已經發現不同時期的各類化石和文化遺物地點27處,出土人類化石200餘件,石器10多萬件,還有大量用火遺蹟及上百種動物化石,是我國乃至全世界重要的人類化石寶庫。正因如此,1987年,周口店遺址正式被世界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第一批世界遺產。
不同於文明時期的遺址,作為舊石器時期遺存的周口店遺址面積並不大。發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龍骨山猿人洞是一處天然巖洞,東西長140米,南北最寬處40米,西部最窄處2米,但是洞內遺存卻十分豐富,有不同時期的堆積層十餘層。每一層相隔幾萬年至幾十萬年。儘管每層堆積最厚不過兩米,但是整理這些遺蹟卻耗費了考古工作者數十年的時間。從1918年至今,周口店遺址考古已經過去了100多個春秋,但是周口店給人們帶來的驚喜還在繼續,有理由期待它再次驚動世界的一刻。
琉璃河遺址
北京的人類文明史可以追溯到數十萬年以前,北京的建城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由於史籍上語焉不詳,讓這座聞名遐邇的古都的身世充滿疑雲。直到一個偶然的機會,北京建城史的謎團才迎來一絲曙光。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華北最大的洋灰公司準備在北京建造一座水泥廠,貸款銀行派經理吳良才去北京房山地區的琉璃河考察。經過一片荒野地時,吳良才發現一塊高地上遍地都是古陶片,獨具慧眼的他撿起一些陶片,找到當時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考古學家蘇秉琦。蘇秉琦一看到這些陶片,就斷定這是商周時期的東西,無奈當時時局動盪,考證之事就被耽擱了。
1962年,已調到北京大學歷史系工作的蘇秉琦在安排學生田野實習時,想起十多年前吳良才給他看過的陶片,就提出讓學生去房山考察,從此拉開琉璃河遺址發掘的大幕。隨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隊(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等多家單位先後對這裡進行了5次大規模發掘工作,延續時間之長、發掘規模之大,在北京考古工作中僅次於周口店遺址。
琉璃河遺址東西長約3.5千米,南北寬約1.5千米,主要包括古城址、墓葬區和居住區三部分,東、西、北面城牆外還發現了護城河遺址,城市內佈局嚴謹,宮殿區、祭祀區等功能區明確,是一處規模較大的西周早期城市遺址。經過考古人員的辛勤工作以及專業研究,認為琉璃河遺址是西周燕國的初都所在地,是北京城的發源地,將北京建城史上溯至3000多年前。這也符合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的記載,周武王滅商後,進行了分封,其中“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孔子的《禮記》講得更具體:武王克商,“封黃帝之後於薊”。武王克商所處的時期,就是3000多年以前。
琉璃河發現的城址遺蹟就是史籍中記載的“燕”。1986年,考古學家在琉璃河發現一座有著4條墓道的西周大墓,出土了眾多精美的器物,其中銅罍和銅盉上有43字相同的長篇銘文,記載周王褒獎太保並“令克侯於燕”,克侯於是治理燕地平定叛亂的事蹟。這兩件器物是為克侯鑄造的,故學界用諸侯克的名字,稱其為克盉、克罍。在這個大墓發掘之前,學界普遍認為1974年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堇鼎記錄了燕國第一代燕侯的相關事件,這位燕侯曾派官員“堇”到宗周給太保送食物,被太保賜貝,於是造寶鼎以紀念這次朝見活動。克盉、克罍的年代明顯早於堇鼎,所以現在一般認為克是第一代燕侯,同時明確了召公封其長子就封的史實,對探索燕國早期歷史具有重要的意義。
金中都
“燕”的建立為北京留下深深的烙印,至今北京還有許多與“燕”相關的地名和歷史,北京北面的山被稱為“燕山”,遼代在北京建立的陪都被稱為“燕京”。遼代時期的北京,正是北京步入快速發展的重要時期。五代十國時期,後晉的統治者石敬瑭將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人,自稱兒皇帝。938年,遼太宗耶律德光將北京也就是當時的幽州擢升為“遼南京”。後來,由女真人建立的金國將遼打敗,佔領了遼的勢力範圍。海陵王完顏亮更是將都城遷到北京,史稱“金中都”。金中都仿照北宋汴京之規制,在遼南京城基礎上擴建。經過相關專家的考證,今天北京的右安門大街、牛街、長椿街至鬧市口一線,就是金中都時的南北通衢。
20世紀80年代,考古工作者對北京房山地區進行考古勘探,在一處大坑中,發現200多塊重達1噸的石塊。這些石塊擺放整齊,並非天然形成,下面必然隱藏著什麼秘密。經過發掘,考古人員發現了兩具石槨。所謂槨,就是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材。這兩具石槨用整塊的漢白玉製成,上面雕刻著精美的龍鳳紋飾。經過考察發現,石槨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和他的皇后。如今,這兩件精美的文物已被收藏於首都博物館。金太祖完顏阿骨打之孫海陵王完顏亮篡位奪取皇權,為了能夠穩固政權,不僅下令遷都,甚至把先祖的陵墓一起搬到了北京。
由於歷史變遷,金中都當年的盛況已漸漸被時間掩埋。不過,20世紀90年代,北京城南一處小區建設時,發現了一座金代的城垣水關遺址。整個遺址為木石結構,全長43.4米,水關以地樁、襯石枋、過水地面石建築而成。現在,只要去北京的遼金城垣遺址博物館走一走,就能感受到當年金中都的恢宏氣勢。
後來,蒙古人建立元帝國,將都城從內蒙古的上都遷到北京,史稱元大都,就是前文提到的“大元三都”之一。
明清時期的北京為後世留下了諸多珍貴遺產,如故宮、天壇、長城、頤和園。如今,這些古蹟早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實,北京還有許多少有人知的“寶貝”,比如,京郊的法海寺,那裡保留了巨幅明代壁畫,筆觸細膩,構圖精巧,共畫人物35個,三五成組,互相呼應,是明代壁畫中的精品,即使在全國範圍內也不多見。位於北京二環內的智化寺,是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整個北京城被列為第一批“國保”的古蹟也不多。智化寺是一個家廟,為什麼一個太監建的家廟能從眾多古蹟中脫穎而出呢?其實,這個太監可不簡單,他就是“攛掇”明英宗御駕親征瓦剌的王振。後來的歷史,大家也都知道了,明代出現了“三朝兩皇帝”的奇特現象。儘管王振在史籍中的口碑不大好,但是他建的家廟卻非常有價值,整個北京城幾乎找不到第二座如此原汁原味的明代建築群。像法海寺、智化寺這樣的“低人氣”珍貴遺址,北京還有許多許多。當然,這需要我們慢慢去尋覓,說不定轉角處就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百科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