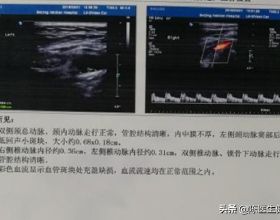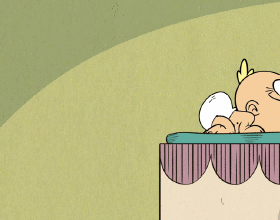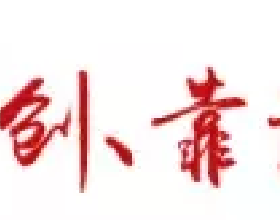寇準和李迪等人,在與劉娥、丁謂間的政鬥失敗後,遭到了殘酷的打擊,丁謂自詡完全掌握了朝政,卻有一人暗中佈置起了反抗丁謂的計劃。
天禧四年閏十二月,王曾找到了遏制丁謂的突破口,樞密副使錢惟演向來敬服王曾,兩人頗有私交,作為吳越國王子出身,錢惟演出身高貴,博學多才,奈何因沒有科舉出身而影響仕途,再加上他與劉皇后義兄劉美的家族結有姻親,導致朝中忌憚他外戚的身份,使其空有才學,只能作為作為劉娥的代言人在朝中立足,如此境遇之下,眼高於頂的錢惟演能得連中三元的王曾結交,自是求之不得,王曾知道若要保護好地位岌岌可危的皇太子趙受益,必須要爭取到劉皇后的支援,而錢惟演的態度必然能影響到劉皇后。王曾對錢惟演說:“如今太子年幼,沒有中宮的支援,地位無法穩固。而中宮如果不依仗太子的法統,又得不到人心歸附。皇后厚待太子,則太子平安,太子平安,他必然也會讓劉氏家族一直平安下去。”錢惟演作為劉皇后的親戚,馬上聽進了這句話,回頭就向劉皇后進行了轉達,我們不知道丁寇間的政爭,讓劉娥對趙受益的態度有何影響,但自從聽得這番話後,他們母子之間的關係,確實愈發親近,由此一場潛在的政治暗流被消弭於無形。
對此情況,感觸最直觀的自然是同在深宮,久病在床的真宗了,他可能並不知道王曾在宮外付出的努力,但是當他看到自己心愛的女人和兒子和睦相處時,也不由得感嘆,並以手詔的方式,對大臣們表達了心聲:“朕近覺微恙發動,四體未得痊和,蓋念太祖、太宗創業艱難,不敢懈怠,憂勞積久,成此疾疹,今皇太子雖至性天賦,而年未及壯,須委文武大臣盡忠翊贊,自今要初之政,可召入內都知會議聞奏,內廷有皇后輔化宣行,庶無憂也。”其後的天禧五年,朝堂終於迴歸了寧靜,丁謂等人專注於迫害王欽若,太子繼續在資善堂豐富學養,而輔佐皇子治政的重任,則肩負在了劉皇后的肩上,和煦的陽光撒在真宗的病體上,讓他感到了久違的靜謐,他錯誤的記憶中,如今和諧的朝堂之外,寇準也正在某個富裕的內地小城中悠然養老,他的國家,他的大臣,他的家庭,他都努力保護了下來,至少他是這麼認為的。
時間來到乾興元年,僅僅一年之後,宋真宗趙恆也終於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後一刻,面對著床榻旁哭泣的文武大臣,年幼的皇太子,還有那個他深愛一生的女人,真宗使出了最後的力氣說到:“皇后所行,造次不違規矩,朕無憂也。” 在人生的最後一刻,他仍在為劉娥鋪路,鞏固她施政的根基,作為人夫,誠無愧也,但作為一個皇帝,他從一個原本與皇位無緣的皇子,陡然成為天下的九五之尊,原本應該說是幸運的,但是當他努力治政了進十年,眼看著將邊境動亂平息,讓百姓生活安定,卻只因一連串天災人禍,就讓他的皇位再度動搖,他又是個何其不幸的人,生在武人時代的尾聲,他曾試圖肩負起這份軍事獨裁者的重任,御駕親征河北,戰略佈局隴西,最後卻因一個無能的將軍和一次意外的暗殺而前功盡棄。
面對命運的惡意,他想要堅守那份責任心,但最終還是被那份無力的空虛感和無盡的疾病所擊垮,他把自己的餘生,都投入到了對內心空虛的彌補之上,在這個士大夫熱衷於思辨的時代,封禪的逼格,早就淪為了野心家肆意玩弄的道具,他真正的危害,乃是讓滿朝大臣都沉浸在了這份慾望之中,太祖太宗兩朝建立的質樸風氣,就這樣逐漸消弭。賢明幹練如王旦、寇準,也沉溺於這份安逸奢靡之間,即使宋真宗還屢屢告誡臣下少用金銀摒棄奢華,這又有什麼用呢?真宗自己早就成為了奢華之風的核心,宋真宗就是這麼個矛盾的人,他堅守對名臣呂端、李沆,寇準,王旦,王曾等人的禮遇,承擔著繁重的政務,完成了國家的治世,但同時他又親近佞臣,沉迷符端,貽誤國事,為了一座玉清昭應宮徒耗民力,觸碰到了暴政的邊緣,他肩負起了一個皇帝大部分的責任,他本有機會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明君,卻因為一本荒唐的天書,而與英主之間隔開了不可逾越的距離,在無限的遺憾中,真宗時代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