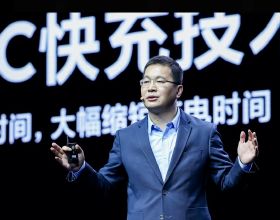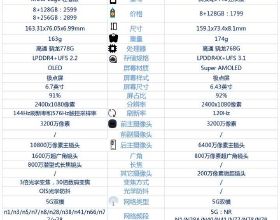巴西是一個神奇的國度,狂歡節和足球運動讓“熱情”成為她的標籤,毒梟和罪犯又使這樣的熱情蘸滿瘋狂,黑道成為她歷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裡幅員遼闊、物產豐富,本該是個富饒的天主之國。
實際上,巴西卻是世界上極端不平等的國家之一,在這個國家,最富裕的六個人掌握的財富幾乎和超過一百萬最貧困人口所擁有的財富一樣多。
巴西曾經的首都里約熱內盧就是這一社會的小型縮影,茨威格曾說:“上帝花了六天時間創造世界,第七天創造了里約熱內盧。”其繁華美麗可見一斑。
這座旖旎繁華的大型城市背後卻有著整個拉美地區最大數量的貧民窟,聞名世界的大黑幫“紅色司令部”長期統轄著這裡。
無地農民的棲息地
貧民窟的起源還要從殖民地時期說起。
十九世紀初期,巴西大莊園主為了擴大其蔗糖和咖啡生產,不斷輸入奴隸充當勞動力。隨後數年,非法輸入的奴隸數量一直在增加,每年至少五萬人。
罪惡的黑奴交易甚至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巴西最盛,里約的奴隸數量比南美洲其他地方的奴隸數量加起來還多。
直到巴拉圭戰爭爆發,為滿足國家的軍事需求,政府不得不向個人和修道院購買奴隸。部分奴隸被招募到軍隊中,他們因此獲得了部分自由,轉變為皇家奴隸或國有奴隸。
這種情況下,奴隸主遭到了強有力的道義打擊,奴隸經濟的破產也在加速進行。
到巴拉圭戰爭結束,奴隸制的危機已經深化,廢奴主義運動的力量日益強大,政府不得不做出讓步。
1871年9月17日,政府頒佈一項法律,宣佈從即日起,女奴隸所生的所有子女將被視作自由民,並設立一項國家預算金,用作向奴隸的主人購買奴隸。
廢除奴隸制的呼聲越來越高,被壓迫的奴隸們為此奮鬥了十餘年,終於在1888年取得最後的勝利。
這年六月,政府通過了法案,宣告在巴西廢除奴隸制,表示與此相違背的一切規定予以取消。
這一法令改變了巴西的整個社會面貌,城市和工業開始快速發展,歐洲移民的收入明顯增加。
這樣的不平衡發展讓巴西直接跳過了土地改革的步驟。
被解放的奴隸雖然獲得了人身自由,但並沒有獲得相應的權力,土地依舊掌握在舊時奴隸主手中,他們很大程度上依舊在為他人勞作。
城市與工業經濟興起後,大量沒有土地的黑人來到城市務工就業,他們活動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聚居在廉租房。
隨著貧民的大量湧入,加之他們的教育水平有限,城市沒能提供相應的就業環境,無業遊民只好自己在城市角落搭建住所。
起先是簡陋的紙板房,條件好些後改成了木板房,久而久之這個角落形成了一種規模,面積逐漸擴大,聚居人口愈來愈多,木板房換成了鋼筋水泥,貧民窟初見雛形。
這裡沒有政府管轄,沒有規則束縛,貧民窟有著一套獨特的執行機制。它就像是繁華城市裡的下水道,兩方相隔很近,面貌卻千差萬別。
這裡的居民也有自己獨特的生存方式,有些人為了溫飽會在城市做著底層工作,有些則靠偷搶維持生計,不論何種方式,人們在此幾乎實現了自給自足,能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
一百多年的歷史發展沒能清繳掉這片區域,反而使它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小社會,職能完善,商場、學校、餐館,應有盡有。
但他們缺少機會、缺少必需品、缺少好的醫療、缺少教育,貧窮在這裡代際相傳,猶如一種詛咒。
黑幫統治的小世界
與貧民窟發展歷史相應的,是巴西黑幫的壯大。
巴西黑幫的前身是一支城市游擊隊,建立之初是為了反對軍人獨裁政權,其成員主要是受過良好教育、屬於城市中產階級的年輕人。
基於幾次遊行抗議無效,一些領袖便認為武裝鬥爭才是從政治上反對軍人政權的唯一途徑。
他們的早期活動主要是搶劫銀行,從軍隊武器庫盜取武器。
之後愈發猖狂,謀殺、綁架之類的案件層出不窮,他們以此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來爭取談判的籌碼,這兩股力量的抗爭持續了數十年。
巴西軍權政府損失很大,這支運動隊伍也不例外,被捕者數不勝數,他們大多被關進格蘭島監獄,與眾多亡命之徒混在一起,這個監獄號稱是里約州最危險的監獄。
文質彬彬的知識分子在這裡就像任人宰割的小綿羊,那些窮兇惡極的罪犯將他們視為發洩工具,欺壓、凌虐、謀殺的事例數不勝數。
知識分子只能抱團取暖、一致對外,漸漸形成高度的紀律性。他們抗議監獄的不公待遇,為自己爭取福利,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這引起了重刑犯頭目的興趣,他決定和這些知識分子合作,成立一個監獄組織。這一組織就是後來的“紅色司令部”,至今仍令人聞風喪膽。
力量壯大後,他們迅速統一了監獄,一些獄警見勢也加入了他們,幫助組織中的幾個大頭目越獄。
他們選擇貧民窟作為自己的大本營,這裡人多,可以發展勢力網,最重要的是此地無人監管,簡直是一處天堂。
販毒、走私軍火、色情交易,他們的犯罪版圖橫跨國際,發展成世界上數一數二的黑幫組織。
被上帝遺忘的上帝之城
貧民窟的一切都在黑幫的掌控之下,沒有規則就是這裡的規則。這裡的人恣意灑脫,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也可以讓這個地方變得更加烏煙瘴氣。
髒亂差的治安環境最易滋生出種種罪惡,貧民窟將這一條理展現得淋漓盡致。
其中,最典型的當屬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據統計,里約共有人口640萬,貧民便佔到了140萬,城中大大小小的貧民窟將近800個。
這座城市的兇殺率常年穩居各大國際城市之首,每十萬人有二十四人死於兇殺,按這個換演算法,若里約的兇殺率為24,居其下位一名的美國則僅為5.1。
警匪衝突,幫派糾紛,毒販猖狂,軍火無制。這裡是罪犯的天堂,連上帝也不願光顧。
“各種各樣的武器,各種各樣的幫派,槍聲在每個清晨響起,一直持續到深夜。”這就是當地人口中的貧民窟,每天都有人被捕入獄,每個人都一問三不知。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算身處這樣的深淵,當地居民卻認同感極強,85%的人不願意離開,94%的人認為自己幸福。
用“魅力”這個詞來形容這一現狀似乎不妥帖,或許電影《上帝之城》可以為人們提供一個參考答案。
這應當是最貼近巴西黑幫、里約貧民窟生活的一部影片,原型都能在歷史上一一對照。
各大幫派勢力錯綜複雜,敵對火拼是常有的事。黑吃黑消滅對手,贏下槍戰的一方獲得一定主動權和管轄權,這時居民們就能收穫短暫的平安。
以暴制暴是這裡維持秩序的唯一有效方式,幫派糾紛中難免有大量無辜者犧牲,有無辜的犧牲就會有不斷的仇恨。
在這裡,善良的普通人有之,更多的則是為保自己和家人平安加入黑幫的人。
整個貧民窟的犯罪勢力交錯盤結,居住者大多已習慣了這種獨特的生活,與其說是對其生活的認同感,不如說是他們的幸福閾值太低。
在我們看來最基本的生命保障卻是他們所追求的最高幸福。
對於罪犯來說,里約的貧民窟是一座被上帝遺忘的上帝之城,對里約這座大城市來說,這個歷史問題有如一顆毒瘤,短時間內奈何不得,但它時刻危害著這座城市的正常執行。
所謂的無政府管轄,不是政府放任其不管,從不作為,而是因為管不住。
警匪之間亦有暗地裡的勾結,有些腐敗警察黑白兩道通吃,兩頭拿錢,賺得盆滿缽滿。如此一來,這顆毒瘤侵害更甚,也愈發無力管治。
值得一說的是巴西兩任總統對貧民窟問題截然不同的兩種整治方案。
前總統盧拉上臺後,曾發表言論說,“如果在我任期結束時,全體巴西人都能夠吃上早餐、午飯和晚飯,我就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使命了。”
“零飢餓計劃”是他提出的第一個重點施政計劃:給貧民窟的居民提供有條件的補貼,一是必須送孩子入學並保持85%的出勤率。
二是他們的孩子必須接受社會公共服務,比如體檢、疫苗等活動。這讓貧民的生活質量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相較於盧拉總統將貧民窟治理的重心放在其居民身上,現任總統博索納羅則更多地將重心放在黑幫身上。
他採取的是以暴制暴的方式,放鬆對槍支彈藥的管制,讓他們黑吃黑。
同時政府加大清剿力度,提出一個“平定貧民窟治亂計劃”,將消滅黑幫組織定為政府的頭號執行任務,名曰“掃毒”。
實施之初,警察每天都在這場活動中殺死大約五個人,死者大部分是有色人種,平均每23人中有1人為誤殺。
理論上說來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應當有效,事實上這隻會讓政府與黑幫勢力陷入一種死迴圈。
政府清繳力度愈大,黑幫的抵抗愈烈,清繳活動讓本聚居於貧民窟的犯罪分子四處流竄,犯罪地點擴大至其他城市,治標不治本,反而讓犯罪勢頭更甚。
時至今日,巴西的高犯罪率依舊同他們的足球一般聞名世界。
黑幫地位更甚當地政府
十分諷刺的是,在巴西貧民窟,黑幫似乎比政府更加“親民”,總統博索納羅不喜歡黑人,更不用說居住在貧民窟的底層人。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發讓政府的不作為體現得淋漓盡致,總統那句“考慮到我曾經是運動員,就算我感染了病毒,我也不會擔心。”更是為人津津樂道的經典笑話。
無視世界衛生組織的防護準則,帶頭拒絕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撤銷掉地方政府頒佈的封鎖令,呼籲人們回自己崗位工作,一系列迷幻操作讓巴西死於新冠的人數位於世界前列。
貧民窟毗鄰富人區,且人口密集,150萬人集中活動在一個極度狹小的區域,如果疫情在此傳播開來,這一小社群將面臨毀滅性的打擊,特別是在沒有足夠醫療幫助的情況下。
政府不重視、不防控,最終竟然是黑幫組織暫停了一切活動,制定了封鎖不得隨意入內的規矩,以遏制新冠病毒在貧民窟的爆發。
“我們需要強制執行封鎖,社群宵禁現在開始實行,我們對此是100%的嚴格要求,所有人不得外出,都留在家裡。我們不想要病毒在社群傳播,我們需要保護我們的社群免受外國佬的感染,盡一切辦法。”
暴力威脅一直是他們的統治法則,黑幫成員開著皮卡車、架著高音喇叭、拿著衝鋒槍在街上巡邏,警告各家各戶關閉門窗,不準隨便上街,不允許人員流動。
政府的無作為使當地居民異常配合黑幫的宵禁令。
此外,因貧民窟裡醫療防護資源極度缺乏,黑幫頭目甚至要將外用酒精或者其他東西勾兌成手部消毒液。
和巴西總統不同,他們更加遵守衛生規則,還免費向居民分發口罩、手套和酒精。
“我們幫助居民,因為現在賣毒品沒有任何好處,居民是貧民窟的心臟。”一位黑幫成員如是說。
對於這裡的居民而言,有組織有紀律的黑幫比不作為不管事的政府好上太多,尤其是在與新冠病毒的抗爭中,二者截然不同的態度讓居民對黑幫更有認同感。
當地人稱他們從來沒依靠過政府的醫院,從來沒指望過國家任何事,政府幾乎不給他們機會,那些高層眼裡只有資本主義,壓根看不到社會中最窮的那批人。
疫情破壞了貧民窟裡自給自足的生態環境,沒有工作,失去了收入,小社群內的買賣就被動陷入停滯,餐館、商店在三月份幾乎都關閉了。
這期間,貧民窟裡的醫用防護用品的支出都是由黑幫支付。
這大概是二十一世紀最魔幻的場景之一,同時也不乏諷刺。巴西政府要何等軟弱不作為,才能讓黑幫組織代發封鎖令,依靠黑道力量最大限度庇護貧民窟居民的生命安全。
道義上說來,黑幫的庇護無法抵消他們視人命如草芥的各種兇殺,也不值得貧民窟居民對此感恩戴德,更不會因此對黑幫改觀。
如他們自己所說,貧民是黑幫的心臟,是他們賴以生存、能為他們創造一定價值的廉價勞動群體,維護貧民窟,就是在維護他們自己的執行資金鍊。
黑幫與貧民窟早已在歷史的洪流中滲透融合,他們既是壓榨與被壓榨,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同樣也是相互依存,相互信賴的關係。
這樣的矛盾讓這個小社會維繫至今,成為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巴西政府顯然沒有黑幫組織覺悟高,屍餐素位的高層不知道民眾是一個國家的基礎,底層人民更是一股不可忽視的特殊力量。
前總統盧拉的治理頗有成效,可惜沒能繼承實施,現總統在他們眼中就是個不願承認的獨裁者,早已失去了公信力,這同樣是這個國度的一大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