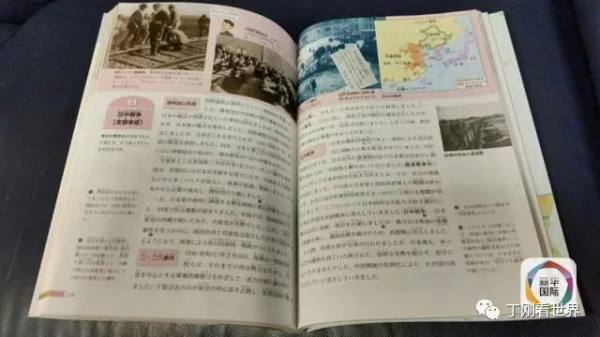荷蘭作家布魯馬曾對兩德合併前的東、西德的教科書做過比較。他說,東德的教科書上印有許多抵抗運動英雄的照片,而在西德的教科書上則印著相當數量的大屠殺照片。有一張照片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照片上有一群穿著鋥亮的皮靴的黨衛軍軍官,他們正在從剛剛運到集中營的猶太人中挑出一些人,送往刑場立即槍決。
在西德中小學的教科書中,有不少有關納粹檔案的詳細介紹,比如1935年透過的種族歧視的法律、一些集中營中的規定、格林或戈培爾的講話等。這些原始檔案無疑會引導學生把自己放進歷史中去反思。
老師的提問著重於幫助學生認識這段歷史的前因後果,知道什麼對、什麼錯、為什麼會錯,錯了怎麼辦,為什麼要有人性之愛、和平之愛。這樣的教育既培養了學生認識錯誤的能力,也讓他們具有了反對錯誤的良心和勇氣。
西德的道德、人性教育在上世紀60年代中出現了一個重大轉變,它以“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特奧多·阿多諾(TheodorW.Adorno)的一次演說為標誌。
1966年4月18日,阿多諾發表了題為“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的演說。阿多諾以“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而聞名於世。他在演講中開門見山地指出,“教育的第一任務是阻止奧斯維辛的重演。”
“奧斯威辛”這個詞,已超越了地名和歷史事件的含義。這個建有毒氣室的集中營成為20世紀種族滅絕主義的象徵。它不僅是一個學術名詞,更意味著人類對歷史苦難、戰爭和人性的重新認識。
奧斯維辛集中營(網路圖片)
阿多諾在演說中提出了兩個領域的教育:一是兒童教育,特別是早期兒童教育;二是普遍的啟蒙。他認為,要〝創建出一種精神的、文化的和社會的氛圍,以阻止奧斯維辛的災難重演,因而在這種氛圍中將會對導向恐怖的那些契機多少有點意識。”
他認為,對抗奧斯維辛定律的唯一真實的力量就是“自律”。他說,“如果允許我用康德的術語來表達的話;也就是反思、自決、不參與的力量。”
正是在這樣的教育原則指導下,西德的一些教師在教學時著重讓學生們認識到,在發生如此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時候,即便是沒有親自參與,無動於衷、袖手旁觀實際上也是一種犯罪。
布魯馬結識的一位女教師對他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她的學校裡有一位老教師,看上去很難相處,總是一付很威嚴的樣子。有一天,有些孩子問起他有關“第三帝國”的事情,他竟突然哭了起來。“我們都是有罪的。”他說,“我們看到了牆上貼著那些要殺盡猶太人的口號標語,卻無動於衷。我們都是有罪的。”
教育的力量是巨大的。
1992年,德國發生了新納粹分子燒燬難民營的事件。全國各地的民眾連續幾天走上街頭,舉行反新納粹燭光大遊行。據統計,當時德國全國有3百多萬人參加了遊行,是全國人口的27%。而在當年納粹影響深重的慕尼黑,幾乎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參加了遊行,其中有許多人都是經歷過二戰的老人。
這次大遊行是全民反思的結果。布魯馬說,它向世界展示了,對納粹有著深刻認識的不只是德國的領導人和專家學者,更是德國的普通民眾。
布魯馬後來到了日本工作,他自然而然地拿德國與日本做比較。他說他曾看過一本許多中學都使用的日本歷史教科書。書中沒有任何有關日本軍人殺戮的照片,而只有廣島遭原子彈炸燬和美國戰艦在珍珠港沉沒的照片。他在一篇專欄文章中一針見血地說:德國人理解二戰的關鍵時刻不在於斯大林格勒戰役還是柏林之戰,而是在於發現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那一刻。日本人的理解則不在於珍珠港或中途島之戰,而是廣島的原子彈。
我從一位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那裡獲得了幾段日本歷史教科書的英譯文。其中第一段引自1998年版的《新社會研究:歷史(新版)》,據說大約41%的日本學校使用了這個課本。
在題為“中日戰爭的開始”的一章中,有這樣一段話(第254頁):“在控制了滿洲之後,日本進入了中國北方。中日戰爭於1937年7月7日因盧溝橋事件爆發。日本與中國軍隊在北京郊區的盧溝橋未經宣戰而發生衝突。戰爭從中國北方擴大到中國中部。這年年底,日軍佔領首都南京。在這個過程中,日本軍隊殺死了大約20萬人,包括婦女與兒童(南京大屠殺)。”
讀完這段話,我不能不為教科書的撰寫者如此用心良苦地選擇用詞而感到震驚。一場由日本侵略者發動的血腥戰爭被寫成了“中日戰爭”。侵略被寫成了“進入”(原文是Advance,意為前進)。“不宣而戰”者究竟是誰,難道還要讓中小學生去猜這個謎嗎?
文中儘管提到了南京大屠殺,可稍稍關注一下有關日本教科書事件報道的人都知道,就是為了這輕描淡寫的一筆。一些有良知的日本教育學家、歷史學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比如,日本教育家、歷史學家家永三郎教授為了將南京大屠殺等暴行寫入教科書,打了32年的官司,他獲得的賠償卻只有3400美元。
家永教授對教科書檢定的起訴被《吉尼斯世界紀錄》認定為“史上歷時最長的民事訴訟”。
新加坡《聯合早報》的特約記者在對日本的中學教科書做了一番考察後說,教科書有關這段歷史的頁數與內容雖有所改善,但這種努力不完全是出自政府。日本文部省對整個侵略戰爭記述的檢定立場基本上變化不大,甚至在背後利用保守輿論或議員做應聲筒,推銷另一套歷史觀。有關的歷史教育因此只能靠部分教師做出個人努力。
《新日本歷史》簡單提到日軍佔領南京,但在註解中寫道:“這個時候,由於日軍導致中國軍民出現了很多的死傷者(南京事件)。對於這一事件犧牲者人數的實際情況,有著各種各樣的見解,現在仍在持續爭論。”(新華社)
從日本的教科書我想到了這幾年從網上看到的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的評論。
最讓我氣憤的並不是那些極右翼分子,因為他們的言詞原本就是混蛋和瘋子的狂言。可怕的是那些以一副專家學者面目出現的討論者,他們似乎並沒有否認這場大屠殺,只是說沒有殺這麼多人,是20萬,或者是10多萬;對於日軍屠殺平民,他們的解釋是,因為中國軍人裝成了老百姓,繼續向日本軍隊襲擊,日軍不得不還擊。他們就像是在認認認真、冷冷靜靜地與你探討一個學術問題!我每每讀到這樣的言論,心中便會掠過一陣陣冷顫。
這絕不是什麼資料之爭,它事關人類對戰爭的認識,事關戰爭中的人性和民族性!
在讀了布魯馬先生的比較和分析之後,我多多少少明白了日本的教育、日本的教科書忽視的是什麼。它忽視的不只是歷史的真實與完整,更是人性的教育,沒有人性與道德的反思,也不會有歷史的真實與完整。
從那些冷靜平淡的描述中,日本的學生怎麼可能把自我放進去思考戰爭呢?又怎麼會對日本民族性中非人道的野蠻性產生深刻反思呢?
近年來,日本也建立了有關納粹大屠殺的展覽和教育中心,其中有一個就建在廣島。我不知道,講述納粹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大屠殺的慘景時,是不是也會多多少少地提及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大屠殺。從網上的介紹看,好像沒有這方面的內容。
不過,我還是查到了這樣一段頗具意味的對話。
有一次,大屠殺的倖存者艾利希博士去那裡訪問,與幾位日本孩子交談。有位14歲的日本小姑娘說她讀過許多介紹安妮日記的書籍,有本書上說,人會變成野獸。他們甚至會像野獸一樣對待自己最親密的朋友。
另一位日本孩子則問她:“在那種環境下,你會不會也成為納粹的追隨者呢?”
艾利希的回答是:“絕對不會,因為我受過良好的熱愛人類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