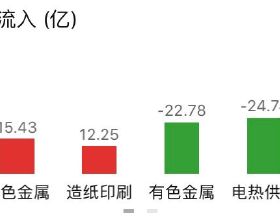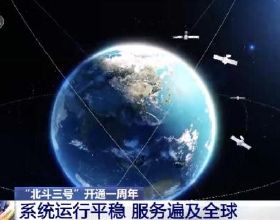大集體時,農村種地主要靠牛,社員們對牛很重視。各個生產隊蓋的牛屋,專職的飼養員,配有飼料,喂好耕牛。
那時吃得緊張,曾有飼養員,將飼料一次往荷包裝幾把,回去人吃。結果,牛喂得皮包骨頭。隊長髮現奇怪,可又沒有一把抓住,只有幾個隊幹部商量後,換人。
耕牛喂得是否膘滿體壯,還是瘦弱無力,關於到田地耕得好壞,糧食的產量。各隊的飼養員,通常都選思想好,責任心,會飼養,沒有私心的人。
我們隊喂有十來頭耕牛,一個腿腳稍微有點殘疾的老飼養員為主,配了一個年輕的飼養員,主要挑水,鍘草,出牛鋪。老飼養員有餵養的經驗和技術,還會保養牛,牛有點小毛病,也會偏方看治,以他為主。
他們兩個除了回家吃飯的時間,睡在牛屋忙活,夜裡起來幾遍,給牛添飼料,中午牛幹活回來,喂牛。不喂牛時間,準備豆料,側牛草,挑水,出牛鋪,墊新土等。一個人餵了好幾頭,要想喂好,忙得人像抽動的陀螺,轉個不停。一頭頭黃牛喂得皮毛水光,體形雄壯。
以前,生產隊的牛屋,在村中間,太小,也有諸多不便。後來在村四五十步的西北角的一長塊平地上,蓋了八九間瓦房牛屋。一間睡飼養員,帶存放飼料,主要磨後的豆料,兩通間放草料及雜物,五六通間喂牛屋帶放牛具、農具,除了飼養員睡著的屋子,其他都是敞門,便於耕牛和農具進去。
每天清晨出工,牛屋門前,一片繁忙、熱鬧的景象。一個個掌鞭的,套上牛,拉上拖子,拖子上放著犁耙,或套上牛車,嘚兒,駕,叭叭的鞭子聲,此起彼伏。吃了一夜料,恢復了體力,精神飽滿的一頭頭耕牛,雄赳赳,氣昂昂,邁出歡快的蹄腳,拉起梨耙或大車,呼呼隆隆地奔向田野。
牛屋是生產隊的第二個活動的公共場所。我們小學生,在牛屋前的空場上,放風箏,抽陀螺,敲木橇,打紙板,推鐵環,抵虻虻牛等遊戲。放寒暑假和農忙假,參加生產隊勞動時,經常到那裡。春夏秋隊上安排我們去牛草,割了一背籠一筐青草,送到牛屋,過秤後,倒成一堆。
隨後,雖在一旁,或吃過飯,跑來看兩個鍘草。鍘草的兩個人,配合默契,一個掐一捆,均勻地往鍘床裡送,一個用力地按下去,半人高的青草,就成火柴棍的草料。有幾個小夥伴覺得好玩,也想試著鍘草,大人不讓,怕鍘到手。
牛屋門前,出牛鋪的糞,還有一家一戶繳上來豬尿糞,堆成小山。經冬發酵後,開春,扒開,冒著熱氣,腐臭氣味,沖人鼻眼。扒開的大塊,用钁頭搗碎,成了很好的黑色農家土。播種時,牛車,板車,人歡馬叫地往田裡送。我們放假的學生,跟著大人們一塊,裝車,推車,拉梢。到了田裡,又卸車。
冬天農閒時,沒有的青草,隊長安排幾個大人和小學生,從稻場麥秸垛、稻草垛,拉來麥草、稻草,幾個大人又鍘成草料。歇歇時,幾個大人侃大山,牛屋又說天南海北異趣趣事的地方。
下雪時,人們用稻草,把幾個窗戶塞嚴,怕寒風灌進牛屋。飼養員和鍘草的大人,又在雜物間生一堆火,一群在外面玩的小夥伴們,凍得鼻涕涎水,一看有火烤,馬上圍上去,湊到火堆旁。可是烤火也不好受。麥秸、稻草,雪天潮溼,點半天才燃著,狼煙大冒,眯得直流眼淚。一旁的牛嚼著稻草,忽閃忽閃的黑圓眼,倒著白沫,偶爾搖晃下碩大的黃頭,鈴鐺響動。乾草料的香味、牛糞的氣息、牛糞的臭味,混合在一塊,瀰漫在牛屋裡。但外面寒風呼嘯,雪花飛舞,只有呆在牛屋。何況小朋友們,都喜歡聽大人說古道今,對他們談論的外部世界和天上仙境充滿了神秘和嚮往。
幾個大人烤著火,用柴棍撥著火,吧唧吧唧抽著旱菸,吞雲吐霧,天南海北地閒聊起來。有個說,分辯是純漢人,看腳小趾頭是否是兩瓣的,兩瓣的都是漢人,不是的,就是少數民族的或混血人。一個人說了一個遇到鬼的事,去年隊上幾個輕人修孟橋川水庫,過年節放假步顛回來,深更半夜,走到後崗坡墳地,突然看到一個女鬼,披頭散髮,灰白的臉,發綠的眼睛,伸著老長的血色舌頭,嚇得幾個失魂喪魂,渾身顫抖,來不及多想,拔腿就跑。還有跑錯路了,離家一兩里路,摸錯路了,天亮才回到,還嚇得害了一場病。我們幾個小學生聽得頭皮發麻,汗毛直豎。一個學生不贊同地反問道,主席說,世上沒鬼,都是人嚇人,還提出要破除牛鬼蛇神。老飼養員打圓場說,信神有神在,不信神不怪吧。存在心裡,不往外說就是了。咱們不談鬼神,就說說其他故事。有個記性好,能說會道的,聽過幾回說書,炒剩飯似說了《三俠五義》、《岳飛傳》等故事片刻,甚至有時朝代、人名弄錯,牛頭不對馬面,小夥伴們也聽得津津有味,只到天黑,只到家家戶戶亮起的燈光,升起了炊煙,大人們高著嗓子喊回家吃飯,才戀戀不捨的回去。
日月如梭,滄海桑田。四十多年過去,生產隊的牛屋早已不復存在,但牛屋印象和它發生的故事,卻鐫刻在了記憶深處。
圖來自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