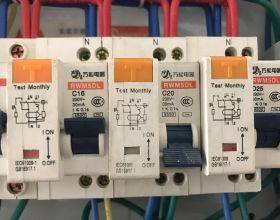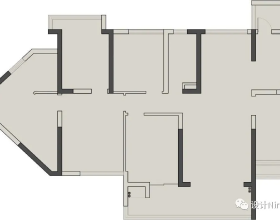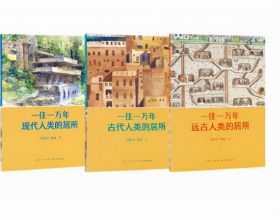1997年,《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版頭條,文章開篇宣告“摩爾定律被打破了”,打破這項著名晶片定律的核心發明人之一,是一位在英特爾總部工作的華人。
他笑稱自己一副“後生相”,認為與其在谷歌的5年經歷密切相關。在谷歌,他和一群“沒有ego(自我),只喜歡做事”的人共事,於是在此後的職業生涯裡,他同樣在追求“心無ego”。
在婉拒谷歌第30號員工的offer、並在之後的三年裡創業失敗後,他找到了一件“喜歡做且願意一直做下去的事”,風險投資。
事情的起點是2003年,5年間,經由他,谷歌投資了百度、大眾點評、趕集網等具有中國第二波網際網路浪潮象徵意義的案例。2007年,他希望再次出手投一家如今的網際網路巨頭,卻被否了。不久後,他萌生了“真正入行”的念頭。
他叫宓群,2008年加入光速,擔任全球合夥人,2011年創辦光速中國,作為早期投資方投過國民皆知的拼多多,投出過除光速中國之外沒有一家美元基金投資的隱形冠軍中際旭創,被投企業小魚在家被百度收購,成為小度在家。
更多的還是像中際旭創這般的to B科技公司,這裡面有“混合雲第一股”青雲科技;估值超過130億元的禾賽科技;還有對自閉症治療有重點突破的優腦銀河,為了投這個專案,宓群動用了“銀彈”——光速中國內部每人每支基金擁有1次銀彈機會,可以投在投決會沒有過的專案。
主要原因是一句定語很長的話,“總要有人投一些絕大多數人認為成功機率很低、但一旦成功就會對社會有很大貢獻的專案。”
最近,光速中國完成了9.2億美金新一期基金募資,也是他們至今募資規模最大的一期。這裡面故事很多,有趣的疑問也很多,我們為此和宓群見了兩次,聊了很久,聊得很慢,他不著急,我們也不著急,他說,“如果一件事情很有趣,那晚一點知道也沒關係”。
主持人:楊曉磊,投中資訊CEO,學習積極份子,投資圈隱形KOL
嘉賓:宓群,光速中國創始合夥人,愛看各種艱深行業論文的硬核投資人
為什麼是9.2,不是10或者12?
楊曉磊:光速中國新基金超募到了9.2億美元。這個有零有整的規模怎麼定的?為什麼不是10億美元或者12億美元?
宓群:規模還是要剋制的,不能跨越性太大。
VC最核心的是人,我把光速中國看成一家創業公司,有10年曆史的創業公司。歸零很重要,如果你總是想著以前投出了點評、拼多多,你是不會有未來的。
我們重點佈局的硬科技和綠色科技,這些都要求投資人對行業非常懂。既懂技術,又懂投資的人才市場上少之又少。我們現在有6位合夥人,都是這一類人。如果我們有更多合夥人,規模可以再擴大一些,但目前還是要剋制。
楊曉磊:比起上一期,規模還是從6億多美元增長到9億多,你說在剋制,但剋制得不太明顯。
宓群:團隊加入了兩位新的合夥人,能力允許我們把盤子做得大一點,所以取了一個折中,9億多美金,不到10億。12億也是能做到的,所以說保持了一定的剋制。
楊曉磊:新基金的投資階段是怎麼設定的?
宓群:剛剛完成募資的是一支早期基金加一支成長期基金,兩個階段各一半;之後還會有一個後期基金。目前我們已經有一支後期基金了,單筆最高投資1億美元。
楊曉磊:你單個案例的投資上限挺高的,這也要求基金夠大。
宓群:對,所以這一期基金,後面還會有後期基金的資金進來,全部加起來肯定超過12億美金了。
楊曉磊:你押注最多的是哪個案例?
宓群:禾賽科技,押了1.4億美金。
楊曉磊:最開始你就這個案例這麼有決心嗎?
宓群:沒有。投的時候還是有風險的,我在全世界這條賽道里挑最好的公司(禾賽),第一筆投了1200萬美金,下一輪融資很多機構看不清,不敢投,我們又放了2000多萬美元領投,LP跟我們一起再投了2000萬美元,共計給它帶了4000多萬美金,把基礎打實了。後來,我們又用後期基金投了1億美金。這也反映了光速的風格:早期投資優秀的團隊、大賽道,後面繼續加持,幫助企業走向全球市場。
楊曉磊:禾賽科技之前,你投資額最大的是什麼案子?
宓群:來也科技,也投了四五千萬美金。
楊曉磊:中間差1億美金。
宓群:對,差的就是後期基金這一筆。
楊曉磊:你給自己制定的單一專案押注最大額度是多少?
宓群:這倒沒有。
楊曉磊:沒有?
宓群:沒有,現在沒有設限。以前沒有後期基金,最多像來也這樣投到4000-5000萬美元,現在錢袋子比以前深了,我們可以投得更多。
要招人,但人多嘴雜
楊曉磊:募了這麼多錢,你的招人壓力一下子就大了。
宓群:要招。不過我希望組織形式是倒金字塔,能獨當一面的人更多一些。為什麼?我們的核心是投早期。早期投得好不是靠“人多”,是要靠“人強”,人多觀點多,但也人多嘴雜,有時反而不容易抓住最核心的東西。
只要投到好公司的早期,即使到C輪的時候大家都去搶額度,我們依然可以拿到足夠的額度。早期投得好,就不會出現好案子額度搶不到的情況。
楊曉磊:所以你需要的那類人,畫像是什麼?
宓群:我們需要有判斷力,對行業非常懂,同時也敢於冒風險的人。投資要看很多綜合的因素,這是最困難的地方。把這些人都找好了,下面的團隊反而不用擔心。年輕人可以慢慢培養起來,也都有機會。
楊曉磊:我經常聽到一句話,對企業家來說,企業往往能成為作品,而投資人似乎很難出作品,投資人在人家的企業裡始終是小股東。而一家投資機構能夠變成一家企業嗎?看起來這是非常難的事。
宓群:是的。對我來說,我早年做企業不算成功,但我非常幸運,為什麼呢?因為做投資恰好是我特別喜歡的一件事,實際上我做投資以後,才意識到(喜歡投資)這件事。創業往往就做一件事,可能成,也可能不成,但是投資可以幫助很多人去成功,你參與的永遠是最先進、前沿的事物。
你可以依據自己的背景,投網際網路,投硬科技,也可以投綠色科技,做喜歡並且擅長的事情。
楊曉磊:所以你沒有“做企業”的執念。
宓群:我覺得沒有。我們是一家小企業,一家創業公司,人不多,但大家又都是很優秀的人,遇到這種工作是很幸運的。
楊曉磊:我懂。之所以跟你談企業,是因為之前和同行交流,人們會覺得光速中國更代表宓群的意志,看起來沒有那麼“機構化”。
宓群: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經過這些年的積累和觀察,我們要以“一家創業公司”的視角去看問題,有一些關鍵的戰略、決策、配置、人,一些不容易做的決定,要有人能夠去承擔。
我從骨子裡是希望能夠有更多的合夥人,現在我們有6位合夥人,長期來講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機構化一定是需要的。
但我必須適應變化,要像創業公司CEO一樣做戰略決策,但同時還要有一個合夥人機制,一起做投資決策,在經濟上有足夠的回報和分享,大家都有動力去做。
楊曉磊:有些大基金有很強的IR團隊,有一個很強的組織在推動工作往前走,但我覺得這是一個標籤問題,AUM到上千億規模的時候,沒有這樣的組織,就上不了那個臺階,這是一個很現實的事。但是我一直沒明白的是,你為什麼不把“這個事”變成“那個事”?
宓群:我覺得你講的有道理。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比如我們最近在招法務負責人,以前用各個外部的律師可能就夠了,但現在覺得需要招,我們沒有IR,現在也在招人民幣IR,這些工作我覺得都要做,我現在的重心就是在招聘。
我也有一個挑戰,如果真成了純粹的管理者、CEO,就會和第一線脫節,這是危險的。所以回答你的問題,我覺得VC永遠不可能做得“太大”,我們現在招的人,招聘前合夥人們都會面試,確保招聘的人都是不太需要管理的,大家都很聰明,很勤奮,能相互配合。
我對自己的要求就是:
考慮戰略、配人,調動團隊積極性,把團隊戰鬥力發揮到極致;
同時也要走在最前面,永遠能看得到第一線;
還要照顧好家庭。
避免成為先烈
楊曉磊:人們常說“投資太早變先烈”。光速設立後期基金,是不是為了降低成為“先烈”的機率?
宓群:我認為避免成為先烈,最重要的是判斷大勢。
我就做過先烈。拒絕谷歌後我創業做了一個雲服務專案,那時候亞馬遜的雲服務都還未問世,自己搭雲服務。當時成本很高,不像現在基礎設施完善,用多少量就花多少錢,所以錢燒得很厲害,那是“真正的先烈”。
我有過這種痛苦,傷疤在那兒。所以,我們會先判斷大趨勢,確定一個時點,爭取在起勢之前先投進去,我們入場的時間在行業拐點之前。這是建立在我們對行業的深刻理解之上,可能是最理想的情況。
楊曉磊:這太難實現了。
宓群:是的,這樣的機會很難抓到,所以稍微早一點也可以。
行業的變化不是任何人能夠完全掌控的,但是大方向不會變。如果一家公司,別人都看不清楚的時候你就認定他是最好的公司,因為種種原因一時半會還沒有起來,我們就用成長期基金再投他一輪。等到拐點來了,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楊曉磊:從這個角度看,你們面對很多早期專案也沒那麼剋制了。比如禾賽,就是一路不剋制地投,而且跑出來了。
宓群:優腦銀河也有點類似。這個專案我們內部爭議非常大,投決會沒有透過,擔心專案成功的機率不高,但我們有銀彈機制,我用了我的銀彈,投資了1000萬美元。
這個專案的診療方式和傳統的醫藥療法不一樣,很跨界。他們運用硬科技,透過核磁共振測腦部血氧訊號,然後做降噪計算,對大腦的200多個功能區做分析,看哪一部分受損,再透過磁刺激的方法精準治療。我自己本科學物理,做晶片,對這些東西有一定的理解和認知。腦的疾病是最難治的,因為大腦有一個屏障,總是把它保護得非常好,使得一般分子進不去,傳統分子藥很難精準觸及。
楊曉磊:你用銀彈的理由,是認為它潛在回報非常高。
宓群:不止。我覺得這個專案如果做成了,會對社會有意義、有突破性的貢獻。透過我們的能力選出這樣的專案,在它最需要的時候支援它,這個過程非常有成就感。
楊曉磊:你很喜歡投增量,這算是很old school的VC理念,投點評和拼多多的時間點,也是在增量市場裡投的。
宓群:點評和拼多多這兩個都是很早投的,是很有成就感。當然其他的案例也有很多,比如來也科技是從天使輪開始投的,禾賽科技是他們開始做鐳射雷達以後的第一輪投的——前面一輪融資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做鐳射雷達。
禾賽的創始人很強,很有學習精神,我花了很多精力去幫助他們,包括飛到國外幫公司打專利官司。陪著公司走過來,現在做到世界第一,這是最有成就感的。
楊曉磊:禾賽、優腦銀河完全是你的風格:跨界、增量。
宓群:但早年行業內像我們這樣做的還不多,比如中際旭創。這家公司已經創業板上市四年多了,目前幾百億市值。大家都知道,北交所要扶持專精特新企業。中際旭創不光是專精特新,它的市場很專,規模特別大,所以能到幾百億市值。
一般人可能沒聽過這家公司,但行業裡的人都知道。八年前公司還很小,它現在是雲資料中心光電細分領域裡的全球絕對龍頭。這個專案沒有一家美元基金參與投資,只有我們投了。用現在的觀點來看,他屬於專精特新裡面的巨人。這個專案是我們八年前投的,在硬科技領域,這也是我們的一個代表專案。
楊曉磊:投早期的VC機構有它的歷史使命,幫助創業者完成早期資金的補給之後,功成身退。但禾賽,你們一直從早期投到後期,很多頂級機構投也投不進去,這樣做是為了賺得更多回報?
宓群:我們的成長基金一半是投我們portfolio裡面的早期公司,還沒跑出來的公司我們會繼續加註,或者在新一輪融資時別的投資人還沒有看懂也不願意投的情況下,我們會再投一輪,這對創業公司幫助很大。
另外一半是投我們A、B輪時錯過了的公司。如果我們覺得標的公司已經屬於行業龍頭,後面很有潛力,我們也會投進去。
後期投資則是另外的考慮。現在中國的這些創新公司已經做到了一個程度,不僅要做中國第一,還要走向世界,禾賽和中際旭創都是很好的例子。我們早期投他們的時候,都還是很小的公司,隨著我們不斷的資金和資源支援,公司都成為了全球市場第一。
楊曉磊:你有沒有覺得北京和上海的VC氣質差別很大?北京VC挺兇猛的,所有人都在搶,搶案子,搶人,上海VC這麼多年觀察下來,普遍感覺比較溫和。你覺得這是城市文化特徵嗎?
宓群:好問題。我在北京住了7年,因為霧霾搬到上海。有一點原因,我覺得北京的基金歷史更長,比如IDG最早就是在北京,大基金組織架構大,人員多,所以內部也有自我淘汰的機制。上海相對來講VC歷史短一點,另外,大家也普遍認為上海的生活更舒服一點,北京呢,交通擁堵很厲害,人很拼,冬天特別冷,所以我覺得稍微有一點你說的這個城市文化的原因,生活環境可能也會影響心態。
楊曉磊:我原來和幾家上海的VC管理人聊,他們都會說比較擅長投B輪,就是在賽道中跑出來排名之後再出手,光速也是這樣嗎?
宓群:我們更多還是投A輪。
楊曉磊:B輪不太經濟?
宓群:實際上是的。現在的B輪其實和A輪的風險區別不大,大家搶得兇,A輪投不到,B輪價格馬上就上來了。當然,好公司你在B輪能夠進去也不錯,儘管估值可能翻倍了,如果是1億美金以內,還是可以投進去的。而且從策略上說,你不但要投到好的公司,還要拿到足夠多的股份。
楊曉磊:這一點上北京和上海的VC有沒有差異?是不是北京的VC對額度的爭奪更積極?
宓群:也不是。我們經常是那種看準了就毫不猶豫的,比如上週五下午五點,我和另外兩個合夥人與CEO坐在一起,聊了一個多小時就決定投了,然後週一上會,馬上籤協議。因為功課都提前做了,我們現在投的不少案子都能拿到20%的持股。
楊曉磊:20%是一次投的額度,還是長期目標。
宓群:理想情況是一次20%,比如我們投的前晨汽車,創始人黃晨東博士是做新能源汽車出身的,之前在蔚來汽車,離開後創業選擇了商用新能源車,先推了兩款新能源輕卡,這個公司我們在公司剛成立時A輪投了1000萬美金,佔20%。現在一年不到,車已經進入市場銷售了,發展得不錯,B輪也已經做完了,目前2億美金估值。
楊曉磊:你會每一輪都繼續追加,追求更高的持股嗎?
宓群:不一定追求更高,但希望能保持20%。
楊曉磊:投錯和錯過,哪一個對你影響比較大?
宓群:肯定是錯過。
楊曉磊:為什麼?
宓群:芒格講過一句話我蠻認同的,他說,你一輩子有十個最大的投資機會,能否成功取決於你是不是比別人有更多的準備,你有準備,就可以重注,而不是把籌碼分散到100個機會里去。機會可能只有十個,但重注得到的回報絕對是遠遠超出其他機會的。
楊曉磊:這種機會你遇到過了嗎?
宓群:拼多多、美團點評,都是賺10億美金以上的,頭條我錯過了,希望禾賽是下一個。
決定走得更遠的關鍵
楊曉磊:你曾經拒絕過谷歌的offer,也錯過了成為谷歌“第30號員工”的機會,後來又回去了,是因為後悔了?
宓群:主要還是機緣。1999年穀歌在一個車庫裡成立——那個時期矽谷很多傳奇的公司都是在車庫裡成立的,恰好那個車庫房子的主人叫蘇珊·沃西基(Susan Wojcicki),是我英特爾團隊裡的同事,現在是YouTube的CEO。她當時加入了谷歌,成為第16號員工。
那時我已經在英特爾做了7年,做晶片設計、EDA,還有市場。谷歌給我offer的時候,我正琢磨著要創業——受矽谷的影響。
跟谷歌兩位創始人談的時候,我們圍著一張乒乓球桌坐,我問起他們,公司的商業模式是什麼,他們說,我們也不知道,可能是企業搜尋,完全不是今天的搜尋廣告。
楊曉磊:一個商業模式是什麼都還不知道的公司,開的Offer很好嗎?
宓群:當時也覺得不好,現在看其實挺好。他們告訴我,谷歌未來會是一個價值60億美金的大公司,我心想“聽起來不太靠譜”,最終還是選擇創業去了。
楊曉磊:幾年後你又改了主意?
宓群: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絡,有次一起吃飯,他們問我,公司做得怎麼樣,我說收入300萬美金。他們又問了一句,一天300萬美金嗎?我心想“這傢伙又在信口開河了”。(笑)
2000年,網際網路泡沫破裂了,整個市場變化很大。我太太畢業去了雅虎,當時雅虎剛剛上市,股票從15元一直漲到200元,又一路跌到了不到10元。谷歌創始人跟我講,谷歌的業務發展非常好,收入資料驚人。我就想,同樣都是創業公司,為什麼別人做得這麼好?當時有點後悔第一次拒絕了他們,最後決定還是去看看。不過那已經是2003年的事情了。
楊曉磊:在谷歌工作有意思嗎?
宓群:是一個挺寶貴的經歷。谷歌的員工在美國都是頂尖的人才,大家都沒有ego,就是單純喜歡這件事。我們組建的中國團隊非常高質量,比如黃崢,他是個與眾不同的人。
2003年的時候,谷歌的中文搜尋做得並不好,而且沒有一個工程師是專職做中文搜尋的。我們2004年就成立了一個6個人的團隊——這些人後來發展得都不錯。黃崢當時是做工程研發的,但經常會來幫忙,還會問我產品怎麼設計。他是一個很好學、很謙虛的人,後來他也是最早離開谷歌去創業的人之一。
在谷歌的經歷,讓我看到高質量的人在一起工作能夠產生什麼樣的化學反應,也能看到最前沿的東西,讓我相信,你真的可以想象未來,然後組織力量,去實現那個未來的願景。某種程度上講,當時我們是走在世界最前沿的,不在行業核心位置上,很難看到這樣的可能性。
楊曉磊:一直“走在世界前沿”不會令人很焦慮嗎?比如,當有新事物出現的時候,你沒有第一個發現,而是聽別人講的,可能就會覺得自己跑慢了。
宓群:我不太會為這種事焦慮。如果這件事很有意思,那晚一點知道也沒有關係。我認為,最重要的始終是成長性思維,而最核心的就是,相信自己有不斷成長的潛力,保持學習、好奇的心態。
讀書的時候,考試有排名,你永遠在跟別人比較,但是這個動力是不夠強的。最強的動力還是好奇心,是發自內心的喜歡。也許我的提高每天只有0.1%,這也沒有關係,只要我在不斷地提高就好了。
楊曉磊:但是很多人無法獨善其身,容易受到環境影響。
宓群:會的。但我認為,這也是能不能走得更遠的關鍵。
如果都是靠比、內卷,情緒很容易受影響,動作也變形。世界這麼大,為什麼非要排出個名次呢?我學過物理、電子工程等很多東西,最重要的是快速學習的能力和思辨能力。現在很多人缺少思辨能力,靠別人說的、或者投行報告,就信以為真了。實際上,真實世界是什麼樣子,需要自己去探索。
楊曉磊:光速招人也這麼苛刻嗎?
宓群:我們非常看重這些點,尤其是成長性思維。比如面試時,你給他一些負面反饋,看看他的反應。很多人下意識的反應是要解釋,要辯解,想體現出自己好的地方。但是厲害的人有成長性思維,他會反思,願意聽反饋。
楊曉磊:錯過張一鳴,你是怎麼反思的?
宓群:當時頭條B輪,張一鳴來跟我聊,聊了一個小時。我當時想的是,媒體行業還是比較傳統,移動網際網路當然有機會,但是做個性化的新聞,如果網際網路媒體巨頭入局,技術上似乎沒有太多壁壘。
我最遺憾的是,當時我沒有感受到張一鳴有這麼強的能力。因為他福建人,說話多少帶著點口音,聊天不是很順暢;我也沒去跟SIG的王瓊、龔挺他們聊——他們是最早投張一鳴的。總之,因為種種因素我沒有真正瞭解張一鳴,他的許多過人之處我沒能看到,所以才在B輪錯過了他。
回過頭看,我覺得張一鳴是個戰略思考深度非常深的人,當時沒有這種感覺,也沒有跟他多聊,這個判斷是失誤的。
楊曉磊:擁有成長型思維能抗衰老嗎?
宓群:我現在頭髮比以前少了些,白頭髮也比以前多了一些(笑),但我覺得年輕更是一種心態:保持好奇心,認同所做之事的價值,是非常開心的事情。我曾經開玩笑說谷歌這幫人看起來都比真實年齡要年輕,就是因為這個。
這些人都非常好奇,能力很強,但又沒什麼ego(自我)。喜歡做事,願意幫助別人,這種人看起來是更“後生相”的。
楊曉磊:現在讓你不剋制地暢想,你覺得未來十年哪些賽道會成為大勢所趨?
宓群:綠色科技一定是未來10年以上的機會——全球性的機會。這個領域對科技,特別是硬科技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在一個增量市場裡,我們會去想哪些是最有價值的、也是最難做的環節,再去找到這樣的團隊,和他們一起成長。
比如我們投的藍晶微生物,透過它的數字化原生平臺,生成了許多合成生物管線,再透過生物合成方式生產出可全降解的塑膠。目前,可降解塑膠技術還是歐美控制的,中國還沒有真正完全做出來。但是藍晶用的合成生物方式,未來有非常大的前景。創始人本科學生物工程,博士學物理,也是跨學科背景,很對我們的路子。
跨學科的創新肯定有風險,但我們覺得一旦支援他做成,對社會的貢獻就會相當大。
楊曉磊:跨學科,需要極強的專業知識,這些知識不會是你本來就知道的吧?
宓群:當然不是,我天生喜歡瞎折騰,很愛看各種行業論文,比如前陣子我看了一篇很有突破性的,關於核聚變的論文,之後也就在找相關的專案。
楊曉磊:很多管理者已經不太有時間跑一線了,我知道你還在自己投,你不想“退居幕後”。
宓群:我大概一天見1—2個創業者,但我會提前篩選。通常情況下,優秀的人不會輕易給你介紹他認識的人,如果是我認可的人介紹的創業者,我肯定會見的。早期投資需要有第一線的感覺。
楊曉磊:時間管理很重要,我有時候遇到一些老闆很暴躁,就想他肯定是昨天沒有睡好。
宓群:對。而且我覺得沒有睡好,對判斷是有影響的。我現在儘量保證8小時睡眠,昨天晚上看《突圍》,剎不住,就睡了7個小時不到。但還是會提醒自己,最重要的是這一天裡,做對最重要的1-2個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