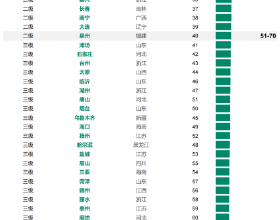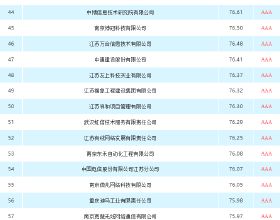這是軍旅作家李鋼林寫下的一篇文章。
這是一個美國士兵對那場戰鬥的描述。
1950年12月,一個苦寒之夜,約翰和他的戰友們在距離鴨綠江僅幾十公里的一個小村莊過夜。
儘管在兩個月前遭到志願軍的迎頭痛擊,狂妄的美國人依然判斷中國人不會全面進攻,他們“只是想在破船上撈點東西”。
士兵們喝著咖啡,聽著將軍們許諾讓他們回家過聖誕節,然後在鴨絨睡袋裡暖暖地進入夢鄉。
突然,夢碎了,槍炮齊鳴,火光沖天,埋伏在村外的志願軍發起了進攻。
約翰扒開鴨絨被堵住的窗戶向外望去,夜空被照明彈照亮,身披白布斗篷的志願軍,組成戰鬥隊形衝鋒。
美國人引以為傲的裝備開火了,像無數的火蛇在原木中穿行。
“…巨大的火球在原木中滾動,他們像僵硬的原木一樣倒下,又有人不斷地從樹林中湧出…”
“…火光中,冰雪在燃燒,大地在燃燒,河水紅了,潔白的冰雪也紅了,他們仍像僵硬的原木在移動…”
半個世紀後,當移居加拿大的老約翰對李鋼林說起這段往事的時候,依然難掩內心的驚駭和恐懼。
那天晚上,約翰和他的連隊被志願軍合圍,僅十幾人逃脫。
那天晚上,全套美軍冬季裝備的約翰,凍掉了七個腳趾。
約翰不知道的是,志願軍的防寒裝備與美軍的差距,甚至超過了武器的差距。
有的戰士在躍起衝鋒之時,竟發現身邊朝夕相處的戰友,已經與冰雪化為一體。
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們依然手持武器,堅定地注視著前方,注視著攻擊發起的方向。
不要哭,眼淚會凍住的。
鐵在燒。
1951年6月的鐵原,註定是兩軍以死相拼的戰場。
在五次戰役中,得勝班師的志願軍突遭美軍機械化部隊反擊,志願軍六十三軍一八八師奉命在鐵原城外的高臺山組織防禦,守衛這個志願軍囤積軍需物資,轉運危重傷員的重鎮。
通往高臺山主陣地的,是一條兩側坡度平緩的山溝,十分利於美軍機械化部隊機動,一旦被突破,將直接威脅大後方。因此,扼守山溝一側207高地的重任,就落到了563團1連2排這支特功排身上。
1連2排的對面之敵,是名聲在外的美騎兵第一師,這支部隊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獨立戰爭時期,雖稱騎兵,但早已是全部機械化,可以說是精銳中的精銳。
美騎一師肩章
更令人心驚肉跳的是範弗裡特,美第八集團軍司令,騎一師的上司,這場機械化追擊戰的直接指揮者。
這是一個唯武器論者,火力至上原則的衛道士,著名的“範弗裡特彈藥量”就是他的“傑作”。
在他的眼裡,沒有什麼是一次火力打擊解決不了的,如果有,就再來一次。
根據美軍條例,24小時內火力支援上限是40次。
但在鐵原,這個數字是250到280次。
207高地,在燒。
一通暴風驟雨般的炮火後,騎一師計程車兵開始向寂靜無聲的207高地進攻。
100米,50米,40米,30米…
就在美國人逼近到20米時,他們的頭頂突然飛來漫天的手榴彈,緊接著就被衝鋒槍成片撂倒,2排戰士們從深深的工事中一躍而出,同剩餘的敵人展開白刃戰。
精銳中的精銳撤了下去,又是一頓暴風驟雨的炮火覆蓋了207高地。
等他們再次抵近到20米之內時,迎接他們的還是手榴彈,衝鋒槍,還有2排戰士的刺刀。
同樣的事情,在1951年6月6日的高臺山207高地,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與團部的通訊中斷了,傷亡人數在激增,但高地依然牢牢地掌握在2排手中。
當2排掩護友鄰部隊突圍撤退後,全排最後8個人也陷入了敵人的重重包圍,彈藥幾乎打光,背後是懸崖絕壁,突圍已不可能。
沒有人膽怯,沒有人驚慌,這8名勇士,在烈焰沖天的陣地上,砸毀了槍支,向敵人甩出最後一顆手雷,然後縱身跳下懸崖。
中國人在此。
關於上甘嶺,我們不知道的,還有太多。
一位軍史研究者,曾經講述過這樣一段歷史。
1952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兩週年紀念日,十五軍四十五師已在上甘嶺經歷了十餘天血戰。軍長秦基偉連夜把保衛軍部的警衛連也派上了前線,派往著名的597.9高地,這是他手中最後的機動兵力了。
而“聯合國軍”方面,恐怖的“範弗裡特彈藥量”被髮揮到了極致,生力軍韓二師取代被四十五師打得氣息奄奄的美七師,大有一口吞掉上甘嶺之勢,戰場形勢萬分危急。
攻擊開始了,氣勢洶洶的敵人向志願軍陣地撲來。突然,槍聲大作,敵人的身後炸開了鍋——一支志願軍小分隊,不知什麼時候潛入敵陣,佔領了一個美軍修築的堡壘。他們非常冷靜,直到敵第二梯隊集結完畢後,才開火猛打。
這個堡壘,就像一根刺,卡在張開血盆大口的“聯合國軍”咽喉,讓它們始終無法吞掉志願軍。
因此,敵人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拔掉這根刺。
一個連的敵人摸上來了,還沒接近,就被潛出堡壘的戰士用手榴彈“熱情招待”了一番;敵人派出一個班抵近偵察,發現沒有什麼動靜,大概是志願軍都犧牲了吧,於是全連大搖大擺地站起身來,孰料三名戰士突然呈戰鬥隊形出現,對著它們一通掃射,該連遂潰。
四十五師師長崔建功在指揮所裡看到了這一切,邊誇戰士們打得好,邊問這是哪支部隊派出的奇兵,一定要給他們記特等功。
然而,沒有人知道。
所有前沿部隊都說沒有小分隊派出。
第二天,敵人在美軍飛機的掩護下再次發起了進攻,火光與硝煙中,五個志願軍戰士的身影在閃動。
是的,只有五個人。
“聯合國軍”做夢也想不到,堡壘中只有五個人。
他們依託敵方工事,用敵方兵器,同數百倍的敵人決死搏殺。
一天,兩天,三天,堡壘中的槍聲始終沒有停歇,直到10月28日,我軍終於突破火力封鎖,衝到了堡壘前。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堡壘外三位烈士的遺體:
一位烈士躺在鴨絨睡袋裡,應該是犧牲較早,被戰友安放的。
第二位烈士身上的棉衣已被炮火撕碎,子彈打穿了他緊握手雷的雙手。
第三位烈士手指上還勾著手榴彈線圈,身旁的敵軍屍體重重疊疊。
走進堡壘,第四位烈士的遺體在堡壘門口,懷抱一根爆破筒。
第五位戰士跪在射擊孔旁,怒目圓睜,手指還扣在機槍扳機上,走近一看,他也已經犧牲了…
後來推測,他們應該是秦基偉派出的警衛連戰士,在連夜進入陣地時由於敵人的轟炸而迷路,誤入敵陣。恰逢美七師和韓二師換防,那座堅固的堡壘其實是一座被放棄的營級指揮部,五位英雄正是這樣潛伏下來,成為紮在敵人咽喉的一根尖刺,而且一紮就是整整四天。
在這四天時間裡,敵人為了拔除這根刺,始終無法將第二梯隊組織起來,投入對我軍坑道的攻擊。
在這四天時間裡,四十五師一口氣緩了過來,為上甘嶺戰役的完全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戰事緊急,無法迎回烈士的遺體,因此沒有人知道這五位英雄的姓名。
只有一句話,英雄們深深地刻在了堡壘的石壁上——
中國人在此!
老約翰至今也想不明白,那個寒冬之夜,那群如原木般移動的志願軍戰士,為什麼要去“選擇死亡”。
正如有的人至今也想不明白——
為什麼裝備精良,後勤充足的“聯合國軍”,會敗在裝備落後,後勤受制,有時甚至連飯都吃不上的志願軍手裡。
他們至今也想不明白——
為什麼207高地上的八位勇士,不撤退,不投降,慷慨悲歌,不為瓦全。
他們至今也想不明白——
為什麼上甘嶺堡壘中的五位英雄,孤身敵後,依然毫不慌亂,智勇雙全,威震敵膽,戰至最後一人。
當然,他們也不會明白黃繼光,不會明白邱少雲,不會明白千千萬萬志願軍先烈。
他們會信口說:黃繼光我不信,邱少雲我不信,犧牲的都是被洗腦的炮灰,這場戰爭中國人失敗了。
我很可憐這種人。
因為他們不能理解,從1949年上溯至1840年,這個國家任人宰割的屈辱。
因為他們不能理解,屈辱之下,這個民族奔騰百年的憤怒。
因為他們不能理解,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先鋒隊的帶領下,終於砸碎枷鎖,走向新生的鼓舞。
因為他們不能理解,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片土地上的這些人,為保衛親人,保衛家園,保衛未來所展現出的覺悟。
“我愛親人和祖國,更愛我的榮譽,我是一名光榮的志願軍戰士。冰雪啊,我決不屈服於你,哪怕是凍死,我也要高傲的聳立在我的陣地上。”
你聽到了嗎?這是烈士最後的告白。
你聽到了嗎?這是志願軍全體將士的吶喊。
他們夢想著終於有一天,同胞不再被人欺侮。
他們夢想著終於有一天,後輩不再歷盡艱苦。
這是偉大的夢想。
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
所以他們爬冰臥雪,他們寧死不屈,他們血戰到底。
這就是他們的偉大斗爭。
這是一場起於鴨綠江,止於三八線的鬥爭。
這是一場智慧、勇氣與血肉之軀,同飛機大炮坦克車的鬥爭。
這是一場初生的共和國,同世界最發達國家的鬥爭。
這是一場中國人取得最終勝利的鬥爭。
這是站起來的中國人,所進行的第一次偉大斗爭。
記住他們吧,也許他們沒有留下姓名,但我們知道他們共同的名字——中國人民志願軍。
銘記於心,實踐於行,踏著先烈的足跡,朝著夢想的方向——
向前,向前,永遠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