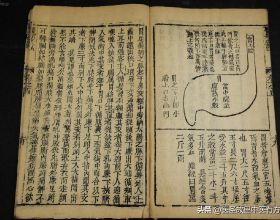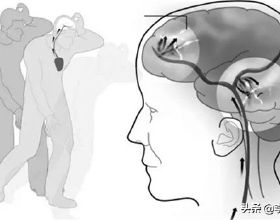突然,我產生了立刻回老家的想法。
老家在農村。從踏入城市的那一刻起,我就開始隱瞞自己的來路。當有人問我老家是什麼地方時,就只說是某某市的。如果還要刨根問底,就說是市區的。這樣做,不是我虛榮,我天生討厭虛榮的人!我是擔心城鄉二元結構下,城裡人對鄉下人那種鄙夷的態度,會給我的工作和生活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羊進了狼群,就得偽裝成狼,還有就是,我認為從考上大學那天起,我就應該算是城市人了。多年的城市生活,也讓我自覺與不自覺地感染上了城市人的那種自以為是的優越感,彷彿中,覺得自己就是天生的城裡人。以至於有時看到那些渾身骯髒、說話粗俗的農民工,不僅沒有同情,反而感到噁心,一臉鄙夷的神色。現在我不得不自曝家門,說出我卑微的出生,是為了讓這個故事不至於因為背景虛假,而有失真實。所有的故事都離不開特定的背景,就象魚兒離不開水一樣,離開了就沒了生命。因為這個故事發在我的老家農村,與我有關。
事實上,自進入城市以來,我就很少回過老家。不是因為忙。忙事藉口,是因為我已經習慣了城市的生活,對城市產生了極大的依賴,對農村那種交通不便、環境骯髒、生活枯燥等狀況已很難適應,就象我的父母不適應城市生活一樣。所以,沒有非回去不可的理由,我是不會回去的,雖然我在城市無權無錢,混得落魄猥瑣。其實,就算我回去了,也不會象當年考上大學那樣,讓父母有光宗耀祖的良好感覺了,還不如那些沒有讀過書,卻跑到城裡混得人模狗樣的兒時夥伴。他們開著高階轎車,帶很多東西送給左鄰右舍,幾萬幾萬地捐錢給村裡修路建廟什麼的,讓鄉親們感激得淚流滿面,風光澤及前代後世。我回不回老家,回去多少次,父母已不在乎。鄉親們早把我忘了。我對老家的感情好象反覆水洗過的衣服,已淡得看不出本色了。
每次打電話回家,還沒等我把編好的理由說完,父親就說:“忙就不要回來了!”並立即掛了電話。
突然產生回老家的想法,是因為那天參加一個會議時,看到一本雜誌上的一段話。當時,領導長篇大論地在上面講要如何如何重視人才什麼的,很無聊,又不敢打瞌睡,就順手抓了別人一本雜誌來看。結果就看到下面這句話:
“女人每個年齡段都應該有那個年齡段的事做,十三歲,應該有初戀的經歷,十九歲,應該有性愛的體驗,三十歲,應該紅杏出牆。要不到了更年期,想出牆誰要啊?”
這句話是小說中一個男人對一個有婦之夫說的,目的是想讓女人為他“對外開放”。說的是80後年輕人的事。我四十出頭的人了,出生在一個思想保守,談性色變或自感骯髒羞恥的時代,應該不會有那樣的經歷。但恰恰相反,因為我初戀時還不到十三歲,竟比80後的還早。這句話,應該叫句屁話,竟突然讓我產生了想回老家的強烈願望。
我想回老家去尋找桃子。
很多年都沒想起桃子了。桃子就像條魚,隨時間的流水不知不覺已從我生命的河床流走,幾乎沒留下任何痕跡。
桃子和我同村,小學到初中,都在一個學校。那時的桃子名如其人,吃粗糧、穿粗布,面板卻象城裡人一樣,白裡透紅,水嫩光滑,水蜜桃一樣,橫看豎看都不象農村的女孩。桃子和我上下學有一段同路。每次到校和回家,我都會在開始同路的地方等她。每次我都走在桃子的後面,走了幾年,我和桃子話都很少說,甚至也忽略了她是女兒身。有一次,應該是春天吧,油菜花已開始稀稀拉拉的開放。桃子穿了一件藍底白花的衣服,像一隻美麗的蝴蝶。午飯後,我們一起去學校。翻到坡頂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樹林裡哼啊直叫,象在打架。我和桃子尋聲而去,結果看到一男一女赤條條交織在一起,旁若無人,不停地扭動。桃子見了,立馬扭頭就走,走時扯了一下我的衣角。我回過神來,立即跟了上去。路上,桃子一言不發,背後烏黑的辮子在花衣服上,合著我腦子裡剛留下的畫面不停跳躍。
“桃子。”我喊。桃子沒應,象沒聽見。
“桃子。”我加大了聲音。
“啥事?”桃子愣了我一眼。
“他們在幹啥呀?”我問,聲音小得如蚊子叫喚。
“流氓!”桃子目光象兩把匕首,狠狠戳在我的臉上。
我低下頭,不敢看桃子。見桃子的腳動了,就移腳跟上,直到學校。
自那事以後,我開始意識到桃子是女人,並在心裡把她當成了自己的女人。那時我才九歲。直到現在也說不清,那叫不叫愛情。後來我才知道那叫暗戀。暗戀叫不叫愛情?愛情專家們沒說過。
我開始默默注意起桃子,包括她的衣服和髮辮。依然每天跟在她身後,只是不敢再像過去那樣近了。
剛上初中,桃子看起來就像大姑娘了,胸鼓起來,像兔子,隨時要蹦出來,出落得讓人直噎口水。上數學的那個男老師寫黑板頭都扭在後面,直勾勾地看著桃子,我恨不得想偷偷地給他一石子,打他個滿臉青包。
初二的時候,桃子突然不讀書了。公社成立了個劇團,招人,演戲,發工資。但不是哪個都可以去,必須是幹部子女,桃子爸是村支部書記,大小也算個幹部,有資格。桃子爸請公社革委會書記喝了一臺,就進去了。
桃子離開後,學校就像
沒有果子的果園,對我突然失去了吸引力。我經常逃課,跑去看桃子排戲演戲。那時我想,要是我可以進劇團就好了,那樣就可以經常和桃子在一起,甚至扮演夫妻。
愛上一個人,就等於做了那個人的奴隸。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桃子,天天都受著見不到桃子的折磨,成績也一落千丈。
有一天,我跑到劇團,鼓足勇氣對桃子說:“桃子,我喜歡你,想和你耍朋友。”
桃子哈哈大笑,差點喘不過氣來。好不容易止住笑,說:“耍朋友,和你?!”
我點點頭,臉滾燙髮燒。
“三娃,快來!”桃子喊。話音剛落,一個長得白白淨淨個子高高的小子,像突然從地裡冒出來的一截木頭,一下子就杵在了我的面前。
“他說要和我耍朋友。”桃子指著我說。說完,又笑,笑得腰都直不起來。我開始後悔,恨不得把腦袋埋進褲襠。
高個子看著我,眼珠睜得像牛卵子,惡狠狠地朝我揮了幾下拳頭,嚇得我渾身篩糠似地發抖。
最後,桃子挽著高個子的手腕走了。走時,烏亮的麻花辮子往後一甩,把我甩在原地,久久沒動。
我不知道是怎麼離開的。
後來我打聽到,高個子是公社革委會書記的兒子,在縣城百貨公司工作。也明白了桃子取笑我原因。
我恨自己不是城市人!恨桃子狗眼看人低!我發誓要努力讀書走出農村!我相信,總有一天,桃子會主動回到我身邊,對我說她愛我。
我哪裡知道,恰恰是我考上了大學,才徹底葬送了我對桃子的渴望。到了大城市,到了大學,看到那些花枝招展的女生,才貌雙全,我才知道桃子根本就不算什麼。她美麗,可美麗在農村有什麼用?就像金子,埋在土裡,永遠都沒人發現,連表面的泥土都不如!我對年少無知的幼稚想法和沒見過大世面的舉動嗤之一笑,也把和桃子的事情丟進了吹往過去的風裡。
幾年前的夏天,有個也考上了大學的初中同學來,閒聊中說起了桃子。說劇團在我們考上大學次年就解散了,人員哪裡來就哪裡去,桃子回到了農村。不久,高個子找了個城裡的女孩,就把桃子甩了。桃子又哭又鬧,說什麼都給他了,死活都是他的人。結果被高個子叫人狠狠打了一頓,還威脅她說,再鬧,就在她臉上劃幾了條口子。我大二的時候,桃子嫁給了一個個子矮矮、身體結實的屠戶。同學不知道我和桃子的事。我聽了,也彷彿是在聽與我無關的事,居然什麼感覺都沒有。
“回來有啥事嗎?”父親問我。
“沒事,來看看你們。”我不好對父母說回來是為了桃子。
父母見了我還是過去回來時那種表情,不鹹不淡。鄉親們見了最多也還是“回來啦”幾個字,一句多的話也沒有,和我對城市裡那些下苦力的農村人的態度一樣。
我不在意父母和鄉親們的冷漠。這種態度我在城市裡早就領教過了。冷漠是城市的一大特色,只是沒想到,自古就淳樸熱心的農村接受這種為人的態度這麼快!好在我已習慣被人漠視和漠視別人,根本不會在意。當漠視別人和被別人漠視已成習慣,也就自然了,自然了也就習慣了!習慣是不分好壞和是非的,要是你突然對人熱情或是別人突然對你熱情,會把人嚇著的,誰都會感到不自在。養成被漠視的習慣,最初的原因來自我老婆大人和她的家庭。大學畢業後,我有幸留在了城市。由於桃子的緣故,我決心要找一個城市出生的女孩結婚,因為我有大學文憑和還算英俊的長相。那時大學生不多,比較吃香,不像現在,哪個旮旮角角都是,就像被扔掉的冰激凌包裝紙,一文不值。很快,老婆和她的父親就看上了我。老婆的父親是我們單位的一把手,但她長相一般,我很猶豫。幾個想討好領導的“黃道婆”(我一直認為女人要評職稱的話,應該有三個:初級—黃花閨女;中級—黃臉婆;高階—黃道婆,只能紡紡棉花而已。當然,這是玩笑話,現在只要是女的都稱美女了)就勸我,說,領導看上你是你的造化,我們想攀都攀不上呢!還曉之以利害,說要是不答應,領導不高興,你在單位怎麼混?答應了,你的前途就一片光明。她們說的真在理,後來,當領導親自找我說的時候,我想都沒想就同意了,還發自內心地說了一句“謝謝!謝謝!”
婚後的日子不是想象中的那樣順溜。老婆始終自視高人一等,家裡,什麼事都她說了算,動不動就說我農民,老土。外面,不管當著誰,也對我指手劃腳的,從不給我面子。她爸因經濟問題出事後,更是變本加厲,甚至還說我是黴星,要是不嫁給我她爸就不會出事。我反駁,她就又哭又鬧,叫著要離婚,還抓著什麼摔什麼,典型的竭斯底裡!為了兒子不受到傷害,我忍氣吞聲。心想,人一輩子,真正為自己而活的有幾人?慢慢地我就習慣了她的橫蠻無理了,什麼事都不與她一般見識,她做什麼我都不問不理,就算她幾天不回家,我也懶得去問,只要她不鬧就行了。我感覺很累。累了好啊,累了就麻木了,就不想再追求什麼了,就象一頭被逼迫狂奔幾百裡的馬,跑不動了,就不想跑了,就什麼也不在乎了,只求能好好喘喘氣,歇息歇息,你罵也好,抽也好,都無所謂了。
我突然發覺想找桃子的原因,不僅僅是那句屁話。真正的原因,應該與我在城市經歷的生活有關。桃子不惜一切地想進城,卻被城市無情拋棄,我進了城,卻始終沒被城市接納。被遺棄是不是我和桃子相同的命運?
我問父親,知不知道桃子現在的情況。
“什麼桃子?”父親說。
“當年支部書記那個小女兒?”
“哪個書記?”
“以前我們村的。”
“不曉得。”父親木訥了半天說。
我突然發現父親真的老了,這些事都記不得了。心裡不禁為沒有多回來看望父母感到內疚起來。人啦!不管你在外受了多大的委屈和傷害,是討口要飯還是揮金如土,都應該抽時間常回家看看老人才對。
我決定自己去找尋桃子。桃子就在本地,應該很容易找到。
我終於打聽到了桃子嫁去的地方,叫楊樹村,離我們村十來裡地。
“桃子住什麼地方?”我問一個在田間勞作的婦人。
“什麼桃子?秋天,有什麼桃子?”婦人怪怪地看著我。
“是人的名字。”我說。
“我們這裡有叫桃子的嗎?”婦人問另一個婦人。
“沒有啊。”被問的婦人搖搖頭。
“李阿桃。”我突然想起桃子的姓。
“你說的是李癲婆吧?”婦人說。
“她在嗎?”我問。
“早就不在我們這裡了,嫁過來半年不到,就癲了,聽說是被男人甩了,氣癲的,癲了就跑了,前幾年有人說在縣城看到她,光著身子在大街上走,估計早就死啦。”
我沒有再問下去。回到家裡,我默默地陪父親喝了幾杯白酒,心不在焉地說了很多關心父母身體的話。
第二天,我啟程返回。到縣城車站轉車的時候,我看到一個瘋癲的婦人,衣衫破爛,雙乳外露,渾身汙黑。很多男人直盯盯地看著她,一臉怪笑。癲婆看到我,突然撲過來,一把抱住我,撕心裂肺地不斷叫著:“三娃、三娃——”
圍觀的人群哈哈大笑。為擺脫窘迫,我急忙把她推開。然後,撒腿就向車站裡奔去。
途中,我一直在想,她會不會就是桃子?可想了半天,也沒想起她究竟是什麼模樣。
回到居住的城市已是兩天後的下午了。到家的時候,老婆不在。家裡亂七八糟的,像被盜竊過一樣。打老婆手機,一個說普通話的女人回答說:“對不起,你所呼叫的號碼不存在。”反覆撥,一樣地回答。
鄰居告訴我:“你老婆前幾天搬走了。”
“為什麼?”我問。
“為什麼?你真不知道啊,你老婆十年前就和一個有錢的男人好上了!”
十年?老婆不就三十歲嗎?!難道真應了那句屁話?
晚上,我破天荒地去了酒吧。酒吧老闆是個女的,四十歲左右,頗有氣質和豐韻,看上去有些面熟。
我問她:怎麼取名叫“桃子酒吧?”
“我叫桃子。”她說。
我給她說了我和桃子的故事,問:“你認識桃子嗎?”
“不認識。”桃子盯了我好一會,說,“我是本地長大的。”說完,就走了。直到我離開,也沒再見到她的影子。
回家的路上,我不禁又想起那句屁話。一陣夜風吹來,忘記什麼叫流淚的眼睛突然嘩嘩譁流出了液體,眼前一片模糊。
我不知道,那玩意兒還該不該叫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