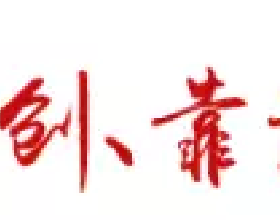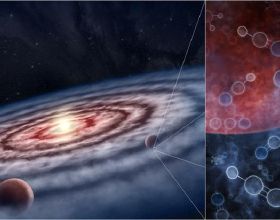人們譴責惡行,是因為兩層原因:
第一層原因——出於一種難以遏制的本能反應。
即所謂下意識的報復,無理性的打擊。這一層反應根本不是思考的結果,而僅僅是如同膝跳反應一樣的自動過程。
無緣無故,就是感到心中有一團火,不吐不快,於是一吐為快。
但是,如果你站在一個超然立場去看,你就會發現人的這種不可自控的自動反應雖然沒有正確的反映人的意志,但卻巧妙的、曲折的反映了“人類的設計師”的意志。
就好像人類的設計者因為要控制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結構,而有意在人類身上設計的一種人類自己無法反抗的自動機制。一種嵌入系統底層,人類的顯意識作為作業系統的應用層無法真正干預、無法自行關閉、無法隔離、無法令其睡眠的強力底層機制。
你將不能靠自我教育真正學會對同類的悲慘遭遇無動於衷,你將不能靠個人意志避免在對同類施加迫害時沾染心理疾病,你將不能忍耐某些現象,哪怕有無數的典籍和宣傳告訴你這是合法的、有正當程式的、甚至是十足正義的。
因為這種反應極其原始,它經常被誤觸,甚至可以說在大多數時刻他如同原始的滑膛槍那樣沒有準頭、屢傷無辜、出乖露醜,令人飽受其擾。
但是,真正到了最後的關頭,它卻是一切暴政最終也無法對抗和閹除的最終防線。
它才是最早而且也是最終的惡行譴責者,在這一層裡,人類只是一個肉體揚聲器罷了。
而對於人類,因為實際上無法干預它的運轉,也就無從去從自己身上找原因了。
當然,你也可以非常“尼采”的把這看作“自然進化遺留的人類尚未達成完全自我控制的殘留”,立志總有一天完全將之納入顯意識的統治之下。
但是你要記住——顯意識是非常懦弱、貪婪、傲慢、片面於是最終本質愚蠢的東西。那個你控制不住的本能要比它勇敢/頑固得多。
人的顯意識,其實是富貴能淫、貧賤能移、威武能屈的東西。它只是善於組織語言打動陪審團。你把那點最終的控制權交給它,那麼將來統治者只要足夠有錢、足夠狠辣,將再也沒有人會有無法遏制、寧可面對死亡也不能不表達的憤怒可言了。
你要知道,世間無數的孜孜不倦慷慨赴難的仁人義士在面對恐怖之時都曾經面對過富貴之淫、貧賤之移、威武之屈,他們都不傻,他們的理智絕沒有天真到認為自己可以造反當上皇帝最後一本萬利。
他們只是做不到用理智的計算壓抑自己沸騰的本能痛苦,不能不做一些事情去讓這種痛苦好過一些。理智的說,除了這種無法自控的痛苦,僅僅從個人收益上說,他們實在是不該去走那些拋頭顱撒熱血的事情的。
出於這個原因,我們現在這些活著的人都有一個額外的理由去原諒出於本能衝動而亂放槍的年輕人——因為這種“誤傷”和那個最終保證我們不會長期被暴政統治的機制是一體兩面的。
我說原諒,不是指放縱,不是指不去提醒,不對其造成的損害追索賠償。(其實原諒本來也不包含這些東西,那只是東亞的糊塗“原諒觀”自以為一定要包含在原諒裡的必備件,這是另一個問題,不展開)。
我說原諒,是指最終心裡對之存一份柔軟。如同對待失意縱酒的老超人一樣——過去他拯救過人類,將來還要指望他拯救人類。
第二層——出於人類對暴力的信奉。
人類是本能的暴力信奉者,這個是沒有什麼可辯解的餘地的。
我們來不妨做個小思想實驗,一探究竟——
你們想過嗎?事實上我們的一切公共政策都可以採用“獎勵做得好的人”的方式,而不用“懲罰做得不好的人”的方式。
但我們極少會真的去探討權衡這種選擇,而會徑直去選擇後者。
我可以直接預言——在評論區裡遲早要出現對“這裡還存在選擇”這個說法本身嗤之以鼻的人,而且還為數不少。
其實,前者遠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昂貴和無效。不過,這不是這個測試的重點。
重點是,絕大多數人都不是經過嚴格的思考和演算而推出前者無效,而是聽到都會大吃一驚——這太荒唐了吧?這怎麼可能?
要注意,我在談論的根本不是這兩個政策到底誰更優,而是絕大多數人是如何排除前者的——要說服他們使用後者,何時需要過嚴謹的計算?
我們不假思索的總是選“罰惡”而不選“獎善”,其實已經告知了我們的這種盤算,也就正是我們為什麼會故意仍要用攻擊性的威懾去震懾客觀上作出危害群體的舉動——哪怕科學研究表明其實這些行為背後最終並無主觀可追究的動機。
因為我們相信這樣會“有效”。一代一代“治亂世用重典”的王朝在人的面前轟然倒塌,也沒有辦法動搖人的這種相信——人們如何總結這些崩潰?——“那是因為他們重典用得太晚,用得太窄,用得太軟”。
也因為我們“無法想象”它可能其實是無效的。極少有人會去仔仔細細的想一想這些暴力是不是真的是有效的,有沒有可能是暴力竊取了別的什麼因素的護國之功。
會不會世界其實是依靠別的力量維持的,暴力只是自稱那是它的功勞?
你真的想過這種可能性嗎?你否決這種可能性的論證,你有仔仔細細的想過它自身是否足夠嚴謹嗎?還是不拘如何,略略一打眼,你就快速的“用腳趾頭想也知道這是對的”,然後蓋上了“我就知道是這樣”的大印了?
腳趾頭畢竟不是思想器官。雖然你天天用它決定各種事,但請相信,它真的不是思想器官。
我去,這句話又會有很多人要用腳趾頭來想。
很多人都在問,什麼是愛?
這裡其實有一個簡單的判定法——在否決愛的選擇時,人有沒有殫精竭慮的去為它算、有沒有竭盡全力的去為它每一點哪怕虛無縹緲的可能性去爭取、有沒有毋寧賭上一些真實的付出去賭那算不出來的因果最終的結果會是正面。
這就是愛心。
人為什麼在成熟到能基本控制本能衝動之後、仍然定義要用譴責的方式嘗試抑制問題?
因為我們都愛心有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