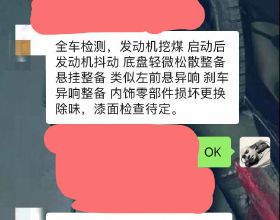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策劃、製圖| 木子童
題圖 |《博物館奇妙夜》
本文首發於虎嗅年輕內容公眾號“那個NG”(ID:huxiu4youth)。在這裡,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態度。
人類的好奇能有多值錢?
世界上五花八門的博物館就是答案。
儘管大多數人印象裡,博物館是國博、市博或者故宮博物院那樣,嚴肅端方、品類齊全的地方。
但不可否認,自從1917年,馬塞爾·杜尚把隨手從商店買來的男用小便池擺上展臺,並命名為《泉》後,就再也沒有什麼能阻止任何奇怪的東西成為一件展品。
心跳聲可以組成心跳博物館、魔法書可以組成黑魔法博物館,就連中世紀狗狗的項圈,也可以組成狗項圈博物館——這些展品本身並不值錢,但因為有人好奇,就有了非同尋常的價值。
如果說,一座綜合博物館是一個城市的名片,那麼一座小眾博物館,則是一個人的志趣所向。
本期虎扯電臺,幾位主播聊了聊,我們去過的小眾奇妙博物館,以及博物館理想的模樣。
去過這些怪奇博物館,才知道人類的好奇有多值錢
vol. 173
主播:黃瓜汽水、木子童、劉喜奔、說說
錄製、剪輯:CC
譬如“失戀博物館”——曾經紅極一時,如今門庭冷落。
2016年,中國第一家失戀博物館在南京開業時盛況空前,一年要接收數萬參觀人次。然而不過短短3年,就因入不敷出徹底閉館。
還在生存線上苦苦掙扎的北京失戀博物館,79塊一張門票,附贈隔壁“減壓博物館”和“星空藝術館”,仍然來客寥寥。

@說說對此早有預料。在她看來,國內的“失戀博物館”,只是對薩格勒布博物館的一次拙劣仿效。
坐落在克羅埃西亞的薩格勒布博物館,由往日戀人歐琳卡和德拉仁攜手創立,是世界上第一家“失戀博物館”,由於主題新穎,2011年曾被歐洲博物館年授予“歐洲最有創意博物館獎”。
薩格勒布博物館的藏品完全配得上它的名聲,幾乎每一件看似普通的物品背後,都藏著一段悱惻的情殤。
一把雕花繁複的鑰匙狀開瓶器,見證了一位斯洛維尼亞女性長達10年的悲劇愛情。她在解說中道:“你說愛我,每天給我送小禮物,這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一把開啟心房的鑰匙。但是你卻又把頭轉開,不願和我睡覺。直到你死於艾滋病,我才明白你愛我有多深。”
另一把來自德國女士捐贈的斧頭,則是她走出失戀陰影的助手——每天用這把斧頭劈碎一件前任的傢俱,“越劈,我的沮喪就越少。就這樣,我把這把斧子變成了為療傷工具。”
沒有過多的刻奇表達,也沒有故作深沉的憂鬱,薩格勒布博物館將每一段經歷平鋪直敘,任人體嘗。
而國內恰恰相反,大概是短時間內專案批次上馬的緣故——最多時,單南京一地就有十幾家失戀博物館同時營業——藏品粗糙簡陋、故事胡編亂造,四壁貼滿好似QQ空間摘抄筆記的短句,釋放360度環繞按頭型emo。

這正是當下各類網紅博物館、網紅展覽的通病。看似高深莫測,實則討巧單薄。
@黃瓜汽水不喜歡這種“ins型博物館”,一場看下來,吃撐了相機,餓壞了自己。
就像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性博物館”之旅,原本期待在這家全球第一所性主題博物館中,看到一些全新的知識,沒想到“跟小商鋪一樣,門口就是一個大媽在那收錢,把錢一交,進去之後發現特別讓人失望。”
儘管每年要接待超50萬遊客,但這裡並沒有考據嚴謹的系統性知識介紹,只有各種與性相關的雕塑、繪畫元素雜亂堆疊,以及大量適宜拍照打卡的人造景觀。
除了博物館二樓那座供人合影的1.8米男性象徵,以及門迎處偽裝成風衣暴露狂的電動人偶,幾乎沒有給她留下任何可資記憶之處。
@劉喜奔認為,再先鋒前衛的博物館或展覽,也該遵循一個原則——讓人搞懂你在幹什麼。
畢竟大多數人去到博物館,可不是為了走馬觀花,而是真的希望學到點兒東西。
“如果去國博看展,你能知道當時的人穿什麼、用什麼、怎麼生活,但你如果是幾百年後的人,回來看我們當代的網紅展,你會發現什麼都搞不明白。”
日本東京目黑川旁的“目黑寄生蟲館”,在講解的明晰性上堪稱榜樣。
作為全球唯一一家寄生蟲博物館,它的藏品,隨便拎出一件就足以讓人渾身爬滿雞皮。
一樓300多件福爾馬林浸泡的慘白標本,每一件都是寄生蟲與被寄生者的一屍兩命。更可怕的是,每一個展品旁邊,都有詳細的配圖講解,告訴你寄生蟲們究竟如何完成寄生。
單看標本,你或許以為螃蟹只是肚臍上冒出了一坨小小的增生。
但配合一旁的講解你會發現,代表寄生蟲的紅線早已侵佔螃蟹全身,把它的身體掏空。
生怕標本不夠生動,展覽旁還配備了幾塊滾動播放的顯示屏,專門用來展示寄生的動態效果。螢幕裡被寄生的蝸牛,兩隻纖細的觸角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寄生蟲偽裝的粗大觸角在頻頻扭動——這是寄生蟲的多級寄生策略,在寄生蝸牛後,它將自己的身體偽裝成誘人的蟲子,吸引鳥兒來捕食,從而得以經消化道進一步寄生在鳥類身上。
被寄生的蝸牛,蠕動部分為寄生蟲
展示鎮館之寶“8.8米長完整日本海裂頭絛蟲”時,館方更是別出心裁。由於人體排出完整絛蟲極為不易,為了讓參觀者感受到8.8米的震撼,館方特別在展品旁準備了粗細相同的一根8.8米白色扁繩,參觀者可以自由使用這條繩子,想象8.8米的絛蟲在人體內的樣子。
由於展覽做得太好,目黑寄生蟲館在日本民間口碑極高,甚至成了高中生的戀愛約會聖地——只要和家長說,是去寄生蟲館見習就好。
展覽做得好,不光能博個好名聲,更能帶來實際收益,有時甚至還能救下幾千條生命。
19世紀的美國,就有過這樣一場驚人的巡迴展覽。
雪白整潔的展廳裡,幾十個奇特的保溫箱一字排開,箱中不是什麼神奇動物,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類嬰兒。

與普通嬰兒不同,這些嬰兒看起來更為嬌小,就像剛剛褪去胎毛的雞雛,策展者稱他們為“迷你嬰兒”,因為他們全部是未足月的早產兒。
這種展覽放到現在,一定會因為“非人道”被批評得狗血淋頭,但在當時,它卻改變了6000多名早產兒早夭的命運。
在當年,護理一名早產兒,代價高昂得嚇人,不算其他人工,單單一臺保溫箱,一天就要花費15美元(約合今天的400美元)。不僅如此,由於主流醫學界尚未認可保溫箱的作用,很多早產兒的父母即便有能力支付費用,也難以找到一張“病床”。
絕望中,Martin Couney成為了早產兒最後的救命稻草。這位迷你嬰兒展策展人,同時也是早產兒保溫箱應用的熱心推動者承諾,為早產兒提供最好的醫療護理,而且完全免費。
Martin Couney和他救助的早產兒
Couney也並非鉅富,之所以能為早產兒提供免費醫療,並且一做就是好幾十年,全因為他找到了一個聰明的解決辦法:利用人們的獵奇心理,舉辦展覽,用娃娃們自己賺的門票錢來養活這些脆弱的娃娃。
Couney的想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展覽一經面世,成千上萬的參觀者立刻蜂擁而來,爭相目睹不可思議的迷你嬰兒。一張張25美分的門票,成為了幾千名早產兒的續命寶藏。
在@說說看來,最好的展覽就該是鮮活而生動的,最好與參觀者實現零距離交融。
就像土耳其街角那棟粉紅色的“純真博物館”,盛滿一樓夢幻。
這座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建造的博物館,2014年被評為歐洲年度博物館,頒獎詞中,組委會讚譽道:“規模精緻小巧,講述平凡個體的日常故事,儲存獨特的本土文化記憶。它以非凡的創意在博物館領域樹立了新典範。”
其實嚴格來說,純真博物館並不能算一個真正的博物館——因為博物館裡藏品的來歷,沒有一樣是真實的。
它更像是與帕慕克小說《純真博物館》遙相呼應的一對互文。
《純真博物館》講了一個令人心碎的愛情故事:富家公子凱末爾與出身貧寒的少女芙頌相愛,凱末爾決定為芙頌解除與貴族小姐的婚約。然而陰差陽錯,當凱末爾解除婚約後卻發現,芙頌早已另嫁他人。此後,無法接受痛失所愛的凱末爾以各種手段,收集起有關芙頌的一切,將它們珍藏進自己的“純真博物館”。
現實中,作家帕慕克所建的這座“純真博物館”,正是書中男主人公珍藏愛的樂園。
博物館裡,一樁樁一件件,皆是芙頌的印痕。有兩人初見時,芙頌所穿的高跟鞋,有門把手、小狗擺件,還有芙頌掐滅的4213個菸頭。
當讀者手捧原著走進純真博物館,就像沉入了主人公琦色的內心。每一件展品都對應著書上的一句愛語,展品的細節裡,還隱藏著芙頌與凱末爾互動的彩蛋。
截至2019年,中國已經擁有5535家博物館,達到每25萬人擁有一個博物館的指標。
我們不缺少嚴肅端正的大型歷史展,只是這樣的展覽,往往板著一副老國營飯店的面孔——愛看不看,不看快走——講解牌只寫個大概的文物名稱,背後的文化故事,全靠定時出現的現場講解,或是觀眾自己查證。
我們也不缺少概念新奇的網紅展覽,總有一波華麗高深的藝術,線上挑逗著流量與快門。
唯獨像“純真博物館”或“目黑寄生蟲館”一樣,小而美、小而精的另類博物館,有些少見。
相傳,博物館最早在希臘語裡,是叫做繆斯庵 (museion)的,代表“祭祀繆斯的地方”。而古希臘神話中掌管古老文藝的繆斯,從來都是九位女神。她們分掌不同的文藝領域,代表不同的審美偏好。
從這條脈絡來說,博物館合該是更有個性的。無怪我們呼喚它的出現。
博物之館,網羅天下之寶藏,浩瀚如紫禁盧浮,當然是件美事。
然而對於普通觀眾來說,拼命跑上一天,跑得腰痠背痛也看不完的無盡藏,有時恐怕並不如一份精深優美的小切片來得愜意。
正在改變與想要改變世界的人,都在 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