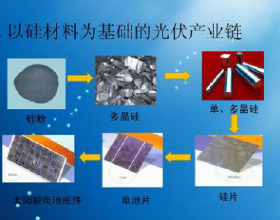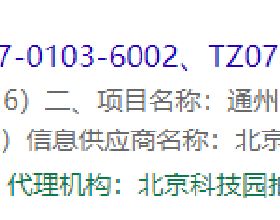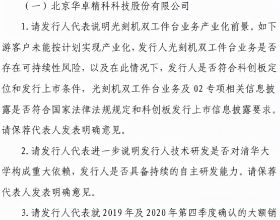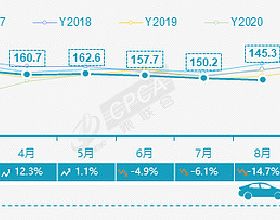1950年這一年對於陳果夫來說,是極其難熬的一年,不論是從政治上,還是身體上,都讓他的內心極度痛苦。
他常常躺在床上回顧自己的一生,他覺得有必要寫一本回憶錄,將自己40多年來的經歷與主張分門別類地寫出來。
對於這件事,他是這樣說的:“我寫此書的目的,在於‘俾世人了我心之所向,與遭謗之由來。’”
當然,這的確是他想要寫這本書的初衷了,但並不完全是因為這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希望借這本書,讓蔣介石知道。
自己是忠於蔣介石,忠於國民黨的,希望蔣介石能發惻隱之心,對陳氏家族另眼相看。
這是他在生命最後階段最想完成的一件事,他將目錄按教育、人事、經濟、政治、道理、制度、CC來源、黨務、豪門等列了出來,希望能夠儘快將這部著作完成。
但是,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病情在不斷加重,他感到死神在不斷地向自己逼近,他倍感時間的緊迫。但又常常感到力不從心,導致回憶錄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
1950年年底,他終於完成了回憶錄之一《蘇政回憶》,瞬間覺得輕鬆了許多,覺得自己精神狀態良好,準備到第二天,再寫其他方面的回憶錄。
除夕之夜,陳果夫獨自坐在床頭,腦海中不斷回想著過去的往事,這是他一直以來的習慣。
每年除夕夜這天,他都會回顧過去一年的工作與生活,但這一年對於他來說,是非同尋常的,有太多值得他感慨的人和事了。
1951年他從臺中搬到臺北市,但因為這裡的氣候炎熱,導致他常常感到十分難受,有時候想要起來坐一會兒,但坐上半個小時左右,就支撐不了了。
所以,他大多時間只能躺在病床上,每次測量體溫,都是38攝氏度左右。
8月18日,醫生在拍完X光後,發現情況已經比預想的更加嚴重,其生命已處於垂危之際。
陳果夫知道,留給自己的時間不多了。臨死之際,他仍然關心著國民黨的前途及臺灣的政局,他覺得自己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掙扎著起床,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在紙上寫下“諍諫之文”四個字,在寫完這篇文章後,他派人將其呈送給蔣介石,以表明他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忠心。
8月25日下午4時52分,陳果夫溘然長逝,終年60歲。
陳果夫永遠的離開了,在他去世當天,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了治喪委員會,並委派CC系骨幹人物洪蘭友擔任總幹事。
8月26日,陳果夫的父親,81歲高齡的陳其業匆匆從臺中趕往臺北護喪,他對兒子先他而去,表現出極大的悲痛。
蔣介石得知此訊息後,也在26日、27日兩天趕到極樂殯儀館弔唁,他望著陳果夫的遺體,表情哀痛,幾度鞠躬,似乎在和陳果夫說這著些什麼......
看到陳果夫的父親也來了,蔣介石哽咽著與其握手,只短短地說了四個字:“逝者安息!”
蔣介石知道,陳果夫病逝這件事對於陳其業老人家的打擊是巨大的,他立刻吩咐工作人員:給予他家人以特殊照顧。
蔣介石之所以這樣做,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希望能夠得到陳果夫在天之靈對他的寬恕。當然,除此之外,他自己本身也是靠陳其美起家的,所以,陳其美可以說是他的恩人了。
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日本,他覺得蔣介石明顯比很多同齡人顯得機靈很多,再加上後來兩人交往甚密,兩人情同兄弟,便介紹蔣介石加入了同盟會。
後來由認識了另一位在日本留學計程車官學生黃郛,三人因為志趣相投,常常在一起談論談下大事,所以後來乾脆結為盟兄。
三人還互換了蘭譜,盟約稱“安危他日終須杖,甘苦來時要共嘗。”蔣介石還將誓言刻在了兩把寶劍的柄上,作為禮物,分別送給了兩位盟兄。
這一次結盟,締造了三人的終身友誼,尤其是對蔣介石在政治上的崛起,以後有非常大的影響。
由於蔣介石精通軍事,擅長策劃,越來越得到陳其美的賞識與器重。後來陳其美直接將其介紹給孫中山。
蔣介石也因此受到孫中山的單獨接見,蔣介石頭腦清楚,見解深刻,孫中山對他大為賞識,這為蔣介石之後政治上發跡準備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有陳其美的大力扶持,再加上孫中山的賞識,1914年之後,蔣介石在革命黨人中的地位也日漸提高,漸漸地取得了獨擋一面的地位。
所以,陳其美對於蔣介石來說,既是盟兄,也是恩人,更是蔣介石與陳果夫建立親密關係的紐帶。
1911年7月,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陳其美親自到南京囑託陳果夫組織了陸軍第四中學同盟會分佈,秘密籌劃南京舉義計劃。
因清軍加強防範,行動困難,陳果夫只得與兩個同學赴上海向陳其美請示。
正在此時,武昌起義爆發,陳果夫按照宋教仁的要求,即率南京同志前往助戰,奉派守衛漢陽兵工廠,後被調到軍政分府軍政科辦事。
漢陽失守以後,陳果夫東下上海,奉父親之命,組織招待所聯絡陸軍小學、中學的同學,分別介紹至各部隊,從事訓練工作。
這時由於工作關係,陳果夫與蔣介石有了接觸。
陳果夫後來在回憶文中專門寫下自己第一次見到蔣介石時的場景。
“那是在1911年10月,我以南京學生軍的身份預備去武漢,到了上海,我在二叔的病榻前見到了蔣先生(蔣介石),二叔向我介紹,說蔣介石是主持杭州方面敢死隊的革命工作的。.....蔣介石威毅穩重的風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十分深刻。”
後來兩人之間的往來也越來越多,陳對蔣十分敬佩,稱“我對他的敬仰之心,便與日俱進。”
從那以後,蔣家、陳家常來常往,如同一家。陳果夫與蔣介石也成為了最親近的朋友、無話不說的至交。
CC組的一個成員在描述陳果夫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時,是這樣說的:
“在委員長(蔣介石)面前,說話能夠盡言而無所畏懼的,只見過兩個人,一位是陳辭修(陳誠),另一位是陳果夫先生。他們兩人跟其他人不一樣,即便他們說的話讓委員長生氣,但他們仍會繼續說下去,並強調讓委員長注意聽他們的話。”
要知道,當時能夠在蔣介石面前直言不諱的,甚至能夠在蔣介石生氣之後仍敢繼續講話的,那一定是蔣十分信任的人。
而陳果夫就是靠著蔣介石的這種信任和庇護在國民黨內展開活動的。
陳果夫幼年患過肺結核病,身體一直十分虛弱,1913年春,曾赴日本調治。
不久,從陳其美的來信中得知將舉行二月革命,陳果夫即提前於6月15日趕到上海,與陸軍中學同學等200餘人組成奮勇軍,自任副司令。
7月中旬,奮勇軍奉派攻擊上海龍華西炮臺,相持數日,終因遭側面攻擊,後援中斷而失敗。
1914年春,開始學習德文,並研究有關合作事業。1915年12月15日,陳其美在上海發動討袁,肇和艦舉事,陳果夫又負責聯絡、通訊及郵件抄寫工作。
討袁失敗後,留陳其美身邊工作。1916年5月18日,陳其美被刺身死,陳果夫返回吳興原籍。
1918年春,陳果夫由其岳父朱五樓介紹去上海晉安錢莊學習錢業,當了助理信房。
1919年秋天,孫中山為了政治活動需要籌集資金,指示在上海設立一家商品交易所。
1920年秋,陳果夫就和張靜江、戴季陶、蔣介石一起開始籌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陳果夫組設茂新號任經理,併為這一交易所第54號經紀人,經營棉花、證券等投機生意;不久,又和朱守梅組設鼎新號,朱守梅任經理,陳果夫任協理,經營棉紗、金銀生意。
從1920年 到1921年,交易所生意十分興隆,做了數萬元交易,佣金收入總計達20餘萬元。
陳果夫的這一段經歷,使他獲得了國民黨“理財專家”的稱號。
一次他在高興之餘,談到過去自己經商的“五大財神”:第一路是擴大營業之神,第二路是縮小營業之神,第三路是維持營業之神,第四路是停止營業之神,第五路是改換行業之神,條條大路通羅馬。
這是根據市場的潮漲潮落、需求變化及時改變自己的經營規模、方式。
在瞬息萬變、捉摸不定的上海證券市場,他的經驗之談不無道理。
蔣介石在大陸統治22年,一部分財政一直掌握在陳果夫的手中,長期兼任國民黨四大銀行之一——農業銀行的董事長、中央合作金庫理事長和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
之所以這樣,還是因為他是個“理財專家”,和蔣介石在上海共過難,一起做過股票生意賺大錢。這是陳賺錢出奇的地方。
陳果夫進入國民黨的權力圈已是1924年,當時正值黃埔軍校創辦,他在上海養病,孫中山派人送來委任狀,任命陳和趙澄志、劉祖漢為上海地區招生委員,同時為軍校採購各種軍用品。
1926年陳果夫擔任中央監察委員,並正式進入國民黨中央決策機構。
國民黨官場權力大小的關鍵不在職務的高低,關鍵在於能否出沒於蔣介石的身邊和為蔣所重用。陳果夫一到廣州就成為蔣介石最重要的助手。
在反共的道路上,陳果夫追隨蔣介石是亦步亦趨,步步緊隨。
在作為蔣介石的反共助手的同時,陳果夫還積極協助蔣介石對付國民黨內其他派系的挑戰,是蔣介石度過政變上臺後至1931年底這一困難時期的堅定支持者。
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後,陳果夫聯合戴季陶、丁惟汾等一批人,在上海灘成立“中央俱樂部”,糾集擁蔣力量,準備迎蔣上臺。
“三會”召開時,陳果夫、陳立夫透過CC系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中的活動,直接控制大會代表的選舉,一腳踢開與蔣不合作的汪精衛派和西山會議派,聯合另一大派胡漢民系,單方面召開“三全”。
透過“三全”,二陳成功地把國民黨改造成清一色的“蔣家黨”,大大鞏固了蔣介石在黨內的統治地位。
“三全”開完,陳果夫的職務被升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執委常務委員等,隨著他在黨內位置的升遷和鞏固,CC系的勢力在“三全”前後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三全”以後至“九·一八事變”,國民黨內進入混戰高潮。
在蔣介石對付挑戰的過程中,陳果夫利用CC系在各省市的勢力,公開的秘密的拆倒蔣各派的臺,挖各家軍閥的牆角,起到了蔣介石的槍桿子無法起的作用,有效和及時地配合了老蔣的軍事和政治行動,深受蔣的讚賞。
1931年6月,陳果夫因肺結核病日益嚴重,提出辭去中組部代部長的要求,到政府裡去任職。
表面上從此就提出國民黨的中央黨務部門,不再從事以進行派系鬥爭和權力鬥爭為主的繁重的黨務工作。後來他的黨權移交給了陳立夫。
1932年8月,陳果夫被任命為導淮委員會代理副委員長,負責治理淮河的工作。
1933南10月,陳果夫又被任命為江蘇省政府主席,兩職相兼,工作便利,使導淮工程加快,到1937年上半年,導淮工程已見成效。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導淮入海入江工程被迫中斷。
1937年12月19日,蔣介石任命正在撤往大後方途中的陳果夫為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主持由陳自己創辦的國民黨政訓幹部的最高學府工作。
1939年,委員長侍從室增設第三處,陳果夫調任處長。該處許可權極大,負責選派參加蔣介石專門培訓高階幹部的中央訓練團人選,掌管黨政軍各部門上層人物的獎賞與處罰。
抗戰勝利後,侍從室改組,第三處撤銷,陳果夫的“主任”職自動停止。
自此以後,除了在經濟界掛有幾個頭銜外,僅是中執委和中常委,在政界再也沒有什麼具體職務。
由於CC系名聲越拉越臭,再加上他的身體越來越壞,蔣介石已讓其處於半退休狀態。
到1948年12月,國民黨的軍事形勢是一片昏天黑地,凶信一個接一個。徐蚌方面,東援而來的黃維12兵團已被團團圍住,逃離徐州的杜聿明的8個兵團正在落入包圍之中。
平津方面,60萬大軍在東起灤縣、西至張家口的長達600公里的戰線上被分割包圍。
蔣介石集團覆滅在前,大佬們紛紛開始安排自己的退路。陳果夫捷足先登,一走了之。
12月6日晚10時,身體已經非常糟糕的陳果夫登上“中興輪”,離開上海去臺灣,第二天深夜到達基隆港,連夜趕到臺中雙十路八號定居。
從此永遠離開祖國大陸,離開家鄉,流落海島,偏安一限。到臺灣後的陳果夫並不輕鬆,政治上的打擊尤甚。先是大權盡去。
蔣介石從培植兒子蔣經國出發,乘國民黨失敗移臺之際,把黨政軍各種大權集中到蔣經國、陳誠為首的新實力派手中,不得不怠慢過去長期跟隨過自己的老人。陳果夫也不例外。
兄弟倆掌管22年之久的黨務、組織、特工、宣傳等大權,全部落入蔣經國系的手中。
陳果夫從抗戰以來已剩不多的幾個具體職務也被剝奪而去;一生高高在上的他,開始嚐到重權盡失、寄人籬下的味道。
再是又遭清算。國民黨在大陸慘敗,使得黨內不少人起來要求追究失敗的責任。陳果夫和陳立夫作為黨務最高負責人,首當其衝遭到清算,要對國民黨失敗負責。
而此時的他們,身為國民黨過去的黨國重臣、軍隊統帥、派系首領,在蔣介石、蔣經國、陳誠嚴密控制下的臺灣,失去了施展各自政治權術的市場,只有聽候發落。
陳果夫因為病重臥床不起,只好任人指斥,與很多國民黨的上層人物一起,充當蔣介石在大陸失敗的替罪羊。
陳果夫的壓力除了來自政治上的麻煩外,還有是來自一輩子沒有治癒的肺結核病。
數十年來,肺部屢屢出現險情,靠著憑藉特權弄到的國內外稀有藥品,得以維持生命,控制病情。
為了弄藥,甚至宋美齡、蔣緯國等人親自出面到美國、或到駐華美軍中去搞。
臨赴臺前夕,肺部病情再度加劇,背後炎症流膿不止,經蔣介石特准後馬上去臺灣安心養病。在臺中市,請遍港、臺的名醫會診,暫時控制住病情。
“安心養病”,怎能“安心”下來,各種打擊不從一處來,除有政治方面、體質方面的外,還有經濟方面的,還得整日為高昂的支出發愁。
治療肺結核,需要鉅額醫療費。陳果夫既無積蓄,又無財產,更無以前的地位。
醫藥費都要靠朋友資助。為方便治病用車,農業銀行看在老董事長的面上,給了一輛小車。可因為農行在臺灣沒有業務,再加上不久農行撤銷,故不提供汽油,汽油靠老部下接濟。
這並不奇怪,陳果夫雖說是國民黨統治集團裡的重要一員,但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為了保持他的地位,提防他人暗算,很少斂財斂物。
正如他給農業銀行的題詞那樣:
“文不取謂之清,深思熟慮謂之慎,刻苦耐勞謂之勒,注重時效謂之敏。”
在國民黨上層,“慎”的人有之,“勤”的人有之,“敏”的人也有之,但像陳果夫這樣“清”的人可真不多見。
事到如今,經濟上的拮据使得陳果夫不得不放下架子,親筆寫信給交通銀行的趙棣華,索取自己兼職董事的車馬費。
趙棣華急忙讓洪蘭友把陳果夫的窘境轉告蔣介石。蔣介石趕緊批給5000銀元作為醫藥費,另外還批給一筆特別費。
老蔣需要的是陳果夫、陳立夫等昔日的軍政大員交出手中的權力,而不是把他們逼入死路,以表現自己的豁達大度和不失情義,尤其是對二陳這樣的重臣。
蔣介石不會忘記陳家兄弟和CC系對自己的突出奉獻。1949年11月6日,蔣介石到阿里山休養,路經臺中時特意到陳府拜訪。
此時陳果夫正在發病,不能講話,只好用書面交談,蔣介石讓陳果夫不要太節省。
次年10月9日正逢陳果夫58歲生日,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倆專門前往祝壽,詢問治療情況。問陳果夫“用中醫治,抑西醫治?”陳答道:“現在用西醫,將來培補時需要中醫。”
蔣介石勸說:“還是西醫可靠。”但是陳果夫已病入膏肓,中醫、西醫均已無濟於事。
臨走前,蔣介石再一次叮囑陳果夫有困難就提,一定不要太節省
1951年1月22日,為方便治療,陳果夫從臺中遷往臺北青田街。
同年8月病情再度惡化,25日下午病逝。蔣介石對他的死去很是悲傷,26、27日兩天連續到臺北極樂賓館悼念,送上輓額,頒發褒揚令。
並且成立了包括陳誠、蔣經國、何應欽、王世傑、吳國楨、周至柔、張道藩在內的31人的治喪委員會,洪蘭友為總幹事。他們把陳果夫埋葬在臺北觀音山西雲寺的右側山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