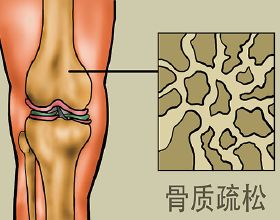幸運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
父親打來電話的時候我正坐在第八十三集團軍醫院對面的一家小飯館吃飯,炒麵剛剛端上來,手機發出輕微的聲響和震動,我翻過來一看,來電顯示為——“爸”。
我沒有去接,首先的表現是抗拒,我看著螢幕閃爍的亮光,就那麼看著,直到它漸漸滅了下去。我不確定父親給我打電話是有什麼好的事情,也許只是問候,可我不需要。可是如果有其他事情呢?比如前段時間打電話讓我接種疫苗。
只是,我真不想和父母有過多的交集。看到他們的名字,聽到他們的聲音,看到他們的臉龐,甚至只是想起他們就能讓我瞬間從陽光明媚的心情中跌落底谷,前一秒還是春風拂面,這一秒就是暴雪冰雹。
想起一句話說,幸運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
還想起一句話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我覺得我對於父母的心理陰影可能這輩子都將伴隨著我如影隨形了,逃不出的暗黑迷霧叢林。
炒麵沒有吃完,付過款來到小吃街買了三個雞爪帶回家。此時已經是八點左右。
我拿出手機看著那個未接來電,幾度踟躕,反正左也是一刀右也是一刀,早砍早解脫,我回撥了過去······
所幸,不是什麼壞事。原來前幾天我希望我弟去鄭州時能幫我捎兩樣東西,但是我爸說讓我弟拐到新鄉太麻煩了,他從新鄉到鄭州還需要倒車到新鄭。我說,那就算了,讓他放家裡就好。隨即我趕緊說,那就這樣吧。我結束通話了電話。像奔逃似的,心裡甚至有幾分慶幸。
掛完電話後我生無可戀地躺在床上,彷彿剛剛跑了一個一萬米,跑到虛脫。每次和父母通電話都是這樣。短短兩三分鐘的通話對我來說簡直像是經歷了一場嚴刑拷打烈火烹熬,把我整個人的生命力都給抽走了。每次和父母打完一通電話,我都得緩一個星期才能緩過來,生活才能再漸漸步入正軌。
我為什麼不願意和父母通話?這就是原因。和他們的通話只會打亂你的生活,還會讓你遭受一次精神的摧殘,你的世界如烈火過境,一片殘垣廢墟,而你要重新花時間去修復你那受傷的心靈······
真的好累啊······
好累啊······
考研時沒這麼累過······打工時沒這麼累過······刷卷子刷得天昏地暗頭暈眼花時沒這麼累過······在工廠的流水線一干幹十個小時不知白天黑夜時沒這麼累過······
可是,僅僅和父母通了兩三分鐘電話,就彷彿奪走了我的生命。
我渴望救贖。
也許我真的該去看看心理醫生,可是,說實話,我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曾經也考上過研究生,我對於心理問題有自己的判斷,我一向對於心理學和精神學嗤之以鼻,因為我覺得,你根本不可能去幫助他人解決一個心理問題。那些人啊,心理醫生啥的,都是唬人的,我才不要去做冤大頭去花成千上萬的錢聽這些人跳大仙似的跟你胡侃。
這不是1+1=2,也不是背一首詩忘了其中的一句詞,這是一個人心理的迷失······
他緩步前行,走在迷霧般的森林之中,林中有老虎,有獅子,有矯捷的獵豹,有眼睛冒著綠光的惡狼,但沒有花朵,沒有兔子,沒有童話的姑娘······這是一個沒有色彩的世界。這是一個灰色的世界。
你懂嗎?
我曾經無數次地想過,該怎樣斬斷這前世今生的宿怨,我想來想去都想不出辦法。我既沒有決心徹底地一走了之再也不管不顧,也沒有耐心在他們膝前盡孝表演閤家歡睦。如果說25歲之前我還曾想過改變想過和解之類的話,那麼25歲以後,我徹底斬斷了這些念想。
不管對於我父母,還是對於我,要改變彼此都是一件痛苦的事,那是一種彼此撕裂的折磨。而這種嘗試和拉扯,我們已經進行了十三年,從我十二歲,到我二十五歲,十三年的光陰流逝,我和我父母的關係仍在原地踏步,甚至更加惡化。
我累了······
不想吵了,不想鬧了,不想爭論了,不想改變了······
這世界上,哪裡有感同身受啊······
西方神話中有一個叫西西弗斯的傢伙,這傢伙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推石頭。他把一塊圓形的巨石從山底往山頂推,然後看著它滑落,然後他再推,然後他再看著它滑落,他推······它滑······他推······它滑······西西弗斯就在這種重複中度過了他的一生······
我忽然覺得,我彷彿也是西西弗斯。在不停地迴圈,不停地重複,在進行一個看不到頭的苦役。
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呢?於是我就惡狠狠地想,如果我是西西弗斯,我就讓那塊巨石碾壓過我的身體,把我碾得血肉模糊支離破碎,然後在我的嘲笑聲中,我將看著那塊巨石麻溜溜地滾到山下,紛飛破碎,玉石俱焚,至少,這一次,我沒有輸!
我是啞巴不說話,一個考了3次研究生才上岸,卻在開學3個月後退學的大齡待業青年。
堅持每日書寫讀書筆記、個人成長、思考感悟。
喜歡的話歡迎點個贊和關注。大家一起進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