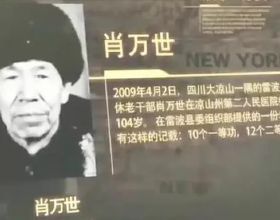養娃十年,我還從沒打過小孩。
因為打小孩這個事吧,想想都很分裂。
前一刻還心肝寶貝小天使,後一刻就揍死你個兔崽子,怎麼都像是神經不好了。
而且吧,我這人偶像包袱還特別重。
扯嗓門甩巴掌,那絕壁是中年大嬸才會做的事。
不好意思,我們美麗優雅的中年少女做不出來。
所以每次有人要打小孩的時候我都會好言相勸:
消消氣,想想別的辦法。
打不是教育,只是在發洩我們自己的情緒罷了。
通常對方都會表示懂了懂了豁然開朗,從此洗心革面重新做媽。。。
好吧,這是不可能的。
這只是我的美好想象。
真實情況是,通常對方都會痛心疾首地對我說:
不是,你只是還沒氣到那個份上!
要是沒瘋,誰會打自己的小孩啊!
不發洩情緒,我怕我活不長!
然後就聊不下去了,只能一別兩寬,各養各娃。
人類的媽的悲歡不能相通,除非遇到同一款娃。
這個道理我直到最近才懂,代價簡直慘痛。
幾天前大麥和小米去上鋼琴課,天氣很好,她們騎上腳踏車就出發了。
我忙完手頭的事也出發了,學校很近,幾分鐘就到。
車還沒停好,手機就響了。
居然是鋼琴老師打來的!
我愣了一秒,這位德國老太太是智慧手機恐懼症患者,平時很少打電話給我。
而且此時已經是大麥的上課時間,小米應該在門口座椅上等著,會有什麼事?
按了接聽,老太太劈頭就問我有沒有看到小米。
我懵了。
老太太說小米不願意坐在門口等,執意要在操場騎一會兒車,但是後來人就不見了。
我向操場狂奔而去,看到那裡空無一人,只有兩輛腳踏車,分別是大麥和老太太的。
學校很小,疫情期間只上半天課,下午除了個別辦公室開著,教學樓幾乎處於封閉狀態。
小米騎著車應該不會去樓裡,也沒理由放著操場這麼空曠的地方去其它地方騎,難道回家找我去了?
這個可能性很小,因為上課的東西已經帶全了,吃的喝的都在大麥的包裡。
但我還是回家找了一遍,不在。
難道是路上走岔了沒看到?
我再次回到學校,直奔操場,希望她從哪個角落裡嘿嘿嘿笑著鑽出來,故意嚇我一跳。
可惜沒有。
操場上還是那兩輛腳踏車。
這時一位相識的老師從辦公樓走了出來,我趕緊迎了上去,問她有沒有見到小米。
她搖搖頭說沒有,之前都在辦公室備課,沒有見到別人。
看著她離開的背影,我腿腳有些發軟,燦爛的陽光下寧靜的校園越看越覺得瘮人。
折回到停車場,突然發現多了一輛波蘭牌照的廂式貨車。
正尋思著,一個身形高大、滿臉絡腮鬍子的男人從遠處走來。
我問他有沒有看到一個騎車的小姑娘,他說他剛來,一個人都沒有碰到,就準備開車離開。
忽然之間,我的腦海裡閃過一個可怕的念頭。
去年這個城市一度流傳著廂式貨車拐騙小孩的故事,各種目擊證人說得繪聲繪色,雖然最後警方出面闢謠,但一時間人心惶惶,滿城風雨。
又是廂式貨車!又是外國車牌!
我暗叫不好,趕緊掏出手機對著車尾亂拍一氣,然後跳上自己的車,一踩油門追了出去。
一邊追,我一邊後悔在司機回來之前沒有朝車裡多看兩眼。
那時候車廂裡沒有任何動靜,裡面到底會是什麼?
想到這裡,渾身汗毛都豎了起來!
貨車在30碼居民區開得飛快,簡直就是大寫的做賊心虛。
我猛轟油門緊追不捨,幾次接近的時候都恨不得把這輛破車直接撞停。
狂追幾公里後來到一個三岔路口,一轉彎,我傻眼了!
每一條路都空空蕩蕩。
急忙盲選一條開到頭,又是一個三岔路口,貨車早已無影無蹤。
跟丟了,我只覺得喉嚨發緊,全身血液都凝固了。
急急開啟手機檢視剛才拍下的照片,發現正好逆光,車牌模糊一片。
完了,我腦袋轟地一響,癱坐在駕駛座上。
好容易讓自己鎮定下來,我單方面宣佈那只是誤會一場,決定再回家碰碰運氣。
鄰居正在整理花園,揮揮手朝我打招呼。
路上行人三三兩兩,有相約出門跑步的,有全家出來遛彎的,有獨自匆匆趕路的。
一眼望去,誰都形跡可疑,誰都不懷好意。
就連那位鄰居也不能排除嫌疑,畢竟我還沒有去過他家地下室。
我打量著這個世界,覺得危機四伏,暗潮洶湧,充滿變態。
家裡還是沒人。
學校是最後的希望,希望她已經回去。
第三次狂奔到操場,我一個踉蹌,差點跪倒。
空無一人的操場上,仍然只有兩輛腳踏車!
我不知道自己衝進教室的時候臉色有多蒼白,老太太聽聞用手緊緊捂住了嘴巴,大喊:
哦不!
這是她的招牌動作,表示無與倫比的驚訝和恐懼。
上回小米宣佈要參加鋼琴比賽的時候,她也是這種反應。
大麥已經急哭,語無倫次地重複著:
她答應我不會離開操場的啊!她答應的啊!
我在腦海裡拼命搜尋其它的可能性,終於想起她最近很愛去閨蜜家玩,會不會在那兒?
因為手抖得厲害,幾次都沒有撥通電話。
終於撥通的時候,我帶著哭腔發出了絕望的靈魂之問:
我娃在你家嗎???
在的。
。。。
元神終於一點一點,慢慢歸位。
這才發現朋友其實早已在群裡留言,只不過資訊太多,幾次匆匆翻看的時候都錯過了。
我捧著胸口坐在教室門外,心臟依然狂跳不止。
中年少女也到底是中年人了,這麼搞是會出人命的。
老太太出來安慰我,說著說著,也不知道是不是安慰了。
她說小米這孩子啊,主意很大,和她姐完全不一樣。
比如你讓她彈慢一點吧,她說她就喜歡彈那麼快。
你說這裡要彈輕一點吧,她說她就覺得重一點好聽。
反正就是,不怎麼滴好教。
當然了,這也不是壞事,這就是一種,哈,一種性格哈!
我同情地看著老太太,內心充滿了歉意。
大麥生氣地說:
這就是一種很壞的性格!打一頓就好了!
我說好,我們去把她捉回來打一頓,就這麼愉快地決定了。
當然我們是用中文說的,不然老太太肯定會報警的。
在去朋友家的路上我心裡一直在彩排怎麼打這個小孩。
我已經氣到那個份上了,我已經瘋了,如果不發洩情緒我怕我活不長了!
這一刻我和所有痛心疾首的老母親們悲歡相通了,靈魂共振了,完全理解了!
少女都給我閃開,大嬸袖子已經卷了起來!
車一停,大麥第一個衝了下去。
小米一臉壞笑地站在門口。
大麥對著她屁股就是咣咣兩巴掌:
你這個小壞蛋!你把我們都要急死了啊!
我驚呆了!
這是要扭轉歷史了嗎?
歷史也就扭轉了一秒鐘,小米立即反應過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回去五巴掌。
大麥再次順應歷史,嗷嗷直叫。
一場混戰打亂了我的思路,想象中打小孩的動作無法一氣呵成,只得先把她倆拎回車裡,等候發落。
此時大兄弟已經到家,聽完我的血淚控訴,沉吟道:
這樣吧,要麼打一頓,要麼罰零花錢,選一樣吧。
我嘆了口氣,到底是親生的,知道給娃留一條活路。
小米在猶豫。
這貨居然在猶豫!
她居然在認真考慮怎樣用一頓毒打去保住她的錢!
這是怎樣一種精神啊!
果然,想了半天之後她問道:
罰錢的話要罰多少錢?打一頓的話要怎麼打,打幾下?
大麥瞬間找出一根巨長的棍子,說:
你給我跪下!杖刑!就像虛竹那樣受罰!
不用說,她最近又在看《天龍八部》了。
小米覺得人格受到了侮辱,但在這個時候又不好發作,恨恨地嘀咕:
什麼虛豬,你才是豬,你才是豬!
這時一家之主大兄弟發話了:
罰錢的話罰一個月零花錢,打的話就打一百下!
真是一道送分題啊,一個月零花錢也就十幾歐,打一百下動手的人也會很累的好嗎?
可是小米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打一百下,誓死保衛零花錢。
大兄弟眼裡流露出一絲驚訝,一絲心痛,還特麼帶著一絲欣賞,對我說:
你來打吧,我下手太重,會打出問題來的。
我???
敢情打小孩還成了煎牛排,你烈火烹油一下就熟過頭了,只有我能完美煎成七分熟?
兩個不會打小孩的人這麼相互謙讓有意思嗎?
我拿起棍子,覺得很不順手,舉起巴掌,又想起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內心十分糾結。
要論舒適性、靈活性和可控性,雞毛撣子才是打小孩的獨門利器,可惜德國沒有。
“你給我好好反省,一會兒再來收拾你!”
我撂下一句狠話,就上樓歇著去了。
躺到床上,心有餘悸,渾身像是虛脫了一樣,半天也沒緩過來。
小米一扭一扭進了房間,蹭到我身邊,又撲在我身上:
媽媽對不起,我錯了,下次再也不這樣了。
說著又撅起屁股:
你打,你打,一百下!
我深深嘆了口氣。
如果只有大麥,我將是一位多麼成功的育兒博主啊!
大麥的一切都長在老母親的希望上,懂事,勤奮,乖巧,各種靠譜,所有老師都對她讚不絕口。
她的存在令我自信,篤定,體面,充滿成就感。
而小米似乎生來就是啪啪打臉的,讓我不停體驗失控和挫敗。
她是與生俱來的“規則破壞者”。
從她會開口說話的那一天起,“不要,不要”、“寄幾,寄幾”就如魔音繞耳,再大一點“這是我的生活不是你的”更是掛在嘴邊,令人又好氣,又好笑,又無可奈何。
她在牆上亂畫,把褲子剪出一個個破洞,把頭髮鉸得像狗啃一樣,永遠不穿我給她搭配好的衣服,永遠試圖去做大麥沒有做過的事情。
她在音樂早教課上脫了衣服嘎嘎嘎笑著裸奔,在芭蕾彙報演出中往地上一躺自顧自地摳腳,在中文聽寫的時候想出各種辦法打小抄,上網課的時候把聲音關掉不理老師,還假裝網路不好什麼都聽不清。。。
就連騎個腳踏車,也是這種畫風的:我騎了一輩子腳踏車也沒想過要擺這個造型。
大麥如果不戴頭盔根本連腳踏車都不會碰一下。
所以這是魔童轉世嗎?
我從來沒有打過小孩,雖然有時候急火攻心也會有瞬間的疑惑:
是不是有的小孩就是不打不行?
可每次慢慢消化掉自己的情緒之後,又會心軟,總是想:
真的沒有別的辦法了嗎?再試試看吧。
至少她現在不會亂塗亂畫了,也不會搞破壞了,上課能好好坐著,表演能盡力配合,也知道作弊的嚴重性了,犯過的錯誤後來也都改正了。
雖然費了老鼻子勁,過程漫長得簡直能要人命,但是畢竟,必要的規則感還是在她內心慢慢建立起來了。
不算是多麼成功的教育,可好像也沒有多麼失敗。
想了想,我在她屁股上拍了一百下。
她一邊笑著說舒服,舒服,還要,還要,一邊使勁往我懷裡鑽。
我問她,為什麼要選打一頓,是捨不得錢嗎?
她眼珠骨碌碌一轉,說,也不全是,我就是想知道你們到底會怎麼打我。
我突然明白了,這貨是想要證明我們到底有多愛她。
我抱了抱她說:
爸爸媽媽還有姐姐都很愛你,所以才會這麼著急。
上次姐姐按錯電梯不見了,你是不是也急哭了?
這次姐姐也急哭了,連媽媽都快哭了。
你已經八歲了,要有點責任感了,答應別人的事要做到,不能想起一出就是一出。
以後做每一件事之前都要想想後果,考慮一下別人的感受,不能只顧自己。
如果說好的事情要改變,一定要事先交代好,讓大家放心。
她若有所思,點頭表示同意。
這時大麥跑了進來,興致勃勃地問:
打了嗎打了嗎?怎麼打的啊?
我說打過了打了一百下,你得保密,不能報警。
大麥班上有個小男孩經常被他爸一言不合一通暴揍,以至於到後來考得不好老師都不敢髮捲子。
這個男孩孤僻,暴戾,打架鬥毆,破壞公物,成績一塌糊塗。
也許就是傳說中那種“不打不行”的孩子吧。
可是小學四年,情況沒有好轉,反而越來越糟。
從一年級的稍顯調皮,到四年級的自暴自棄,似乎進入了一個“越打越不行”的死迴圈。
要知道,德國孩子剛進小學老師就會告訴他們,任何大人都沒有權力打小孩,父母也不能,如果有人打你,可以報警。
然而,哪怕全世界都知道他經常捱打,這個孩子始終沒有報警。
孩子對父母的愛和依戀,往往比我們想象的多得多。
當最愛的人對自己拳腳相加時,世界是崩塌的,情感是分裂的。
而報警這種大義滅親的舉動,從根本上是違反人性的。
孩子內心的痛苦和糾結,成年人很難體會。
其實有時候我們比孩子更任性,仗著他們的愛肆意妄為罷了。
我常常想,生孩子也許就像買樂透,遇到天使型的孩子就好好珍惜吧。
萬一遇到魔童型的,那就要做好準備面對一場修行。
沒有修行的艱苦,哪來緣分的深厚。
我們擔的驚受的怕,還有那一地操碎的心,也許就是將來他們飛走後,還會回來的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