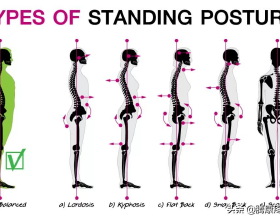「你本就應當是我的。」他頭一次紅了眼,沙啞著聲音說道。「是我先娶的你,是我先教你動了情,你本就應當伴我一輩子,你本就應當愛我的。」
她垂著眸子,久久不語。
長久的沉默後,她也只是輕輕開口,像是嘆息,也像是解脫。
「太遲了。」0.
「你現在這是在做什麼。」他面無表情的看著眼前的女人。
她一如既往的端正,規矩,一絲不苟的挑不出任何錯誤,就那般攏袖挺身直直的在他面前站著,神色無波。
而這些都讓他極其厭惡。
她平靜的看著眼前的男人,細細掃過他眉眼,再開口時卻隱隱帶了一絲不易察覺的脆弱。
「縱使是偽裝也應當叫旁人看不出端倪才是,更何況今日春華盛宴,口舌眾多,殿下應當至少注意自己的行為。」
「王妃是在教本王如何做事嗎。」衛延盛不耐煩的開口打斷,露出譏諷的神色,口中說出的話卻無比毒辣。
「王妃雖然憑藉母族為自己搏得了王妃的身份,不會還在奢望本王對你相敬如賓吧?」
此話一出,衛延盛滿意的看著面前的女人的神色出現了動搖,像是一張完美的面具出現了裂痕。
他享受欣賞眼前這個處處完美的女人在他面前崩潰,他想看她狼狽不堪的模樣。
「…殿下。」衛延盛聽著眼前的女人輕輕啟唇開口道,眸色似乎一瞬間有些晦暗。「我們走過三書六禮,是明媒正娶,京城皆知。」
衛延盛依舊面無表情的看著眼前的女人,直到看見她素來精緻的面孔上泛開一抹蒼白,指尖才下意識動了動。
「殿下也應當敬我愛我,如我待殿下一般。」
說完這句話似乎已經抽乾了她的力氣,讓她似乎都沒有多餘的精力去聽衛延盛的回答。
她轉身,微微有些踉蹌的緩步離開。
在她身後,她聽見了男人一聲冷嗤。
「絕不。」
1.
京城人人皆知,當今皇子衛延盛風風光光的迎娶了舒家長女,舒長清。
那一日的十里紅妝可謂是鋪滿京城街道,極度盛寵再也不僅僅是說書先生口中的風景,而是衛延盛一點點為舒長清在京城蓋出來的。
城中貴女們都豔羨舒家長女一門好婚事,從此搖身一變皇子妃。可無奈就算她們羨慕嫉妒的眼睛都紅了,手帕子都快擰爛了,卻也沒人會在背後嚼舌根,說上半句這婚事的不搭。
誰都知道舒家手握兵權,舒家家主和長兄弟們,哪個不是在戰場上立下赫赫戰功?平定邊疆騷亂,內定潛在叛徒,舒家都立下了不少功勳。
更別提舒家家主年輕時,更是隻身縱白馬,提一柄血刃白銀長槍,殺入敵營深處,以一隻眼睛的代價保回了當今聖上。
如今聖上對舒家盛寵不斷,深信不疑,甚至連皇子妃的候選人都沒列舉幾個,直接就欽定了舒家。
倘若舒家長女若是貌醜了些,才學疏淺了些,那麼貴女們倒也不必如此妒忌忿忿;可偏偏舒長清稱得上是京城才女,大家閨秀;容貌端莊秀麗,恪守禮節,自小便是那別人家的閨女,是從小被大人們樹立的榜樣。
更何況舒長清與衛延盛自小相識,有青梅竹馬的緣分在先,此刻結姻,更應當是緣上添喜。
如此,這婚姻,稱得上是男才女貌,門當戶對。
只不過舒長清自己知曉,這不過是外相。
褪去了那些被他人處處稱讚的假象,留給她的,不過是大婚當晚被挑開蓋頭後,衛延盛一聲冷笑。
那晚她應當是羞澀的,少女皆懷春,舒長清也不例外。大婚那日她已按嬤嬤說的,一整日未進滴水粒食,縱使頭上壓著沉重的頭飾,也挺直著脊背,以素來毫不出錯的禮儀風範走過了所有場合。
過長街,跨火盆,拜堂成親。
可當眾人鬨笑散去,丫鬟們退下並貼心的關上了門窗,隱隱紅燭倒影跳躍,她坐在新床上的核桃瓜棗中間,蓋頭被掀起後,她只聽得衛延盛一聲冷笑,和一句漫不經心的:
「好了,別裝了。你不覺得倒胃口嗎?」
這話在舒長清心裡激起層層浪,幾乎一瞬讓她有些不知所措;但多年端莊的教養讓舒長清不會輕易失態,所以她只是穩了穩心神,抬頭溫和的看向自己的夫君。
「夜深了,不如夫君先同臣妾飲過合巹酒,爾後再……」
她話未說完,衛延盛便不耐煩的蹙眉,那張英俊的臉龐上清楚的寫滿了厭惡。
「做給外人看的東西你還沒演夠?這門婚事本來就不是你情我願的事,有必要演戲演到底麼?舒家女,你莫要得寸進尺。」
也許是得寸進尺這個詞用的過於陰陽怪氣,讓舒長清立刻就明白了衛延盛的意思;縱使有著粉脂點綴,卻還是讓她不自禁的白了白臉色。
與自己成親,竟讓他委屈至此,甚至連行得一個完整的婚禮,於他而言,都算是得寸進尺麼?
久久沉默下,衛延盛像是不滿意她的安靜,繼而又開口道。
「我本不願苛責於你,畢竟我們也算是自幼相識,有過青梅竹馬的緣分。我敬你如妹妹,時常惦念你的好;你我本就應當如此以兄妹相稱,各自嫁娶,幸福的過完餘生。可你千不該萬不該,在知曉了我與嬌嬌兒的事後,還恬不知恥的以你舒家的手段,強迫了這段婚事。」
他說的如此冠冕堂皇,理所應當,言語裡的惡毒幾乎要化作鋒利無比的劍刃,一下下往她心口挖去。
舒長清垂著眸子,唇瓣哆嗦。
她沉默,長久的沉默著,像是不願反駁,像是無法反駁。
她越是不開口,衛延盛眼底的嘲諷便又是多一分,他便愈發肯定,是舒長清假借家族之勢,強迫了這門婚事。
打小他就明白的,舒長清對他的感情不僅僅是兄長之情;那雙常常跟隨著他的眸子裡含著別的情愫。
這份感情在舒長清還年幼的時候尚且無法好好的隱藏,表達的明顯且炙熱,卻讓同樣年幼的衛延盛無所適從。
舒長清在他心中,一直是鄰家妹妹的存在,別無他想。
因為衛延盛過往裡最先瞥見的那一抹豔紅,那一抹暖陽下綻放的無拘無束的笑意,才是徹底驚豔了衛延盛整個年少時光的存在,那個他愛了十年的女孩。
沈嬌。
2.
舒長清很快肩負起了府上的打理工作,上至處理府內要事,下到解決下人瑣碎,她都辦理的井井有條,毫無紕漏。
就連覲見皇后,她也精心挑選了合適的禮品,以宮廷嬤嬤都挑不出錯的禮儀姿態,和皇后交談了足有大半個下午。
皇后掐著程度試探的詢問了婚事當晚,舒長清恰到好處的羞紅了臉低頭,露出小女兒家的嬌俏姿態。那一副含春羞澀模樣,早已代替了千言萬語。
皇后瞭然,終於放下心來。「如此甚好…本宮到底是女人,這些事上多些考慮是應該的。你倘若能早早生個孩子,那對你地位上的鞏固是極其有幫助的。」
語半,皇后似乎頗為愛憐的抬手輕撫舒長清面頰一側,指腹捻著替她挽起額角碎髮,眸子裡隱藏著舒長清有些看不太明白的神色。
「長清,本宮也算是看著你長大,待你更是如親生女兒般。你且聽本宮一句勸,倘若延盛這孩子若要納娶妾室,你自隨他去便是,切莫要為一些小事而鬧了笑話。你如今是皇子妃,是容不得出錯的存在,府內府外多少眼睛盯著你準備看你犯錯,你斷不能讓他們瞧見,知道了嗎?」
舒長清看著皇后的眼睛,將含在嘴邊的那句“我與殿下未曾洞房過”終究還是嚥了下去,緩緩地點了點頭。
這一輕輕點頭許諾,皇后卻像是鬆了極大一口氣似的,疲憊的向後靠去,攏手遮住雙眸垂頭。
「如此便好…如此甚好。你從小就是個令人省心的孩子……本宮乏了,今日你且先回吧。」
有宮女欠身領著舒長清往宮外走去,穿過層層紅牆,直到馬車離開大門,身後的宮門沉重關閉,舒長清這才堪堪回神,心口止不住的翻上酸澀的難過。
這令人喘不上氣的心情過於沉重,一時間竟然讓舒長清有些不知所措;在狹小的車廂內她獨自一人,眼眶裡蓄滿打轉的淚,視線模糊大片,卻終究還是咬咬牙,用帕子擦壓過眼底,在淚珠於臉上留下痕跡前擦拭乾淨。
衛延盛厭惡自己至此,於新婚之夜拋下自己,當著守門丫鬟的面揚長離去,絲毫不顧及自己的臉面。
若不是守門丫鬟是自己的陪嫁丫鬟阿蘭,舒長清或許真的要狼狽的受流言蜚語影響了。
但或許這多多少少漏傳了一些到了皇上耳中,第二天在自己同衛延盛前來覲見皇上皇后時,衛延盛便被皇上單獨叫走了去。
也不知說了什麼,說了多久,只是舒長清回府之時,衛延盛便已早早歸府。
據小廝打聽,衛延盛從宮中回來後便面色極差,下唇被咬的毫無血色,把自己關在書房裡砸了不少東西。
舒長清遣丫鬟往書房裡送了幾次吃食,又叫小廝在書房四周連夜挑燈,在不少丫鬟小廝的目光下,回房中點燈靜心謄抄一夜佛經。
第二天,舒長清身邊的大丫鬟阿蘭對府中下人稱,昨日進宮,陛下對皇子提及江南水患已決堤崩潰,兇猛洪水弒民數千,投金千萬卻被潛在的貪官汙吏們蠶食;殿下心繫百姓,憂國憂民,一時恨自己無法親身改變民眾命運,於書房苦讀思慮整夜未宿,而自己則素衣跪坐謄抄一夜佛經,願為水患受災民眾祈福。
流言一出,很快便從府裡流傳到了坊間,且越說越玄乎,越傳越奇特,硬生生將衛延盛塑造出了一個明賢皇子的模樣,心繫天下憂國憂民,風頭居然一時大盛,口碑甚至超過了太子,還有不少人紛紛稱讚兩人是天作之合,天造地設。
衛延盛知道這是舒長清的手段,但他不可能會為了下舒長清的面子,而白白浪費掉宣傳自己好名聲的大好機會。
衛延盛雖然討厭舒長清,甚至厭惡她,但他心裡有比愛情更重要的東西:權力。
趁著這個風頭,衛延盛的幕僚們暗地裡又推波助瀾了一把,藉機打壓了一下太子黨的那些死對頭們,又以皇子衛延盛的名義對水患區域施以援手,散發食糧衣物。
一時間,人們對衛延盛更是紛紛稱讚。
緊接著,一個月後。
沈家三嫡女,沈嬌出嫁給今年的狀元郎杜斌。
而衛延盛,則在沈嬌成親的當晚消失不見。
那晚阿蘭悄悄來到主院內向舒長清通知,殿下不在書房,也未曾收到殿下要出門的指示。
舒長清點點頭,示意阿蘭此事不能叫他人知曉,要封好眼線。
阿蘭退下後,舒長清淺淺嘆了口氣,坐在院子裡久久未動。
直到手裡茶杯徹底冷下,頭頂肩上落滿桃花瓣。
他那日如此癲狂,原是因為從陛下那裡得知了這門婚事。
陛下應當是想讓殿下徹底死心,不可再為兒女情長毀了其他。可惜帝王心卻終究是沒琢磨透他人尚且敢為愛情奮不顧身的勇氣。
舒長清深深吸了口氣,抓著杯子的手緊了緊。
不能失態,不能犯錯,不能露出一絲叫他人可以抓住的把柄。
今日……本應當是自己的生辰的。
3.
舒長清出生的時候,命數並不好。
青雲寺的大師替尚在襁褓中的女嬰算了一卦,算出這女嬰將來命運坎坷,多受蹉跎,且處處有難,若是行事不妥,還會有血光之災。
這卦一出,脾性急的父親就差點拿起他的槍桿來捅了這大師,母親則悽悽切切的痛哭起來。
舒家女兒就這麼一個,還算得如此命數,這叫人怎麼接受?
大師斟酌著,又是念念有詞又是畫符潑酒,終於給夫妻二人出了個主意。
對外宣稱個假的生辰八字,一個吉時,一個有福的八字;對內則將此生辰寫在黃紙上燒成灰,給女嬰喝下,並要夫妻二人從小教女孩行事端正,不碰武不動刀,止步於書房,停留於閨閣,由此才可堪堪逆天改命。
舒家夫妻忙不迭地答應。
舒長清小時候不懂得母親為何總給自己尋來最嚴厲的管教婆婆,一舉一動都要像是被戒尺衡量似的行動;若有分寸不妥,便是厲聲訓斥和掌心捱打,直讓舒長清眼淚汪汪,委屈難言。
一次幼時,也許是孩童天性,舒長清終於忍不住管束,在一次熱鬧集會的日子裡,偷偷溜出了府。
那一日在舒長清的記憶中永遠鮮活明亮,處處是明豔的色彩;縱使日後多少次她路過了同樣的街道小攤,卻再無當時的心情。
那一日尚年幼的她好奇貪婪的注視著一切,享受著屬於孩童的放肆樂趣,徹徹底底的體味了一把快樂的滋味。
但在鬧市街頭,一個獨行的小女孩到底是會引起歹人的注意。
在舒長清還沒回過神來,她的胳膊就被人抓住了,捏的生疼,以足以讓她跌跌撞撞的力度扯著;一個佝僂的婦人凶神惡煞的衝她吼,「賠錢貨,你又往哪跑去?莫要再鬧,隨娘回家!」
她驚恐的眼淚都要掉出來,支吾拒絕,可零碎的語言根本鬥不過那婦人,讓她只能無助的被拖拽著走。
直到有人反方向拽住了她。
那也不過是個半大的孩子,穿著華貴,一臉意氣風發。他一邊牢牢拽著舒長清另一隻手,一邊嗤之以鼻的對那婦人開口。
「這姑娘生的如此膚嫩貌美,怎的會是你這乾癟婦人的孩子?你莫不是個拐孩子的人伢子吧。」
那婦人頓時惱了,嚷嚷著讓小男孩莫多管閒事,甚至還裝模作樣的抬手要打人。
不過很快就被一群暗衛摁住了。
那時舒長清才知道,那時救了她的是當今三皇子,年僅九歲的衛延盛。
他救了他,又送她回府,臨走前還笑著同她說,外面危險的很,小姑娘莫要隨意外出。
舒長清只記得自己呆呆的看著衛延盛離開,似乎什麼都反應不過來。
之後的事,便是自己被母親哭著打了許久。
那還是自己第一次見母親哭成那樣,全然沒了平日的模樣,對自己又哭又罵,又是撂下狠話,說不願再要自己這個孩子。
直到自己也終究是慌了,哭喊著抱上母親的腿,垂頭認錯,再與母親一起抱著痛哭。
後來,後來母親和年幼的自己說了許多當時無法理解的事情;唯一清楚記得的,那便是自己原本的生辰時刻,是個糟糕到所有人都想要隱瞞的秘密。
而後愈發長大,自己也漸漸可以理解父母的苦衷了。舒長清並不恨父母,相反,她覺得這很好,這對她來說,父母做了正確的決定。
她久坐在桃花樹下,靜靜的守著那壺冷下去的茶。
身後凌亂的腳步聲傳來,有人從背後猛的抱住了她,刺鼻的酒味襲向她鼻腔。
是衛延盛,不知何時回了府,又不知何時入了院門。
舒長清還在思考他這一路是否叫太多人看見,自己明天又要如何替他遮掩。她的思緒被打斷,衛延盛慵懶的嗓音貼在她耳邊響起。
「西貢的月牙白……不錯,好品味。」
男人的嗓音裡帶著醉意,有一絲酥,吹在耳邊癢癢的,叫舒長清垂下眸子,下意識躲了躲。
「殿下若想品嚐,臣妾便再沏一壺;這壺已經冷了,喝了對身體——」
她話音未落,男人便抓起冷茶,就著壺嘴一飲而盡。
茶水從他嘴角淌下,在舒長清的肩頭打溼一小片。
令人不適的冷意。
「冷茶只配遲來者,倒適合我了。」衛延盛自嘲的笑,隨手摔了茶壺到一旁後,猝不及防的撈抱起舒長清,跨步往屋內走。
舒長清倒抽口氣,卻不敢吱聲,只是緊緊摟住了衛延盛的脖子。
她不敢叫嚷,生怕引來不必要的關注。
屋內,衛延盛扯下床簾薄紗,壓在舒長清身上。他沒有急切的動手,只是一動不動了片刻後,似醉非醉的忽然問了一句。
「你到底圖我什麼呢。」
舒長清垂眸。「殿下深得聖心,乃當今皇位唯一合適的後繼者人選。舒家代代為黎國守衛邊疆,臣妾願與殿下結姻,以示舒家忠誠,以表未來……」
她話語未落,面上一側忽然重重的捱了一耳光。
衛延盛或許並沒有用那麼大力氣,也許對衛延盛來說他大概根本沒用力;但那耳光還是抽懵了舒長清,在她面頰一側上迅速留下了通紅的指印。
她慢慢的,慢慢的回頭,對上了衛延盛猩紅的,盛著醉酒後明顯怒意的眸子。
「就因為這些可笑的理由,你們便要棒打鴛鴦,拆散他人……你們有心嗎?你有考慮過我的心情嗎?我不是你們攀附權勢獲得聖寵的工具,我愛的女孩今晚將歸於他人,而我卻不能作為她的男人度過餘生!」
他越說越激動,怒意到後面根本壓不住。
洩憤似的,他撕開了舒長清的衣裙。
在綿長的疼痛交織下,舒長清感覺自己現在無非是一副空蕩蕩的軀殼罷了。
她盯著頭頂上微微搖晃的簾子,眼角有微涼的淚流出,很快隱沒於她的髮間。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她回憶起自己幼時第二次見到衛延盛的時候,他們隔著宮宴的桌子對視,那個小男孩衝她眨了眨眼睛。
她回憶起自己偷偷告訴了衛延盛自己真正的生辰,忐忑不安的女孩生怕被男孩厭惡或者視作不詳,卻在幾日後,自己真正生辰的那一天,等來了男孩親手挑選的禮物。
那是一把桃花簪,樸素卻簡潔大方。
她記得男孩塞給了自己禮物,一臉意氣風發。
「我斷不能允許他人如此對待你的,哪有那麼多迷信的話?呸,一群糊塗人罷了!你的生辰好得很,此刻正值桃花開,怎會有不詳血光之兆?」
那時候的衛延盛,在自己眼裡閃閃發光。
她回憶起這個閃閃發光的小英雄,在那不久後,一臉驚喜的貼著耳朵偷偷告訴她,他喜歡上了沈家的那個姑娘。
她記得他說,「長清,我將來定要娶她。」
今夜,偌大京城,萬家燈火。
沈家三嫡女與當今狀元郎杜斌成親同房,喜結連理。
三皇子府,舒家長女第一次落紅。
4.
那晚瘋狂後,舒長清足足有數月沒和衛延盛正面打過交道。
也許是衛延盛在刻意躲著她,也許是她刻意躲著衛延盛,兩人藉著聖上下達的治理水患的旨意,彼此心有默契一般的開始了無聲的合作。
衛延盛在外奔波,而舒長清在內打理。
衛延盛聯絡各地災區,檢視水患,修理堤壩,嚴查貪汙;舒長清鞏固府上名聲,戒齋數日,為逃亡來京城附近的難民們施粥。
衛延盛名聲大起,在完美解決了這次水患後,得聖上賜號,封為賢王。
衛延盛匆匆回京後,回府上不過是為了拿點卷軸書籍,卻不湊巧的和舒長清在拐角處相遇了。
兩人皆沒有開口說話,明明是夫妻此刻卻比陌生人之間還要冷漠。
衛延盛打量著她,舒長清看起來更瘦了些,顯得她愈發弱不禁風;他的目光停留在舒長清的面頰一側,那上面早已不見任何蹤跡。
他在那一夜後記得自己的瘋狂和過分,更別提在第二天狼狽似的逃離了那個現場。但最讓他不敢面對的是,在那一刻他心中對舒長清的愧疚心疼,遠遠超過了對沈嬌的背叛感。
他素來覺得自己是偉大的,試問哪個男人可以為了一個得不到的女人守身如玉?
可等他真的破戒的那一刻,他居然沒有多少對沈嬌的歉意,反而只一個勁的反思自己,為何如同禽獸一般那樣對待舒長清。
幸而隨後不久他就接到了聖旨,匆匆離開京城。
他一頭扎進工作,恨不得用工作麻痺自己。
但他還是無法抑制自己去打聽京城的訊息。
在得知舒長清操持得當後,他居然有一絲欣慰和滿足。
因為有舒長清在,自己才會在這般焦頭爛額的事情中不必憂心京城裡的事。
他聽說舒長清戒齋祈福,偷偷遣人往府內送了許多補身子的藥;他聽說舒長清在京城外打著皇子府的名義接濟難民,又暗地裡增派了人手保護她安危。
也許是因為良心譴責,又或許是因為她是自己的女人,衛延盛發現自己開始無法對舒長清狠下心來。
而此刻與她在府中相遇,衛延盛端詳著舒長清,卻又不知該如何開口。
斟酌片刻,他訕訕道。
「近日身子如何?」
「託王爺的福,臣妾身體並無大礙。」一如既往中規中矩的回答,稱謂恰當的改了。
似乎又陷入了尷尬的沉默。
衛延盛咳嗽一聲,還沒來得及開口,舒長清卻又道來,「不久後便是皇后娘娘操持的春華盛宴,屆時雖並非強制要求參加,但此次宴會將邀請晉國特使,以做兩國友好往來之示。還請王爺斟酌考慮參加。」
「…本王知道了。」衛延盛心不在焉的答道,繼而開口詢問。「府內還有什麼需要打點的,儘管開口。」
舒長清微微頷首。「謝王爺詢問,府內暫無短缺。只不過…」
「只不過?」衛延盛眉頭微動。
「只不過京城各貴女名冊已送達,臣妾憑家世背景以及容貌品德為王爺挑選了些許,但真要負責甄選還請王爺自己過目。」
此話一出,衛延盛臉色就沉了下去。「本王娶妻才過了多久,未至一年便如此急著往府中塞人?看來是本王高估了你對家族臉面的看重,倒也不怕他人嚼舌根。」
舒長清面色如初。「臣妾趁王爺在外奔波治理水患的期間內教京城名貴們均信賴王爺為人正直,且以妾身母家擔保,為王爺在百姓中博得了好名聲。王爺斷不必擔心儘早納妾會取得壞名聲,臣妾以明禮懂教的標準尋來的貴女名單,現如今京城上下皆以為王爺不計男女之差,願廣聽珍言,納賢之舉更甚至妾室都要求懂得教義禮儀,更何況幕僚乎?由臣妾親自挑選妾室更是展現了王爺家風清正,婦人無妒,他人自然更無權對王爺家事指指點點。」
她一口氣說了一大段,聽起來無懈可擊,利益關係更是羅列的清清楚楚,叫衛延盛竟然一時間無法反駁。
他只清晰的記得她最後那句,“婦人無妒”。
衛延盛緊緊盯著舒長清的面色,試圖在其中找到些許蛛絲馬跡。
但是沒有,她沒有絲毫的神色變化,連嘴角的弧度都是那麼完美,像一張精細的面具一樣,令人完全挑不出錯。
衛延盛有些氣餒,旋即是揮之不去的煩躁。
他不耐煩的擺手。「本王知道了…還有別的事嗎?」
舒長清望著他。
「沒有了,王爺。」
衛延盛轉身便想離開此處。可前走了幾步後,他忽然又折返回來,居高臨下的瞧著舒長清。
她一動未動,保持著垂首的姿勢,像是還在等待他離開。
衛延盛覺得,自己本來應該是想要好好同舒長清說話的,他在遠離京城的那幾個月裡就一直在這麼打算了。
可話說出口,就完全變了味。
「你就這麼迫不及待的往我床上塞女人。」他聽見自己貼在舒長清的耳邊,用只有二人才能聽見的聲音咬牙切齒的說道。
從遠處看,不過像是夫妻二人在耳鬢廝磨。
「你自以為做的滴水不漏,殊不知在我看來卻更多像是畫蛇添足。我不需要你,也不需要舒家給我撐腰,你記住這一點。」
衛延盛起身離開,大跨步的離開。
在他身後,垂眸低頭的舒長清保持著恭送的姿態,捏著裙角的指尖卻微微泛白。
在某個瞬間或許衛延盛是在心裡希望她能叫住自己的,或打或罵,至少鬧一鬧,指責他的態度或者其他,都比舒長清現在這樣一根木頭似的要強。
但是沒有,王妃端正的站著,任由他離開。
5.
衛延盛最後還是從舒長清給的冊子中挑選了一個姑娘。
是一個小官小戶出身的年輕女子,姓李;知書墨,會樂器,很標準的大家閨秀。
但是舒長清知道為什麼衛延盛會選她。
因為長得和沈嬌的確太像了。
平日裡便有七八分像,若是回房熄了燈,那就更是差不多有九分像。
衛延盛的心思,著實太容易猜。
舒長清清點好東西后,合上匣子,深吸了口氣。
她身子不好,血氣不足,光是站久了大口呼吸一下,都會覺得頭暈目眩,眼前發黑。
阿蘭擔憂的在一旁扶住她。「小姐……」
「住口,是王妃。」
舒長清低聲呵斥了阿蘭。阿蘭不情願改變稱謂,從前不喜歡喊皇子妃,現在不喜歡喊王妃。
看著自己的陪嫁丫鬟難過的低下頭一聲不吭,舒長清嘆了口氣,也不好再教訓她什麼,只是低聲開口道。
「這王府內外多少雙眼睛盯著我的一舉一動,你若是叫他們抓住了口舌把柄,可如何是好?」
阿蘭心裡多少不情願,此刻也只能低聲說是,卻偏過頭在舒長清瞧不見的地方里偷偷紅了眼眶。
自己的小姐,脊骨從小便挺的這麼直。
就算自己要受委屈,也絕不會讓他人看出來。
那位姓李的妾室自打入府以來,衛延盛倒是並沒有像舒長清心裡想的那樣,夜夜逗留。僅僅是剛入府的那晚留宿一夜,隨後似乎是公務纏身的樣子,時常不在府內了。
姓李的姑娘全名叫李薇,在第二天前來見舒長清的時候,舒長清便從她臉上瞧見了顯而易見的失落。
看來衛延盛沒有做那事。
舒長清垂下眸子,接過李薇手裡的茶。
兩人短短交談片刻後,李薇像是斟酌著開口道。
「聽聞王爺公事繁忙,以後王妃若是乏悶,妾身願意時常陪王妃說說話,或是彈琴做詩,這些妾身都是會的。」
舒長清愣了愣。「…能有你這番心意便是好的。」
李薇斂眸。「王妃哪裡的話…妾身能看出來王爺與王妃伉儷情深,妾身從不渴求王爺的寵愛,只求能安穩生活。」
舒長清眼睫動了動。
不知道衛延盛和她說了什麼,竟讓她覺得自己和衛延盛是感情深厚的夫妻?
但不管如何,舒長清是不會戳破這個謊言的。
她保持著端莊的微笑,點頭應下。
「你大可不必憂心,王府會給你富足生活的。」
不給過多的資訊或者保證。
不要犯口舌上的錯誤。
而後幾天,衛延盛倒是會夜間回府,卻不去李薇那裡,也自然不會來舒長清這裡。
本來若是不相見,便不會有爭執的可能,但人在同一屋簷下,怎麼可能一直不見?
又過了兩三日,舒長清要去青雲寺參拜上香。
本來那一日本就是從簡,可在她準備出門前,卻遇到了衛延盛。
對方看見她也是一愣。
兩人之間每次都是舒長清先開口。
「王爺日安。」
「你做什麼去?」
「臣妾去青雲寺上香。」
隨後便是沉默。舒長清垂下視線,等著衛延盛讓自己離開。
但對面的男人不知怎的,沉默片刻後,竟是開口說道。
「本王也隨你一同去。」
舒長清驚詫的抬頭,一時間居然有些摸不準衛延盛的心思。
但男人並沒有過多言語,只是遣派下人去做些準備,隨後自己便要往馬車的方向走。
舒長清這才有些遲鈍的跟了上去。
在上馬車前,衛延盛回身,伸出手來要扶舒長清上馬車。
男人寬厚的手掌有些溫熱,還帶著握劍留下來的繭。舒長清搭手在他手心的瞬間,下意識瑟縮一顫。
她想起來小時候,衛延盛也是伸手牽過她的。
但緊接著她想起了那一晚。
就是這手衝她毫不留情面的扇了過來。
她渾身一僵,迅速上了馬車,迅速抽離了手。
6.
一路上是兩人在狹小車廂內無言。
舒長清閤眼假寐,衛延盛卻煩躁的靜不下心來。
他沒想到自己會如此突然的脫口而出要和她一同前來,也有些懊惱自己的所作所為。或許是因為前一晚聽手下彙報了舒長清在京城為他做的那些詳細事,也或許是因為他開始認清這個女人是自己的王妃這件事。
嬌嬌兒已經嫁人大半年了。
她一定是夜夜和她的夫君纏綿,過的或許比自己想的要好。自己不能總是做那個沉迷過去的人吧?
但是……
衛延盛看了眼對面假寐的舒長清。這個女人為什麼連閉眼休息的時候都不會露出毫無防備的姿態?和嬌嬌兒不同,嬌嬌兒敢怒敢笑,鮮活靈動,可舒長清呢?像根木頭,時刻都端著架子。
但就是這樣端著架子的舒長清才能這麼好的幫自己打理了王府……
衛延盛懊惱的揉眉,內心的矛盾讓他下意識的就想逃避。
等到了青雲寺,衛延盛大步下了車,卻再沒回頭去扶舒長清下車。
舒長清怔了怔,但卻沒過多在意。
沿著石板路走,兩人隨著接待的小僧到了接待的屋子裡。小僧合手道了句稍等,便掩門離開。
又是兩人獨處。
舒長清不開口,衛延盛也不好開口。
但或許是過於寂靜了些,令人渾身不舒服。片刻後,衛延盛忍不住了。
「你時常來上香麼?」
他想起了自己治理水難的時候,聽聞舒長清時常去寺廟。
「此處讓人心思平靜。」舒長清答道。
「…是了,的確。」衛延盛喃喃。「我們過去似乎是一同來過的。」
沒有了自稱,舒長清抬眼看了衛延盛一眼。
那已經是小時候的事情了,過於久遠,舒長清以為衛延盛可能都忘了。
不,怎麼會忘呢,他肯定不會忘的。
他明明就是在這裡遇見的沈嬌。
衛延盛似乎陷入了對過去的回憶中,面色舒緩,低聲開口。「你莫不是不記得了,我們過去曾——」
緊接著他就被打斷,其中一個手下匆匆趕來,低聲附在衛延盛耳邊說了幾句。
衛延盛旋即起身,丟下一句去去就回後,跟著手下離開了。
他走後,舒長清一人跪坐於室內。
她也開始回想起兒時的那一天。
那一日是衛延盛帶舒長清過來的,說是這廟宇附近有隻肥的油光水亮的狸奴,他想抓來給舒長清瞧瞧。
男孩費勁的鋪網撒餌,在等待的時候又是上樹摘果,又是折花捉蟲,好不鬧騰。
舒長清就蹲在一旁眼睛亮晶晶的瞧著他。
直到那簡陋的陷阱處傳來動靜,男孩才拍了拍手,興奮的喊著「上鉤了!」,一邊衝過去瞧。
但被網住的哪裡是什麼狸奴?是個氣的瞪著眼睛的小姑娘罷了。
她被弄的灰頭土臉,卻還是氣勢不輸人的大喊。
「這是什麼勞什子東西?」
男孩不服氣。「是我做的捕網,用來抓狸奴的!你怎的破壞了我的網?」
女孩卻又笑了。「抓狸奴?你們這倒是有趣,我看起來像狸奴嗎?快快放我出去,我也要同你們一塊瞧瞧,這玩意能抓個什麼。」
那日初見,男孩就目光便被女孩徹底吸引了。
從此好似再也沒有回頭看過背後的小姑娘。
舒長清在自己的回憶中也像個旁觀者,只是靜靜地去回憶他人的故事。
自己那日後來如何了呢?是因為亂跑被母親斥責了,還是因為太過勞累第二天腿腳痠軟了?
她不記得了。
掩著的門推開了,舒長清抬頭,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大師。
她連忙起身行禮。
大師卻合手低頭。「不必如此拘謹。」
「是必要的尊敬和禮儀,大師莫要嫌。」
等對方入座後,舒長清還沒開口,大師便端詳著她眉眼,輕嘆。「…這麼多年了。」
舒長清怔愣,等著大師的下一句。
對方卻不語了,微微笑著替她倒了杯茶,轉移了話題。「瞧王妃似乎是心有憂慮的模樣?」
「近日身體總有不適,但或許不是什麼大問題。」
「王妃心有鬱結,緊抓不放,最後擾的還是自己罷了。」大師以熱水澆盞,佈滿褶皺的臉上露出苦笑。「所有的大問題都不過是從小問題堆積起來的。」
舒長清垂首。
「貧僧知王妃有過多壓力,但或許也是時候該考慮如何放過自己了。」大師正了正神色。「…王妃究竟在堅持什麼呢。」
聞言後舒長清也愣了。
她在堅持什麼?
也許是不敢正視這個問題,也許是太多的問題都是由此而來,舒長清幾乎是腳步踉蹌,稱得上是狼狽的以身體不適為由,不留答案,告辭離開了那處。
身後室內的大師未語片刻,低頭飲茶。
「距離貧僧算的那一卦,都過去這麼久了……」
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著離去的背影說道。
「命格未變啊。」
7.
舒長清是從寺內一個人回去的。
衛延盛不知去了何處,她一個人在馬車上靜靜等待了足有一個多時辰,爾後才低聲吩咐回府。
至於衛延盛究竟做什麼去了,舒長清不過問。
幾日後,皇后娘娘便以身子不爽利為由,召她入宮陪著說說話。
大概也不過是旁側敲打一些什麼吧,舒長清沒有多想,只是動身前往。
宮內,皇后半倚靠著美人榻,在她低頭屈膝行李前免了這些規矩。
「不必行禮了,來陪本宮解解乏。」
舒長清遲疑一瞬。但她沒開口詢問皇后為何不與後宮嬪妃們解乏,只是安靜的坐下。
皇后端詳著舒長清,眉宇間是讀不懂的複雜神色。「你看起來氣色不好。」
舒長清垂眼。「近日有些悶熱,勞煩娘娘操心了…娘娘最近聽說身子也不大爽利,可是累著了?」
「能有什麼累著不累著的…這宮裡哪有甚麼還需要本宮做的?」皇后不在意的擺手。「你不必同本宮說話如此拘謹,本宮和你父親頗為相熟,過去也有不少交情,放輕鬆些談話便是。」
舒長清微微蹙眉。她不曾聽過父親說過和皇后娘娘的交情,更是從來不知道有這層關係。
「嫁給盛兒,多少委屈了些吧。」皇后忽然開口道。
「…臣妾不曾覺得委屈。」舒長清下意識的開口否認。「殿下…咳,王爺很好。」
「是麼。」皇后不置可否的冷哼。
窗外有輕微的蟬鳴。
美人榻上的女人身穿華服,即便上了年紀,也還是能從眉眼中看出屬於過去的影子。
皇后忽然抬手,牽起舒長清的手來捏了捏。
她沒說什麼,只是示意所有宮女都退下。
等宮內稀稀疏疏的清空了,房門合上後,皇后才瞧著舒長清的眼睛認真的開口道。
「盛兒這孩子是有抱負的…他本性並不壞,只是時常不清楚自己真正需要和想要的是什麼。現在大臣中盛兒的口碑甚至超過了太子,而這大約也是為何陛下會匆匆立盛兒為王……」
舒長清一怔。
皇后卻又繼續說道。「宮內人多眼雜,本宮不好多說,只能透露你些許。你是個懂事的孩子,令人放心,你會明白要做什麼的。只不過,你千萬要記得一點。」
皇后附在舒長清耳邊說了些許什麼。
後來直到舒長清離開了皇宮,等到那扇大門在身後合上,她都久久沉默著,只是出神的瞧著車窗外。
她忽然很思念母親,很懷念過去在家中,不必憂慮太多,也不必肩負重任。
但時不同往日。
她應該明白的,早早在那日她向父親開口的那一刻,她就應該明白往後自己該走的路的。
回了王府,衛延盛倒是破天荒的在她居所。
舒長清還未行禮,就被衛延盛一把拽住了胳膊。
他擰眉。「不必了,只是來一同用晚膳。」
舒長清沒有過問為什麼,吩咐下人準備。
這頓飯著實怪異。
很明顯衛延盛是有什麼事想說,但又不開口,只是彆扭的悶頭吃飯。
舒長清不動聲色的為他佈菜。
後來等吃的差不多了,消食的茶端上來的時候,衛延盛終於開口了。
「你……入宮後和皇后娘娘說了什麼?」
舒長清蹙眉。「娘娘身子有些不爽利,天氣熱,臣妾陪她解解乏。」
「如此甚好。」衛延盛舒展開眉頭,旋即片刻後又問道。「幾日後的春華盛宴,晉國特使的確是會赴宴吧。」
「是的。」
「如此甚好。」
兩人雙雙又陷入沉默。
後來舒長清終於有些忍不住。「殿下可是有話要同臣妾說?」
衛延盛像是在糾結要如何開口,神色複雜了片刻;他斟酌著,隨後終於還是說了出來。
「陛下不久前透露過,有意指派人手南下,同季老將軍一同鎮壓南部蠻兵。」
「本王……我需要這個機會,希望舒老將軍可以在陛下推薦。」
舒長清直直的望去。
衛延盛似乎有些難堪;這是應該的,他之前明明那麼唾棄指責舒長清依靠家族勢力來強迫了這場婚姻,結果現在卻低著頭來請求舒家的力量。
但他得得到這個機會,這是個拉攏力量的好契機,他不能眼睜睜的看著其他皇子,或者太子,搶走這個機會。
現在他治理水難有功,名聲正好,若趁此機會,還能再———
「抱歉,王爺,恕臣妾無法答應王爺這個理由。」
衛延盛有那麼一瞬愣住了。
他根本就沒期待從舒長清這裡得到拒絕的回答。在他看來,舒長清這是欠他的;動用舒家力量為他所用才是應該的,但她居然拒絕了?
衛延盛喉結動了動,下意識的開口。「不能?你這是什麼意思?」
舒長清直直的看著他。「如今王爺名聲大噪,太子黨羽自然會有所提防;太子此時並無大錯,不至於讓陛下起了換嫡的心思。倘若王爺再奮力出頭,只會讓太子起了針對的心思,或者更甚,惹得陛下反感。王爺與臣妾成親,他人自然會認為舒家力量會為王爺所用,而舒家男兒們皆是戰場上有名的將領;倘若王爺再得到此次南下接近季老將軍的機會,王爺以為,陛下會如何想?」
衛延盛久久不語。
「所以臣妾私認為,」舒長清放緩語速,「此刻需得王爺按下風頭,任由其他人搶奪這個機會。治理水患是一回事,可接近頗有實力的季家便又是另一回事了。王爺,機會重多,不必拘泥於這一個。」
衛延盛抿唇。
這些話,幾日前他的幕僚中也有人如此說過。
但不乏有反對的聲音,甚至有幾個攛掇他務必要爭取這個機會,因為機不可失,說的他熱血沸騰。
可冷靜想想,舒長清說的是對的。
自己為什麼腦子一熱,血氣上湧的就打算去搶這機會?
衛延盛面色肉眼可見的陰沉了下來。
自己的幕僚黨派中,有心思不正的。
直到面前的舒長清喚了他一聲,衛延盛才回過神來。
他看著眼前自己的妻子,心裡除了僥倖,還有些後知後覺的後怕。
為什麼在聽見她拒絕的那一瞬間,自己暴怒的恨不得又對她說那些傷人的話?
那刺人的態度,別說是舒長清這種姑娘家,就連衛延盛聽了都或許會倍感難受。
但也是這樣,他也意識到,舒長清的確是一個合格的妻子。
一個非常,非常合格的妻子。
嬌嬌兒不再是他的了,以後也不會是。
但眼前的人以後會是他的,一直是。
自己為什麼不試著接受她?
如此想著,衛延盛第一次露出了柔軟的神色。
「…王妃說的對。」他低聲說道,眼底流露了讚許滿意的神色。「不愧是京城才女啊。」
面對他最後的調侃,舒長清只是淺淺笑了笑,低下頭去。
燭光下,女人纖細的脖頸顯得格外雪白。
衛延盛喉結動動,聲音沙啞了幾分。「…長清。」
舒長清身為女人的敏銳立刻察覺了對方的意圖。
但她卻選擇了避開。
「王爺,」她不動聲色的往後避了避。「近日不巧,恰逢臣妾身體不妥……」
衛延盛也回過神來,咳嗽一聲,站起身。「如此,明日記得叫小廚房溫些暖粥來。本王…我就先離開了。」
黎國男子,素來在女人來月事的時候要選擇隔屋避嫌的。
舒長清起身送衛延盛離開,目送他和小廝侍衛們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
她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拒絕了衛延盛。
也許是那一晚太過於痛苦,令她不禁對做那事有了恐懼似的心理。
那種感覺…真的不願意再受一次。
她抓著裙角的手緊了緊。
在當初向父親請願嫁給衛延盛的時候不就決定好了要接受一切嗎?現在又退縮了?
但是畢竟一朝被蛇咬。
她所求不多,因為她知道衛延盛痴心沈嬌數年,若不是造化弄人,他們應該是會修成正果的。
她所求的只是相敬如賓,這便足夠了。
舒長清從小就不是一個會得寸進尺的人,她一直都清楚一個道理。
適可而止。
8.
春華盛宴當日。
自打衛延盛那晚從舒長清的屋內離開後,兩人關係似乎緩和不少。
衛延盛時不時會與舒長清來共同用膳,偶爾也會留在小書房裡帶著。
兩人之間迎來了難得的平靜。
李薇來給舒長清請安的時候,都會掩唇調笑兩人的關係,似乎是誤會了不少東西。
但舒長清也不多做解釋。如此便是好的,兩人之間有起碼的尊重,這也不錯。
尋常夫妻不也大多如此?
春華盛宴當天,舒長清做盛裝打扮,格外重視自己的髮飾衣裙,生怕太過樸素叫人看了王府笑話,又生怕太過惹眼,平白無故搶了他人風頭。
她和衛延盛抵達王宮的時候,本是相安無事。
舒長清自若的和那些夫人們坐在一處,舉止得體規矩大方,談吐優雅知性,叫他人絕挑不出一絲錯。
直到有熟悉的聲音在背後響起,帶著點久別重逢後的小小欣喜,又帶著點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
「長清…!」
舒長清頓了頓,微微側過身望去。
一襲豔麗衣裙的姑娘,梳著婦人髮髻,卻依舊洋溢著屬於少女的動人神采。她是如此明朗,像一簇陽光般落在此處。
她驚喜的朝舒長清走來,伸手就欲挽她胳膊。「好久未見了…!」
但她挽了個空。
舒長清淡淡避開。「杜夫人自重。」
沈嬌的笑容有那麼一瞬僵在了臉上。
其他夫人們雖然面上帶笑,卻難免在笑容裡多了點譏諷的意味。
其中一位口舌快的,還不忘提醒沈嬌。「這可是賢王妃,怎麼還能如此隨意?」
沈嬌面色有些尷尬,但還是撐著笑。「我同長清自幼認識,她是清楚我的脾氣的。這些條條框框的規矩對我來說素來是有些繁縟,但長清是不會怪我的。」
她一點也沒變。舒長清垂眼。
下一刻,她就聽見自己清冷的聲音響起。「時不同往日,杜夫人。既然已經嫁為人婦,自然需要多少遵守點禮節了。更何況現在是在盛宴中,莫再喚我名諱,需稱呼賢王妃了。」
沈嬌咬咬下唇,眼底的光似乎暗了一瞬,面上的委屈毫不掩蓋。
她看著舒長清,嘴上雖然應了,但眼底對舒長清的指責和責怪過於明顯。
若是放在以前,衛延盛定是要心疼了。
但此刻,衛延盛不在這兒。
沈嬌有些情緒低落的行禮離開,也不知去了何處。
或許是去尋她夫君了也說不定,舒長清想道。
其中一位夫人吃笑出聲。「聽聞杜家夫人向來脾性直爽,卻不曾想沒規矩成這樣。」
「的確,一上來便喊王妃的名諱,還瞧著不情不願的,像是誰教她受委屈了似的。」
夫人們又笑起來,舒長清只是勾了勾嘴角,並未言語。
爾後便到了宴席開場的時刻,夫人們紛紛起身回到了自己夫君身邊去入座。
按官職等級劃分的座位,舒長清自然是可以坐在高處的,甚至離皇帝皇后還挺近。
她注意到了身邊衛延盛的有些心不在焉,視線不斷向下座瞥去。
正所謂之前未曾見到的時候便不會去想,如今忽然和心上人重逢了,五味成雜到被不斷搶走注意力嗎?
舒長清抿唇。
晉國特使上前來向陛下行禮,並端上了以表友好的禮物。
陛下看起來心情大好,笑容滿面。
舒長清打量了下這位特使。
身材欣長結實,穿著和黎國不同的服飾,鍍著金線的黑色衣物很好的修飾了他的身材。有著晉國特色的長相,五官鋒利立體,帶著侵略性,薄唇總是若有若無的勾著笑。
但最獨特的,還是他那雙狹長的淡色眸子。
在黎國從不曾見過淡色瞳孔的人,舒長清便有些好奇的多打量了一眼。
猝不及防的和特使對視上了。
對方似乎還促狹的笑了笑。
舒長清立刻有些狼狽的移開視線。
陛下和特使交換完了象徵兩國友好交際的禮物,隨後便是請他入座,宴席開始。
衛延盛自打入座後便一直是心不在焉的模樣,只是頻頻打量下座的視線有些過於明顯頻繁,令人有些心煩。
但舒長清煩的不是他不停的看,而是害怕被他人看出什麼端倪。
他們的位置很靠上,距離太子和承王很接近。唯一兩個封了王的皇子就只有衛延盛和二皇子,剩下的便暫時還未得到稱號,因此坐的地方自然也有些距離之分。
特使的位子在太子邊上,在衛延盛的對面。
男人們在舉杯交談,說的無非就是些客套話。舒長清瞧見太子妃和承王妃也只是聽著,時不時略略小幅度點頭附和,並不插話。
遂她也如此。
特使此刻起身舉杯,開始向各位敬酒。
來到衛延盛這桌時,隨著衛延盛起身飲酒,舒長清也連忙端著杯子敬了敬,準備飲盡。
對方微微咳嗽一聲,打斷了她動作。
「這是晉國的特色酒。」特使那帶著點笑意的聲音響起,「賢王妃看起來年歲不大,大約是飲不慣這種酒的。」
舒長清怔了怔,抬眸對上了男人的淡色眸子。
「不必擔心是否這會有些失禮,在晉國婦人不飲酒是很常見的事。賢王殿下自然是會為夫人分憂的。」特使又笑笑。
衛延盛瞧了瞧舒長清手裡的杯盞,倒也不覺有什麼大不了,但還是點頭接過,代舒長清飲盡。
「賢王好氣魄。」特使誇道。
「過譽。」
等特使離開前往下一桌,兩人再度入座後,舒長清忍不住低聲向衛延盛詢問。
「這晉國的特使,倒是瞧著不像是尋常臣民。」
衛延盛點頭。「他本就不是尋常臣民。晉國為了表示對此次交好的重視,特派了他們的二皇子過來。」
舒長清點頭。
原來是皇子,怪不得。
9.
盛宴逐漸到了尾聲。
衛延盛似乎有些微醺,但絕還不至於到失態的程度。
只是他盯著下座沈嬌方向瞧著越來越明顯了。
爾後更是在瞧見沈嬌離座後,也站起身來尋了個蹩腳藉口,說是去外面吹吹風散散酒意,便也跟著後腳離開了。
舒長清感受到了來自皇后娘娘有些擔憂的目光。
她抿唇。
衛延盛一路跟出去,終於在迴廊上瞧見了沈嬌。
她似乎是因為不小心把酒水潑到了身上,在等著宮女去拿東西擦拭或者更換,正獨自靜靜的坐在那。
衛延盛站在不遠處,神色複雜的看著她。
自打她成婚那晚,衛延盛隔著遠處瞧見她穿著紅嫁衣的身影后,便再也沒有見過。
直到現在。
他一直忍著不去打聽她的訊息,也忍著去主動見一面的衝動。
但是…
他有些痴的看見沈嬌,捨不得挪開視線。
從青澀時期最初愛上的那個人,愛了這麼多年,怎麼可能就這麼輕易的放下?
他小心翼翼,不敢驚動沈嬌。
但她還是看見他了。
沈嬌眼睛一亮,站起身來。「盛哥哥…!」
她旋即像是意識到了什麼,苦澀一笑,提裙屈膝。「賢王殿下。」
衛延盛擺擺手,匆匆上前把她扶起。「你不必在我面前如此拘謹,以前不必,往後也不必。」
「但我們早已身份不同…」
「不必如此。」衛延盛喃喃。「只要你願意,你只管喚我盛哥哥便是。」
他頓了頓,但終究還是沒能把嬌嬌兒三個字喚出口。
他看著沈嬌梳的婦人髮髻,心裡發酸。
也許是酒勁上來了,竟然有些眼紅。
「盛哥哥倒是和以前一樣,我還以為會都物是人非呢。」沈嬌苦笑。
「都?」衛延盛一怔。
「如今盛哥哥和…長清成親,我也和杜郎成親,定是和過去有所不同了。」沈嬌有些落寞的垂眼。「我過得很好,盛哥哥看起來過得很好。如此就足夠了,我相信長清待你是極好的,她從過去就對你……」
「夠了。」衛延盛打斷她。「這些都不必再說,時不同往日。」
沈嬌一愣,隨後笑笑。「是了…長清也是這麼說的。」
衛延盛看著她。
但沈嬌沒再說了,只是淡淡掙開衛延盛扶著她不放的手,行了個標準的禮。
「賢王妃舉止得到,品行端正,和盛哥哥是極配的。我不求其他,只求盛哥哥心願順遂,和…賢王妃,長久圓滿。」
她抬眼,衛延盛瞥見了一抹她眼底似乎若有若無的溼意。
這令他心頭一動,不禁就要伸手去抓她。
但沈嬌扭頭便立刻腳步匆匆的想要離開,從背後望去,還有幾分逃離的意味。
與此同時,舒長清也從宴席中出來,在花園內透氣。
天色晚了,獨屬夜間的清爽略略驅散了剛才室內的悶熱。
她不知道衛延盛去了哪,但大概是去追著沈嬌跑了吧。
舒長清嘲諷似的垂眼。
希望別被太多人看見他們拉拉扯扯的樣子就好了。
身側傳開細微的聲響。
「賢王妃在這兒獨自一人,是嫌宴席上有些吵了?」
舒長清抬眼望去,撞入一雙淡色眸子。
她怔了一瞬後,立刻站直身子行禮。「特使閣下。」
對方也回了她一禮。「賢王妃。」
舒長清有些侷促,悄悄拉開了點距離。「無非是有些悶熱,出來透透氣罷了。特使閣下怎麼也在此處?」
「和賢王妃一樣,透氣散步,順便藉機端詳明月,望能吟詩作賦,出幾首佳作。」
舒長清抬頭看了看夜空,一輪朦朦朧朧的月牙,不甚明顯。
「今夜明月可能要讓閣下失望了。」
她收回視線看向對方,卻看見男人像是才發覺似的,抬眼隨意的瞥了一眼夜空。「王妃說的是,此月無感,不好作詩。」
「那閣下…?」
「作不得那便不作了,不強求明月完整,那便只好耗到明日天亮,再做一首關於圓日的詩。」
舒長清有些無語。「…閣下所言極是,大多讀書人大約會苦等數日,只為等一個完美的圓月,到時候再吟詩作賦。閣下不受那些詩人的倔脾氣所束縛,倒也是一種自由。」
特使衝她彎了彎眸子,沒做評價。
舒長清覺得再和外男獨處下去,自己大約也會傳出不好的傳聞。這世道對女人不公,若是自己名聲受損,那可是有關身敗名裂的。
念及此,她欲開口告辭。
但還不等她說話,那男人又開口了。但這次不是沒頭沒腦的調侃。
「我與賢王妃似乎也頗有緣,能在此相遇。賢王妃不必端稱我為閣下,頗為生疏。太子妃和承王妃皆知曉我名諱,不若我也與賢王妃一說,日後賢王妃想如何稱呼,便是看賢王妃如何掂量交情了。」
舒長清下意識的要拒絕。
哪有這樣的道理?一個不甚熟悉的外男,還是他國特使,哪有這樣強硬態度的道理?
雖這人說太子妃和承王妃都知曉,但她還是不想太節外生枝。
可她還是嘴慢,沒能及時拒絕。
也或許是男人的淡色瞳孔太有迷惑性,一眨不眨的盯著舒長清的時候,叫她下意識猶豫了一瞬。
眼前的男人行了一禮,保持著最禮貌規矩的距離。
「晉國二皇子翟承訣,見過賢王妃。」
10.
舒長清沒有在花園久呆。
也許是那雙含笑的眸子盯的她有些羞,或者也許是她不太適應和其他外男獨處,更何況對方是他國的特使。
她匆匆告辭,轉身往擺宴席的宮內走去。
但在路過迴廊的時候,舒長清卻猛地停下步子來。
迴廊裡緊緊擁在一起的兩人的身影,實在是太熟悉不過了。
熟悉的有些扎眼。
衛延盛緊緊抱著沈嬌,懷裡的女人似乎在低聲啜泣,面色泛紅,緊閉著眼。
兩人站在兩處通風的迴廊裡,就這樣旁若無人的相擁。迴廊的不遠處還有兩三個宮女,正不安的垂著頭,一副不敢看的模樣。
舒長清眯眼,攥緊裙角。
還沒等她冷靜下來,她便已經捏著裙角向他們走去。
「王爺似乎是飲多了酒,遇見故人後亂了分寸。夜色也深了,該回府了。」
舒長清的聲音猝不及防的叫兩人嚇了一跳,衛延盛一把推開懷裡的人,轉頭對上舒長清頭一次帶著冷色的眸子。
他忽然有些莫名其妙的緊張,像是被抓包了什麼似的有些窘迫。但很快衛延盛便清清嗓子,低聲想要解釋。
「長清…」
我是愛看小說的數數:喜歡我的推文嗎?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排雷補充啊!!!想看更多精彩推薦記得點贊、關注、轉發哦!你們的關注和點贊是我最大的動力,我會持續推文,讓你們遠離書荒。想看什麼型別的小說可以在評論區留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