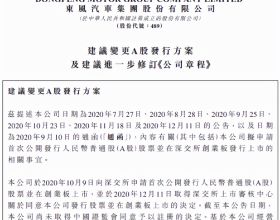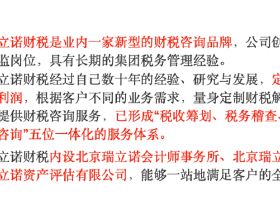在過去日本橫濱的街頭,有這麼一道起義的風景線,一個奇怪的老婦人整日在橫濱的街頭駐足、遊蕩。
婦人的體態佝僂,臉上塗著厚重的白色妝粉同時搭配著無比誇張的眼影,身著白色的紗裙,更為誇張的是腳上與年齡完全不相符的高跟鞋,惹得不知情的行人退避三舍。
婦人叫做西岡雪子,也叫做橫濱瑪麗,她是個沒有家的日本娼妓。
由於影響市容市貌,她被抓進警局二十二次,人們反感她,厭棄她,但是她卻始終從容優雅地守候在橫濱的街頭。
這位煙花女子在74歲的高齡仍在站街,街頭60年一直拉客,卻備受日本人尊重,這是為何?
西岡雪子
一、悲劇初始
瑪麗是二戰後日本初建的殘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國內滿目瘡痍,發動戰爭的國家自食惡果,受苦的終究還是國民,一夜之間無數的日本人失去了工作,流浪街頭。
本文的主人公西岡雪子,人們更喜歡稱呼其瑪麗。
1945年,瑪麗24歲,她出生於日本的一個富裕家庭,同樣也是無數個深受戰爭其害的家庭之一。
從小,瑪麗的父母便對其悉心培養,她知書達禮,精通彈琴、書畫、英語,在那時的人看來,完全是一個大家閨秀。
日本戰敗後,她的處境就變了,父親戰死,母親離世。
滿目瘡痍的國家,僅剩混凝土的殘骸還有扭曲外露的鋼筋骨架,如果仔細凝望,也許還有在街頭無人認領的屍體。
在女子地位低下的日本,弟弟為了霸佔家業,將其驅趕出了家門,她也成為了無數流落街頭的日本人中的一員。
在那時的日本,就業是很難的,男性或許能夠憑藉自己的力量找到為數不多的苦力工作,但是女性又怎麼能夠尋到工作的機會。
直到有一天,一則意外的招牌資訊映入瑪麗的眼前:“做新女性:涉外俱樂部招聘女性事務員,包吃住,高收入,限18至25歲女性。”
無法拒絕的優厚待遇加之廣告的政府官方背景,瑪麗不假思索地報名了。
她哪裡知道在這則招聘廣告的背後,一隻深淵巨口正在緩緩張開,將無數無辜的日本女性吞入腹中。
瑪麗去應聘了,她的容貌出眾,擅長樂器、書畫,更為關鍵的是她還會說英語,很快她便應聘成功。
瑪麗成為了慰安婦,發現真相的時候,為時已晚,她穿上了豔麗的服飾,等待著大批的美國大兵上門。
起初她還能夠哭喊,到後來她的雙眼無神,身體完全麻木了,就像被圈養的畜生一樣,失去了所有人的感覺。
二、荒唐與不公
瑪麗應聘的地方是“RAA特殊慰安措施協會”。
在宣佈無條件投降後,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將目光投向了戰前與自己關係不錯的美國身上。
美國成為了日本試圖避免戰後清算的救命稻草,美軍進駐日本成為了日本政府一番決策後的荒唐決定。
更為荒唐的還在後面,由於美軍進駐日本後時常發生暴力事件與強搶民女的事件,一味討好的日本政府最後便決定用少部分女性換取大部分的日本女性的安全,他們修築了慰安所,為美軍提供“消遣”、“服務”,可謂荒唐至極。
進駐日本的美國大兵大多都是一些補充兵以及在戰爭中被摧殘人性的大兵。
如同野獸一般,沒日沒夜地蹂躪這些在慰安屋內的女性,他們的手段殘暴至極並且拒絕使用安全避孕措施。
沒過多久,慰安屋內便有不少的女性染上了花柳病,不久之後,便徹底蔓延開來。
疾病的傳播導致了輿論的反映無比強烈,尤其是來自美國國內美軍家屬們的嚴正抗議,他們擔心這些美軍回國後繼續傳播性病,日本政府最終才關閉了各處的慰安場所。
但是這些慰安屋內的女性們後續生活該當如何。
這些進過慰安所的女性的餘生註定將受到種種歧視非議,患上花柳病的女性甚至面臨著極大的生命危險,她們成為了償還罪孽的犧牲品,莫名地成為了慰安婦,待一身傷痕後,又被慘無人道地趕到了街上。
儘管這些所謂的“接待”是有薪酬的,政府表面上宣傳這些“慰安婦”賺了很多的錢,但是實際上很大一部分的錢都被日本政府和機構扣下,加之後來日本的大通脹,餘下的錢根本無法維持日常生活的所需。
三、相遇與守候
隨著慰安所的關閉,瑪麗也流落在了街頭,和大多數的慰安婦一樣,沒有謀生的能力,沒有生存的資金,在惡劣的國內環境下,她們只能繼續這份行當。
她們站在美軍經過的街道兩旁,妝容濃豔,穿著性感的裙子,擺著性感的姿勢,這些站街攬客的女郎,被稱為“panpan”。
與這些行為性感風騷的攬客女郎相比,瑪麗倒是顯得有些不同,她從來不學著那些搔首弄姿的姿勢,她總是把自己收拾的乾乾淨淨,穿著一個潔白的復古的裙裝,撐著把小傘,舉止優雅,在眾多的攬客女郎中,顯得鶴立雞群。
瑪麗一口流利的外語和出眾的鋼琴技藝讓她在一眾“panpan”當中名聲大噪,到了後來可以算的上是當紅的“panpan”,周圍的人稱呼她“皇后”。
這似乎是瑪麗在那個時代下留下的最為深刻的印記,瑪麗正值當紅,維持生計後,但是她的臉龐卻少有笑容。
“我的人生早就已經死了”,這是她那時對自己所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可是她如今所作的一切都是卻都是為了這個麻木的軀體能夠活下去。
既然已經做了妓女,將來還有什麼是她可以期盼的,她總是這樣暗自想著,她已經好久沒有真正地笑過,一切只是為了活著。
瑪麗最快樂的日子是遇見了那個美國軍官後,如同枯木逢春一般,她如同一潭死水的內心泛起了點點波瀾。
和其他的客人不同,這個美國軍官似乎是第一個把她當成朋友的客人,兩人平等地交談,他談吐幽默,目光真誠而沒有一絲輕薄。
瑪麗頭一次感受到了愛情,他們私定了終生,瑪麗心中原本昏暗的未來似乎出現了點點光亮,隨後光亮慢慢擴散開來,無比明亮。
美國軍官吻過瑪麗的臉龐後,還送給了她一枚翡翠戒指,他說這是定情的信物,“多麼的幸福啊。”瑪麗的嘴角微微上揚。
1951年,瑪麗和相戀的美國軍官來到了橫濱,小日子沒過多久,美國軍官便收到召回國的命令。
縱然瑪麗萬般不捨,但卻是無可奈何。
臨別時,美國軍官擁抱著瑪麗,二人擁吻良久,軍官對她說:“瑪麗,等我,等我從美國回來就和你結婚。”
郵輪的汽笛聲響起,軍官帶著行李匆匆上船,站在船頭,他駐足良久,朝著瑪麗揮著手。
那一天的碼頭擠滿了人群,直至郵輪開動,瑪麗在簇擁著的人群中緩緩地追趕著船的方向,她呼喚著軍官的名字,“親愛的,我等你,永遠都等你。”
瑪麗追逐著,直到看不著船的影子。
瑪麗留在了橫濱生活,她相信心上人會再回到這個地方找尋她。
她找不到工作,於是便只能重操舊業,她在根岸家繼續工作,這裡是橫濱夜晚的象徵,男人們晚上齊聚於此。
軍官走後,瑪麗又恢復了那張難以靠近的冷豔面容,她從不刻意討好誰,但總是受到歡迎。
瑪麗有著自己的驕傲,她期待著有朝一日,自己的心上人,把自己接走,離開這個骯髒的地方……
時間一年又一年地過去,一年又一年的失望,那個在心中佔據重要地位的面容始終未曾出現。
1980年,根岸家在一場意外大火之中燒燬了,瑪麗又失業了。
她又重新流落街頭,但是她仍然相信軍官會回來找她。
瑪麗害怕軍官找不著她,便只穿當年相遇時的復古蕾絲紗裙,戴著純白的蕾絲手套。
原本清秀的臉上塗抹了厚厚的白色妝粉,眼睛用無比誇張濃郁的眼影包裹著,嘴唇常年是鮮豔的硃紅色。
在外人看來怪異且誇張,瑪麗絲毫不在意他人的看法,她之所以如此打扮,就是希望等到軍官回來的時候,能夠一眼就把她認出來。
為了生存,瑪麗繼續在橫濱招攬客人,她對客人說的最多的便是:“我什麼都可以給你,但是你不能吻我。”
四、歷經世事
歲月如刀,曾經美麗的瑪麗,容顏漸老,三十多歲的時候,她依然頗受歡迎,到了四十歲便很少有人找她,五十歲的時候,便幾乎沒有人找她了。
即便接不到一個一個客人,她也依然保持著那副奇異的裝扮,整日駐足於橫濱的街頭。
沒有收入自然無家可歸,奇異裝扮的瑪麗常常拖著自己的全部家當,出現在橫濱的街頭巷尾。
人們嫌棄她,厭惡她,避之唯恐不及,面對他人鄙夷的目光瑪麗熟視無睹,她保持著優雅,仍然堅持著雷打不動地出現。
橫濱的許多店家都把瑪麗拒之門外。
在瑪麗常去的理髮店,客人便常常跟老闆娘抱怨道:“如果她還來這裡做頭髮的話,我們就不來了。”
對此,理髮店的老闆娘只能夠抱歉地對前來的瑪麗說道:“請你今後不要來了。”
瑪麗有些失望地再次詢問道:“真的不可以了嗎。”
再次遭到拒絕後,她只是有些遺憾說道:“這樣啊,那好把。”隨即便一聲不吭地默默離開了。
幾乎所有人都嫌棄厭惡著與瑪麗一樣的街頭妓女,以瑪麗為代表的這些受到舊日本政府殘害的性工作者,似乎使得這些沉迷於昭和繁榮的日本青年思索起了不堪回首的過去。
瑪麗的存在似乎就像一面鏡子,時刻在提醒著他們日本那份罪惡的過去。
儘管大多數人都不待見瑪麗,但還是有少部分的溫暖的人,有好心人給瑪麗提供了一個睡覺的地方,一個大樓大廳內的長凳。
儘管是長椅,瑪麗依然十分感激,因為其他大樓的負責人都會驅逐她,只有這個老闆願意讓她留在這裡。
長椅是瑪麗的床,更是瑪麗的家,很長一段時間裡,瑪麗就靠著長椅將腳放在行李包裹上入睡。
她不願意平白接受這個在她看來寶貴的饋贈,因而每年瑪麗過年的時候,瑪麗都會給老闆寄一些小禮物,比如一張明信片、一條毛巾。
瑪麗常去的咖啡館,也有客人嫌棄她,老闆不忍趕走她,便為其專門準備了一個被子,瑪麗每次到咖啡館時,便會禮貌地說道:“請用我的杯子給我裝一杯咖啡。”
五、生命中的暖意
1991年的時候,瑪麗已經七十歲了,她結識了一個叫做元次郎的年輕人。
元次郎的工作也不光彩,他是個歌手,同時也是個男性娼妓。
元次郎的母親也是個娼妓,她在世的時候,元次郎很是厭惡自己的母親,不知道母親無奈的他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並且大罵不知廉恥。
母親去世後,他似乎漸漸明白了母親所承受的一切,但懊悔卻是來不及了。
直到元次郎遇到了瑪麗,母親的影子似乎又再現了,他像兒子對待母親那樣對待瑪麗,兩個素不相識的人成為了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
周圍人的閒言碎語、唾棄厭煩並不能阻礙瑪麗的生活,瑪麗在橫濱的幾十年都是這樣過來的,似乎沒有什麼能夠將她趕走。
瑪麗逐漸變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有導演上門邀請她拍攝紀錄片,她也欣然同意,她似乎很樂意分享自己的故事。
時間來到1995年,一場紛飛大雪後,瑪麗卻突然消失了,人們開始試圖尋找那個數十年來雷打不動出現在街頭巷尾的老太太,可是誰也不知道她去往何處。
瑪麗回到了自己的故鄉。
念頭是突然產生的,也許是人老了便會開始想念故鄉,瑪麗踏上了歸鄉的火車,一個人靜靜地離開,誰也沒有告訴。
瑪麗走了之後,整個橫濱的居民們這才發現似乎少了些什麼,多年來日復一日出現的拖著行李的佝僂老太似乎已然成為這個城市熟悉而又獨特的印象。
再次得到瑪麗的訊息是在六年後的一天,身患癌症靜靜等待死亡到來的元次郎收到了瑪麗的來信:我想回橫濱了……
元次郎很快便出院,第一件事便是前往瑪麗的故鄉。
在一處敬老院內,元次郎再次遇到了瑪麗,他像初次遇到瑪麗那樣,給她唱第一次見面時的那首歌。
瑪麗不再是那副怪異的妝容,她用回了自己的本名“西岡雪子”,變成了一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和藹老太太,在臺下一臉慈祥的微笑,默默地觀看著元次郎的表演。
2005年,瑪麗在養老院中安詳地離世了,她活到了八十四歲,手中依然戴著那個翡翠戒指,心中的遺憾一直留到了最後……
五、尾聲
在瑪麗去世後,由日本知名導演中村高寬執導的紀錄片《橫濱瑪麗》方才正式上映,瑪麗的故事一經播出便轟動了整個世界,一時之間反響熱烈。
這部以瑪麗為主人公的紀錄片在世界引起紛紛議論的同時,其日本社會上的“公之於眾”,如同掀開了日本看似自強繁榮的遮羞布,就像一個巨大的冰錐扎進了無數對本國發展沾沾自喜的日本人心中。
橫濱瑪麗悽美的故事背後代表無數個和她一樣在那個時代背景下被犧牲拋棄的日本女性,她們是建設殘餘的碎片,日本政府無數次想要讓國民強制抹去的歷史再一次地回到了他們的記憶之中。
紀錄片的最後,瑪麗和唱完歌的元次郎訴說著陳年舊事,離別時,元次郎對瑪麗說:“要活到一百歲啊。”
瑪麗開心地和元次郎拉起了勾勾,兩人在並不光明的養老院走廊,牽著手,慢慢地走著。
拍攝尾聲,鏡頭裡清晰地出現了瑪麗慈祥蒼老的臉龐,瑪麗的嘴角微微上揚看起來心情很不錯。
本以為會有拍攝人員上前採訪她,然而卻並沒有,導演只是靜靜地說著:“看到瑪麗的那一刻,根本再也不想多問什麼了……
紀錄片的播出使得瑪麗受到了無數人的尊敬,但是斯人已逝,只願像橫濱瑪麗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
參考文獻:
紀錄片《橫濱瑪麗》
中外文摘《站街60年》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