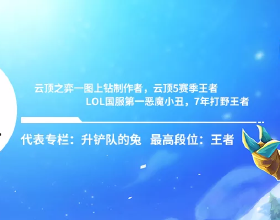故事起源於一包蠶豆。
1915年的北京城還算平靜,袁世凱雖然天天做著那當皇帝的夢,政事倒是照常施行。
至少平常人家準備逃難的包袱一時半會兒還用不上。
好日子誰不想過?但是正值亂世,“亂”也得有“亂”的活法。
大街小巷裡,四處都是小販們的吆喝聲,左邊打仗,右邊遊行,老百姓的生意不好做。
一間賣果脯小食的雜貨店裡,進來了個丫鬟打扮的小姑娘,直言要買黑皮的五香酥蠶豆,價錢不是問題。
只見這姑娘雖然打扮樸素,但一打眼就能看出來是大戶人家出來的,想必定是為哪個小姐姨娘買的解膩零嘴。
慧眼如炬的老闆聽著喜笑顏開,忙不迭抽出一張乾淨的報紙,是時下最權威的《順天時報》,剛剛打印出來不久,還留有淡淡的墨香味。
不過很快,那一絲墨味就被鹹香撲鼻的熟蠶豆味蓋住,一大包新鮮出爐的蠶豆被丫鬟拎在手中,直奔“新華宮”而去。
那是曾經的天潢貴胄、皇親國戚才能住的地方,如今,是袁世凱一家人的“行宮”。
只見這個小姑娘輕車熟路的進了旁人只能遠觀不可褻玩的地界,目標明確的衝著一間裝飾華美的屋子走去。
正等著吃蠶豆的大家閨秀望眼欲穿,見到侍女手裡的包裹,頓時喜笑顏開。
這姑娘不是旁人,正是袁世凱的三女兒——袁靜雪。
自己最喜歡的零嘴就在眼前,袁靜雪忙開啟報紙,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順便瞟兩眼報紙上的最新訊息。
可看著看著,她發現不對了。
此時的袁靜雪年紀還小,正是孩童心性,可這並不意味著她看不懂包裹蠶豆的報紙有問題。
《順天時報》雖是日方注資開辦,但是當時社會混亂,許多紙媒紛紛倒閉,這個外資的報紙也就逐漸成為了民眾接受訊息的最大來源。
掌握了流量就控制了發言權,一百年前的民國也不例外。
《順天時報》的繁盛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民意”。
而作為明面上國家的最高領導者,又處在復辟的關鍵階段,袁世凱自然對此報的“民意”甚為重視。
閒暇之時,這位身居高位的總統大人總會抽出一段時間細細品讀當天的時政新聞、社會觀點。
當他看到報紙上對其如今功績大加讚揚之時,總是頗感欣慰,認為自己做皇帝乃是“順安天命”。
大家長對《順天時報》尚且如此推崇,那袁家人或多或少也對其多點關注也是情有可原。
或許是天意,發現不對的,正是頗受袁世凱寵愛的袁靜雪。
包著蠶豆的報紙同樣是當天的《順天時報》,為何與她今日看的不同?
深思熟慮、兩相對比之下,她得出了一個驚駭的結論:
有一份報紙是假的!
她知道,這份報紙和大哥袁克定脫不了關係。
實際上,家裡孩子與大哥的關係都不好,於是袁靜雪選擇問風流儒雅的二哥——袁克文。
袁克文卻只和她說了一句話:
“我在外邊早已看見和府裡不同的《順天時報》了,只是不敢對父親說明”,袁克文道:“你敢不敢說?”
“我敢!”
後續的事情很難得知細節,女孩年紀還小,不知道這是何等嚴重的大事,告知真相時,父親袁世凱的沉默卻讓她心驚膽戰。
她只知道,第二天起床之時,全家人都在討論大哥被父親用鞭子狠狠抽了一頓的事。
那年的袁克定,37歲。
一張報紙,為何能讓袁世凱對向來看重的兒子痛下狠手?甚至罵其“欺父誤國”呢?
袁克定,字雲臺,別號慧能居士,可他做的事,卻稱不上一個“慧”字。
1912年,喜愛馳騁於馬場的袁克定終日打雁,終被雁啄了眼,摔下馬,直接將腿摔到了不能站立的程度。
加入政場十幾年,袁克定與袁世凱的關係遠非“父子”可輕易定論,武昌起義、南北和談、外交事務,袁克定均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
袁世凱是個相當重視嫡庶親疏的傳統人物,他將袁克定視為接班人,幾十年來親手培養,哪見得兒子落得如此地步。
聽說德國醫療事業發達,他迅速派人將大兒子送到了德國最好的醫院救治。
若是袁老先生預知了日後諸多亂事,皆因此念而起,不知道會不會悔青了腸子。
畢竟是一國元首的親生兒子加得力助手,袁克定一到德國,就受到了極大的優待,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甚至特意為其舉辦了歡迎宴會。
燈紅酒綠,鬢影香風,推杯換盞間,被晃花了眼的,不止袁克定一人。
或許威廉二世要的就是這個效果,與袁克定客氣了許久,他終是帶著些許誘惑的口吻無意道:
“中國不適合共和制,只有君主立憲制,才是大勢所趨。”
“君主立憲”?昏昏沉沉中,袁克定聽到了這四個字。
亂世出英雄,人是中國人,國是中國人的國,除卻真正賣國求榮的漢奸之流外,不同階級、不同政黨、不同陣營的政治家們,都只有一個目的——“救國”。
而袁克定心中或許有這個心思,不過瞬間膨脹起來的虛榮心讓他暫時無暇他顧。
所以,我們不能說袁克定被豬油蒙了心,他只是不會預知而已。
他不能預知一戰、二戰,德國既是發起國,也是戰敗國;
他不能預知其父的皇帝之位只坐了83天;
他同樣不能預知,中國早已不是“君主”可以控制的國家。
袁大公子只看到了德國的兵強馬壯、國富民強。
他看不見專制讓人民苦不堪言,看不見戰爭讓國民流離失所,甚至看不見威廉二世眼中,那被掩蓋在善意之下的貪婪和野心。
世界是個圈,想穩坐霸主之位,東亞國家的加盟必不可少,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而處於亞洲漩渦的中國,必須要以重寶徐徐圖之,拉攏結盟。
當然,這份拉攏和寶物究竟幾分真心,幾分利用,或許只有德國的政客們自己心中清楚。
而袁克定此時以為自己發現了什麼常人難以得到的寶藏,迫不及待地拖著一條病腿回國邀功。
君主立憲制?中國不就有現成的嗎。
袁世凱想做皇帝這個念頭究竟是何時興起的?古今中外諸多學者專家討論了許久也沒個準確答案,可有一條是大家紛紛贊同的。
他想集權。
而眾所周知,皇帝才是中央高度集權制的最大受益者。
民國初立的前兩年,各類民間黨派層出不窮,軍權、政權,被分流進各個軍閥高官手中,袁世凱這個總統看上去風光無限,實際上處處受人掣肘。
袁克定從德國帶來了“君主立憲制”的訊息,讓曾經不會在意的袁世凱第一次認真考慮起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從那一刻起,“復辟”就板上釘釘了。
而若說此舉是袁世凱為了將權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行動,那袁克定的想法就簡單多了。
父親若是能當皇帝,他就是“皇太子”,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曾親眼看見皇權破碎的夕陽之景,自然也瞭解萬民供養一人的盛世華景。
此時的袁克定,或許已經選擇性地忘記了,曾經的他,也是一個堅定的革命鬥士。
相較不受父親喜愛的生母於氏,袁克定在袁家“金貴”多了。
雖說袁世凱是庶子出身,但是並不妨礙他將嫡子看得最重。
袁世凱與於氏的婚姻熱度只維持了短短兩年,或許這門親事唯一的意義,就是生下了對袁家來說十分重要的嫡長子。
袁世凱並不迂腐,但是他相當重視嫡庶,從小到大,他從未想過讓袁克定以外的人繼承他的衣缽。
作為袁家二公子的袁克文比袁克定小11歲,與袁克定不同,雖同樣深受寵愛,但是並沒有作為接班人培養,於是從小千恩萬寵長大的他一直是個浪蕩公子,並不醉心政術。
讓袁克文一直苦惱的是,袁克定一直將其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比如在立太子這件事上,後者甚至曾直言:
“如果大爺(袁世凱)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殺了!”
雖然聽起來是氣話,但是也足以說明袁克定對“皇太子”之位的垂涎欲滴。
自從袁世凱決定復辟之時,袁克定就已經以太子自居,為人極其倨傲,甚至不把父親手下的老臣放在眼中。
1913年新年伊始,段祺瑞與馮國璋按舊禮給袁世凱拜年,袁世凱身居高位,在二位老臣行跪拜大禮時,連連擺手,稱“不敢”。
而作為晚輩的袁克定面對兩位老者的大禮,卻端坐在首,安心受了幾拜。
人情世故是個不明言說的默契,袁克定此舉,稱得上狂妄。
可惜,假《順天時報》暴露之後,袁克定在袁世凱心中的地位急速下降,“欺父誤國”的標籤直到袁世凱悲憤逝世之時,還扣在他信任一生的大兒子頭上。
可這時的袁克定顯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袁世凱因復辟失敗憂憤離世後,家中的長輩只剩下當家主母——於氏坐鎮。
雖說於氏只是個不通文墨的小腳女人,但是長輩不亡家不散,豪奢一時的袁家撐不起袁世凱逝世後的門面,也只能看似安穩的照舊生活。
3年後,於氏去世,袁家正式分家。
作為家中長子兼封建大家長的角色,袁克定分得的家產是大頭。
據傳,除去古董字畫、不動房產、珠寶店面之外,他還拿到了40萬的現金大洋。
而其他庶出兄弟們,只分得了12萬元,還比不上袁克定的半數之資。
根據袁克定的侄子袁家賓所說,袁世凱在世時,曾存於法國銀行200萬法郎,而這些錢,最終都歸到了袁克定手中,家中兄弟還曾因此鬧過一陣。
儘管已沒有了“袁家天下”的供奉華景,但是不得不說,如此厚重的家產和資金,也足以供得起一個富貴之家。
可最終,袁克定為何落到了吃破菜葉子的地步?
北伐戰爭勝利後,時局變了。
國民政府執政時期,是袁克定生活水平的急速下滑期,虎落平陽被犬欺,不再從政的他人人都能來踩一腳。
袁克定本身是傲氣頗重的。
他曾因家中弟妹不聽從自己建議,隨意婚嫁,大庭廣眾之下下人面子。
也曾因不能接受憲兵警察的搜身之舉,一怒之下再未去過天津。
而最為知名的,則是他於華夏存亡之際,堅決不為三鬥米折腰的故事。
1928年前後,國民政府曾對袁克定名下的財產進行了沒收和封禁,這導致其生活水平本就每況愈下。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狼子野心妄圖吞併中華大地,沒正式露出兇狠面孔時,四處招攬收納當時比較有影響力的人物。
袁克定,就是其中一位。
彼時日本在中國的權利相當之大,一系列不公平的條約讓各大港口門戶大開,即便在政治場上,他們滲透的也相當充分。
華北的汪偽政府正在日本人的控制下四處“招兵買馬”,時任華北偽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朱深,“替”袁克定簽訂了一份條約——《擁護東亞新秩序》。
袁克定的缺點不少,乾的錯事也不少,但是骨子裡對於叛國的事情還是有著些原則和分寸的。
聽聞此事,袁克定大為不滿,迅速找尋報社,想做出澄清,可此時北平的報社皆害怕大勢力報復,皆不敢發聲。
重重困難之下,他找遍關係,託遍熟人,終於在一張報紙的小小角落登出一則澄清宣告:
“未經本人同意,署名不予承認。
事實上,在當時的大背景之下,袁克定費盡功夫做出的澄清對其來說可謂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而他毅然的與另一方割席,這成為了袁克定日後十分說得出去的一件得意事,但是並不能緩解其生活的窘況。
19世紀40年代,袁克定的生活早已難以為繼,家中不再請得起傭人家丁,一位老僕人卻依舊忠心耿耿。
最難的時候,已經鬚髮皆白的老人家常常佝僂著身子,去菜市場撿一些別人不要的蔬果青菜,更多的時候是白菜,因為易於儲存。
炒菜、熬湯、做醃菜,袁克定就靠著這位老僕人“化緣”而來的食物聊以度日。
可偏偏這時的他依舊端著那讓外人不明所以的“優雅”,每次進餐必定淨手端坐,戴起餐巾,拿起刀叉,切割著曾經不屑的窩窩頭和鹹菜。
按理說,能在政場上揮斥方瓊的袁大公子絕對不是個蠢人,但是除卻當權政府對其刻意的為難之外,如此困境與他自己所作所為也脫不了關係。
他有極其相信“自己人”的壞毛病。
年輕時被女人欺騙過感情,於是愛上了男色。
他信任自己的下屬僕人,結果被人騙光了房產。
因為不曾懷疑過兒子供養其晚年的決心,他被兒子騙走了全部的股份和資金。
這確實讓人有些哭笑不得。
最終,還是袁克定的表弟——張伯駒,供養了其晚年生活。
或許經歷了太多的恩怨是非,解放之後的袁克定生活逐漸平淡安穩,甚至懂得了感恩回饋。
他會將自己全部的工資收入交給張家媳婦,不參與張伯駒的社交會友,每日除了在文史館中做好本職工作,就是在四方的小院子裡安穩待著。
而他晚年的故事,竟然是由張伯駒的女兒——張傳彩,口述給後人的。
忙忙碌碌了一生,不知道究竟該評他諸事圓滿七彩人生,還是感嘆一句:
曾經種種,竟然皆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