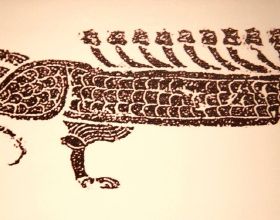“荒田無人耕,一耕有人爭”的這種現象,在現在的農村確實存在。在一臺平臺上,看到一些人討論這個話題的時候,很多的人認為這是一種農民狹隘思想,果真如此嗎?
這裡先舉一個我們村裡的一個事例。
我們村裡李大爺的兩個兒子,年紀都上了五十。兄弟十多歲就在外打工,積下了不少錢,日子過得還不錯,在城裡有車有房,但是,今年初他們回到村裡,種了幾百畝水田。
他們回要的理由有兩個:一是他們的父母都上了八十歲,已經年老體衰,成了醫院的常客,而兩位老人又不肯隨他們到外地的城市去居住,這樣就必須留人在家裡照顧。二是兄弟倆都是初中畢業,在外打工,都在工廠車間上班,雖然都掌握了一門技術,又是廠裡的老員工,工資收入也不低,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體力和精力跟不上了,反應遲鈍,再加上身體健康方面的原因,實在做不下去了。
兄弟倆原本打算回家做點穩靠的小生意,賺一些生活費,多少為孩子減輕一些負擔,也就知足了。他們回到村裡後,發現村後山衝的許多荒田無人耕種,面積有三四百畝,引起了他們再次創業的興趣。
村裡這些水田被拋荒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交通不便,種田要翻山越嶺,靠的是肩挑背扛。二是這些水田,當年責任制分給農戶承包時,就是村裡各個組的二、三、四等田,還有一小部分的水田上不了等級,被視為旱地。
這些水田大致可分成三種類型:一種型別是“天水田”,也就是下雨才有水的田,沒有固定的來水,看天吃飯。碰到風調雨順的年景,產量不錯,但是,如果碰到乾旱之年,產量很低,甚至顆粒無收;另一型別是山溪田,也就是山衝內的田。俗語說“易漲易退山溪水”,山衝小溪或者水溝,雨大時就暴漲起來,把山衝的水田全淹沒,而乾旱時,水田無來水,禾苗就會幹死。這種水田實際上也是看天吃飯,雨水偏多的年分,產量不高,雨水偏少的年分,產量也不高,只有雨水合適的年分,才會豐產;再有一種型別是冷水田,也叫冷浸田,山上的泉水從田裡滲出,夏天也是冰涼冰涼的,這種水田雖然旱澇保收,越是乾旱產量越高,但總的來說,產量不是很高。
兄弟倆畢竟在外打拼了這麼多年,腦瓜子靈活。他們到縣農業部門諮詢,得知政府對種田有多種補貼和獎勵政策,比如,拋荒治理獎勵、再生稻扶持、優質稻種植獎勵、 機械生產獎勵、規模生產獎勵、統防統治獎勵、信貸扶持等,算起來全部累加起來,每畝有五六百元。最關鍵的是,縣裡為了加大治理拋荒力度,對一些交通不便水田成片的山區,加大機耕道修建和水利建設的投資力度。
兄弟倆決定將這些荒田全部耕種。然而,這些水田雖然荒蕪了,但是,每一塊荒田都是分到戶的責任田,都有承包人,也就是農村老話說的:“千里土地各有主”,古代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他們認為,你不去動這些人的責任田,水田裡就是長滿野草,有的甚至已長出了小樹,也沒有人去管,一旦去耕種這些責任田,承包人就會出來“爭”。所謂的“爭”,無非就是“權利”二字。一是爭“權”,即承包權,二是爭“利”,希望獲得一定的利益。因為承包權在人家手裡,這是沒辦法的事,要把這些荒田種起來,必須要透過這些戶主認可,至於要不要租賃費,還未可知。
於是,兄弟對這些責任田的承包權人,在家的人就上門去協商,不在家的就打電話協商。讓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些人家好像都統一了口徑,他們說,你們種吧,不要種任何東西,只要承認田塊的承包權還是我的就行了。有的人還說,你們把我家荒了的田種了,是好事,說不定哪天自己想種了,就不用開荒了,還得感謝你們呀。
為了把事辦得穩妥一些,免得以後發生不必要的糾紛,兄弟倆與責任田的承包人一一簽訂了合同。
這兄弟倆的做法是非常正確的,按照農村的說法,他們的“禮信”到了,也就是既講禮節,也有憑據,免去了責任田承包人的後顧之憂。把已經荒了多年的水田耕種得起來,他們當然很樂意,要不是農業生產的收入太低,誰又願意外出務工,誰又願意自家的責任田荒蕪長草長樹呢?
農村確實出現過“荒田無人耕,一耕有人爭”的這種現象,我們村裡也出現過這樣的情況。究其原因,主要是有人耕種荒田時,事先沒有與責任田的承包人打招呼,也就是說“禮信”沒到堂,沒有尊重別人家裡的“主權”。這種做法自然讓責任田的承包人心裡有想法,發生糾紛,也是很正常的事。上面的政策已經明確,農民承包地再延長三十年。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說明社會發展變化得很快。這是過去的說法,現在社會的發展變化更快了。再過十年,社會發展變化到什麼樣子,農村外出務工的人,還需要不需要這些責任田,誰也說不清楚。
記得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波及全球經濟,我國沿海地區發達城市也受到影響,大批工廠關閉,找工作難,很多外出務工的農民迴流到家鄉,重新耕種責任田。那一年農村好像又復活了。我記得,村裡好多年沒有舞過龍燈,2009年的春節又重新舞起來了,主要是村裡有了人,有人就好辦事。
不過,這次經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很短暫,後來,沿海地區又進入了飛速發展的快車道,農村人口更多地流向經濟發達地區,加速了農村“空心化”,自此,我們村裡就再也沒有舞過龍燈,找不到舞燈的人了。就是有人回村過年,大多是來去匆匆,在村裡停留的時間很短暫,同時這裡也有智慧手機快速發展的功勞,人手一部手機,這種古老的公益傳統文化活動,已經讓年輕人失去了興趣。但是,這次金融危機給農村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讓很多農村人多長了一個心眼。
去年,受新冠病疫情影響,一些上了年紀的在外務工人,迴流到了農村,過起了農村的耕種生活。比如,我們村迴流的男勞動力,每人都種了十畝以上的水田。與過去種田相比,現在種十多畝水田,比過去種三四畝水田要輕鬆多了,耕田、插秧、殺蟲、收割都是機械化。
曾經有一段時間,網路上說,以後農村戶口要比城鎮戶口值錢,可除了城市近郊,土地可以增值外,偏遠的農村,戶口又有多少值得農村人留戀呢?可這種說法,在農民還是有一定影響的。又有一位成功企業家說:“致富未來在農村!”這句話本來沒有毛病,因為企業家是站在他們行業角度來說的,用網路門店與民爭利,是指某種行業資本的擴張,而不是指真正的農業和農村。但是,這句話與一些農村俗語一樣,可以有很多種解釋,讓人產生多種聯想,因此,這種話頗有影響力,影響了一些人。
農民在農村的資本就是土地,自己承包的土地當然要守護好,哪怕荒蕪在村裡,承包的權利也不能放棄,以不變應萬變。
也就因為如此,農村有人耕種荒田來說,就有人出來爭,爭的是荒田的承包權,怕時間長了,失去承包權,失去將來的退路。因此,對荒田來說,一有人爭,就說是農民的農民狹隘意識作怪,這是不準確的,只是一種表面現象。
改革開放幾十年來,現在的農民,由於外出打工、經商掙錢,已經擺脫了土地的束縛,尋找更多的生活門路,因此,面朝黃土背朝天,終生從事種田,不再是農民唯一的經常來源。
隨著外出人員的增多,現在農村人的思想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緊跟時代的步伐。如今在外發展得好的農民,有的城裡買了房子定居下來,融入了城市,成為當地的市民,可仍然在村裡建有新房屋,依然還是村裡的村民,過著雙重身份的生活。經濟稍差的農民,一部分人在家鄉的縣城買房,準備作為將來的養老之地,壓根就沒有要回到村裡的意思,但在村裡依然儲存了祖宅,戶籍依然在村裡;還有一部分人則在村裡蓋起樓房,準備將來年紀大了,無法靠打工維持生活,就回到村裡,種著自家的一畝三分地,以度餘生。
現在的農村,不僅有一部分田荒了沒有人耕種,很多剛剛建好的,花費了數十萬修建的漂亮樓房,大多空閒在鄉村。這實際上也是農村的一種鄉土情結,在這種情結的支配下,迫使他們選擇為自己留“後路”,把根留住,為自己的將來,或者子孫後代多留一條供選擇的道路。
二十年前,這種農村人口的分化現象,在農村就非常普遍了,剛開始的時候,大多數人還與村裡有著千絲萬縷,無法割捨的聯絡。記得那些年曾流行過比較形象詞語,比如,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等,說明那時生活在農村的人,至少還有兒童和老人,那些外出打工的人,還沒有完全脫離農村,農村還有牽掛,隨時都有可能回到農村來。
如今,各種媒體很少使用“留守”來形容農村了,而是用一個與時俱進的形象詞語來形容農村,那就是“空巢村”、“空心村”。村裡的房屋大多沒有人住了,只有房屋,新建的房屋、舊房屋沒有區別,都空閒在那裡,田地自然也就荒蕪在那裡,任野草瘋長。
英國現實主義作家查爾斯·狄更斯的《雙城記》有一句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也是最壞的時代。”社會劇烈變革的時代,必然會引起社會顛覆變革,不僅農村如此,一些中西部地區的城市,也同樣面臨這個問題。
如果有人認為,只有農村才“空心”,那就大錯特錯了。近些年來,一些縣城,三四線城市,也同樣出現了“空心”現象,甚至中西部地區的一些二線城市的個別社群也出現“空心”街道和小區,只是相對農村來說,不是很明顯。
可不可以說,這些城市的房屋沒有人住,一旦別人來入住,就會有人來爭呢?這些有房產權的人出來爭,是不是顯示出他們的狹隘意識呢?
也許有人說,城市房產和農村的田地無法相比,城市房產是個人財產,不容他人侵犯,農村田地不是個人財產,歸集體所有(農村土地為集體所有制),兩者不是一回事。事實上,村裡的房屋和水田,包括自留山、自留地等,都是農家的財產,要動用這些財產,就得徵得戶主的同意。因此,這種所謂的“爭”,並不是無理取鬧,實際上是主張自己的承包權,無可厚非。
過去,田荒了,以前還有田荒兩年田要收回集體之說,但現實當中很少有這麼做的。現在,荒田多了,就更沒有人提這回事了,即便把荒田依法收回來,問題也來了,這些荒田誰來種,能找到種田的人嗎?
總之,“荒田無人耕,一耕有人爭”現象,是三農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並不是簡單地歸咎為“傳統農民意識”和“傳統農民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