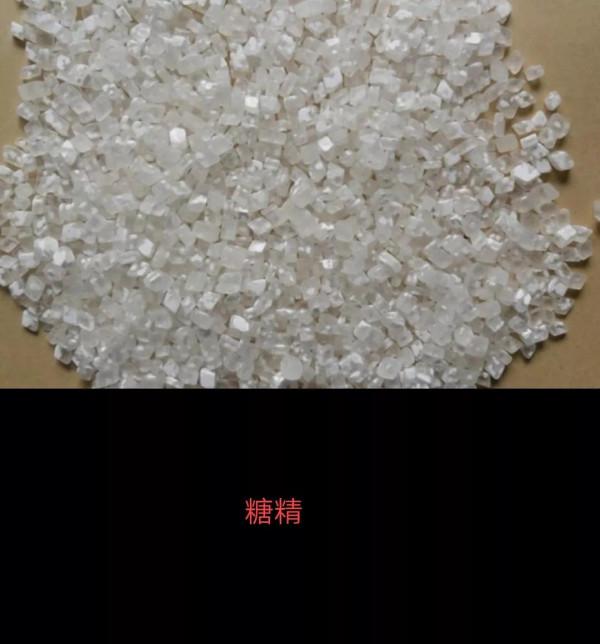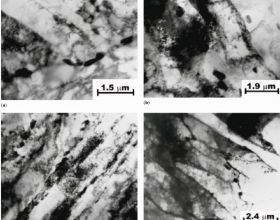上個世紀70年代是個物資緊缺的票證年代。人們的日子普遍過得很是清苦。當時的農村人尤其如此。如何讓苦日子有些愉悅的感覺,那就得先讓嘴巴嚐點甜頭。於是,糖成了農家人共同的渴望。
渴望歸渴望。那時,社會上糖的品種極少,有蜂蜜、冰糖、白糖、紅糖等可憐的幾種。而且,都是憑票供應的。也就是說,光有錢是買不到糖的。更何況農民手中不但少有糖票,而且還更缺錢。據同齡人回憶,當時一個農戶一年給發二斤糖票,家有坐月子的,需要大隊開特供證明。不管怎麼樣,糖又是必須買的。因為,農村人不是把糖當作調味品,而是將它當作了滋補品和藥品。在家鄉,女人來例假、坐月子要用糖;老人腸胃不好、身體虛弱要用糖;就是風寒感冒也得用紅糖薑湯來治。所以,僅能買來少得可憐的糖,只用於特殊人群和特殊情況,健康人一般是不能動的。家鄉人常說,女人月子“三件寶”,紅糖、小米、石子饃。小米加紅糖熬製的四六稀飯泡上石子饃是月婆子的最佳食材,這些有營養、易消化、易吸收、和血化瘀的食品極有利於產婦身體地康復。小時候偶感風寒,人渾身哆嗦。母親就用生薑片、蔥段、紅糖和水熬上一碗辛辣甘甜薑湯讓趁熱喝下,再蓋上被子捂著發發汗,一覺醒來感冒就會好的,很是靈驗。因此,家鄉人對紅糖是有偏愛的。
我家鄉那時的情況是,蜂蜜、冰糖基本上是想也不要想的奢望,因為太珍貴稀缺。得時半閒家裡只能買上二三斤白糖或者紅糖,以備不時之用。當然,大多時候買的是紅糖(家鄉人習慣叫它黑糖)。其實,糖是用全家人都捨不得吃的雞蛋換的。家中那三五隻下蛋的母雞那可是一家人的錢罐罐喲!記得,還買過一種黃顏色的糖,不要糖票的,甜度比黒糖還差些,叫做古巴黃糖,四毛五分錢一斤。小時候,我兄弟三個還隔三差五地偷偷用家中的白糖、黒糖、黃糖夾過饃吃呢!因為,大多數的日子裡只能是生蔥就饃、辣子、鹹菜夾饃,開水泡饃、蒜醋水蘸饃。當時的人生五味,最缺的是甜哪!
沒有糖就得想辦法找替代品。剛好,國家新生產了一種叫做糖精的甜味劑,不要票。從而,糖精就成了一個唯一不錯地選擇。我們家處於關中平原糧食主產區,夏季主產小麥、秋季主產包穀,當然也產可菜可糧的紅苕、南瓜。按理說能經常吃上白麵,可事實上是農民口糧也相當緊張,並且一年的大部分時間的吃食是與黒面、包穀、紅苕為伍的。農家的白麵僅用過年、過事和擀麵條及做沫糊飯用的。大部分的家庭還要為一大家子人填飽肚子想辦法。當時的農村人對糖精這種甜味劑知道得不多,據說是從煤化產品中提煉而來的。它是一種不透明的、小顆粒的白色結晶體,甜度很強。一碗稀飯或者沫糊中放上一倆粒就行了,再多了就成苦得了。農家人渴望的日子是苦盡甜來,但當用上糖精後卻讓人們嚐到了甜與苦的雙重感覺和甜多苦多的別樣滋味。那時候,奶奶給上我一毛錢,就能在大隊代銷點裡買上一小紙包的糖精,拿回家後小心翼翼地裝在一個空的深色小藥瓶裡,當成個寶貝似的,那可是全家人甜蜜的希望所在。
我們全家都喜歡甜食。總嫌南瓜、紅苕等熬的稀飯甜味不足,稀飯出鍋後往往還要再放上幾粒糖精來增甜。當時,口糧緊張,家中常年用黑麵、雜糧和稀飯來哄大人小孩的肚子。如黒面饃、包穀面饃、紅苕面饃、三色花捲(黑麵、包穀面、紅苕面)和幾樣固定的稀飯。除了包穀糝稀飯外,喝紅豆沫糊、南瓜沫糊、紅苕沫糊這三樣稀飯時我家必放糖精。另外,蒸包穀面發糕也要用糖精。
那種甜中微微帶苦的滋味抵擋了腸胃的飢餓和遮蓋了生活的艱辛、也模糊了人們對未來的迷茫,深深地鐫刻在了我的童年時代記憶裡,養成了我終生喜歡甜食的飲食偏好。糖精,也成了一個難以忘懷的時代符號。一個現代人很難想象的甜味品。
改革開放後,隨著糖產品的豐富和人們健康意識的覺醒,糖精也漸漸地淡出了人們的視野。這是一代人的幸福。
2017年國際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將糖精列入致癌物清單中,這又是一代人的不幸!
幸與不幸,糖精作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