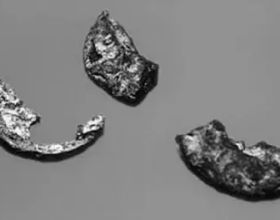氣候變化迫使一些動物遷徙。不要叫他們“入侵者”。
2016年,海洋生態學家派珀·沃林福德(Piper Wallingford)在加州拉古納海灘的岩石海岸進行野外考察時,注意到一個她從未見過的硬幣大小的生物。這是一隻黑色獨角獸蝸牛,它是一種食肉動物,能鑽進貽貝體內,並注入一種酶來液化貽貝的肉。沃林福德解釋說:“它們基本上就像喝湯一樣把它吸出來。”
沃林福德後來瞭解到,這種動物原產於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亞州,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它一直沿著海岸遷徙,尋找新的棲息地,沿途吃掉當地的貽貝。它也是世界上無數物種之一--從白尾鹿到龍蝦,從犰狳到楓樹,都在隨著氣候變化而變化。
生態學家預計,氣候變化會導致這些“範圍轉移”或“氣候跟蹤”物種的棲息地發生大規模變化,這些物種有時被稱為“範圍轉移”或“氣候跟蹤”物種,這將以難以預測的方式重組生態系統。遷徙對於物種在更高溫度下生存的能力至關重要。
沃林福德和其他生態學家告訴我們,科學界基本上認為這種棲息地的改變是一件好事。但公眾和政策制定者的主要視角就不那麼寬容了。“入侵物種”是一個在美國人意識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它已經有了自己的生命,改變了我們判斷生態系統健康狀況的方式,並將地球上的生命巧妙地劃分為原生物種和入侵物種。
例如,2018年《橘郡紀事報》(Orange County Register)關於沃林福德工作的一篇報道稱,黑獨角獸蝸牛是“氣候入侵者”。我認為,任何時候你提出一個新物種的想法,都會有一種固有的反應,“哦,這很糟糕,對嗎?“瓦林福德說。但她鼓勵當地利益相關者不要試圖移除它們。
幾十年來,入侵一直是環境政策的一個典型範例,決定了在有限的保護預算下可以做些什麼。被認為是入侵的物種經常被殘忍地殺死。儘管入侵生物學家很容易指出,許多非本地物種從未成為問題,但入侵的概念幾乎從定義上就使科學家對物種的移動持懷疑態度。但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環境哲學家現在質疑,一個以物種的地理起源來定義的概念,是否能夠捕捉到在一個快速變化的星球上生命的倫理和生態複雜性。在21世紀,不存在所謂的不受破壞的生態系統,隨著氣候變化和棲息地喪失的加速,這種情況只會變得更加真實。我們必須把這件事做好。
馬卡萊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生物學教授、入侵框架的批評者馬克·戴維斯(Mark Davis)說,範圍變化“是核心入侵生物學家要處理的一個真正的問題”。
在最近發表在《自然氣候變化》(Nature Climate Change)雜誌上的一篇有爭議的論文中,沃林福德和其合著者認為,觀察一個物種對當地食物或水源的影響,或者弄清它是否遇到了不習慣捕食者的獵物,需要了解距離轉換的影響。
沃林福德說,這個提議遭到了“很多人反對”,他並不一定反對“入侵”的觀點。批評者說,僅僅把氣候追蹤物種與入侵物種聯絡起來就會汙染它們。康涅狄格大學的生態學家馬克·厄本在同一期雜誌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範圍遷移者不應該被視為入侵物種,而應該被視為氣候變化的難民,需要我們的幫助。
氣候變化及其造成的範圍變化是非常特殊的情況。如果一個物種逃離一個正在燃燒或融化的棲息地,這是否可以稱之為入侵?即使在氣候背景之外,這種緊張反映了入侵物種正規化中的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如果這個標籤讓人感到恥辱,那麼唯一合適的回應就是滅絕,也許需要用其他東西來代替它。
“入侵”是物種的起源
“入侵物種”可能感覺像是一個牢固確立的科學範疇,但研究非本地物種影響的入侵生物學是一個相對年輕的領域。
英國生態學家查爾斯•埃爾頓(Charles Elton)在1958年出版的《動植物入侵生態學》(The Ecology of Invasion by Animals and Plants)一書中指出,地球上每一個物種都有一個地方或生態位,它們在進化過程中得以生存。他認為,那些搬家的人應該被移走。
田納西大學的生態學家、入侵生物學的創始人之一丹尼爾·辛伯洛夫說,甚至在那之前,“就有人認識到了入侵,並對其進行了詳細的評論”,其中就包括查爾斯·達爾文。辛伯洛夫說,直到20世紀80年代,它才凝聚成一個科學家的分支領域,相互交談,並將入侵視為一種普遍現象。生物學家並不反對所有非本地物種的存在。它們中的許多是無害的,一些甚至是有益的。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經驗法則是,大約10%被引入新的生態系統的物種會生存下來,而其中大約10%(也就是所有非本地物種的1%)將導致它們成為“入侵性”的問題。其中一些會造成真正的傷害,比如威脅到脆弱的當地物種。例如,澳大利亞的野貓被認為是小型哺乳動物滅絕的主要原因。
入侵生物學隨著其影響力的增長而與政治糾纏在一起。1999年,當時的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建立了國家入侵物種委員會。它將入侵物種定義為“其引入已經或可能造成經濟或環境危害或對人類健康造成危害”的非本地物種。辛貝洛夫是起草這一命令的顧問。他說,白宮在這一定義中加入了“經濟”成分,這往往會損害農業綜合企業的利益。他說:“有一些外來物種對一些農作物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對其他任何東西都沒有太大影響。”很多科學家都不會擔心它們。
將商業和環境問題結合在“侵入性”類別中,聽起來似乎對企業底線的威脅等同於生態問題。考慮到一些被聯邦和州的管理專案保護不受入侵物種侵害的行業,例如工業單作或養牛業。本身就對生物多樣性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這一點尤其麻煩。關於入侵物種的爭論雙方的科學家都認為這種混淆是有問題的。
例如,普通的歐椋鳥,一種原產於歐洲以及亞洲和非洲部分地區的鳥類,作為一種引入物種在北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康奈爾大學生態學和環境生物學博士研究生娜塔莉·霍夫邁斯特說,它們經常在養牛場吃穀物,每年在美國造成數億美元的農業損失。“這對歐椋鳥來說就像是一件珍寶,”她說。美國農業部野生動物服務部門在2020財年毒死了79萬隻鳥類。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椋鳥會傷害本土鳥類,這聽起來似乎是殺死它們的更科學的理由,霍夫邁斯特說,文獻還沒有確定這是否正確。
入侵模式帶有本土主義的偏見
一些關於入侵物種危害的概念是值得懷疑的。
例如,入侵物種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威脅,不僅因為它們殺死或戰勝了本地物種,還因為它們與它們交配。環境作家艾瑪·馬里斯(Emma Marris)在她的《野性的靈魂:非人類世界的自由與繁榮》(Wild Souls: Freedom and prosperity in the Non-Human World)一書中指出,為了保護物種的“基因完整性”,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常常不遺餘力地阻止動物雜交。想想北卡羅來納州為防止土狼與瀕危的紅狼交配所做的努力吧,這種做法令人不安,與最近才過時的西方對種族純潔性的關注有著相似之處。
這就是為什麼一些科學家對入侵生物學的影響持懷疑態度,並認為該領域在記錄外來物種的負面影響和保護自然方面有著根深蒂固的本土主義偏見。生物學家馬修·周(Matthew Chew)和斯科特·卡羅爾(Scott Carroll)十年前在一篇廣為閱讀的評論文章中寫道,入侵生物學就像研究疾病傳播的流行病學,因為它是“一門明確致力於摧毀所研究物件的學科”。
從歷史上看,這一術語錯誤擴大的想法。如果你原來不在這裡,那麼你就被定義為入侵者。
更重要的是,“入侵”的概念借用了戰爭的隱喻,媒體對本地物種的描述與那些描述敵軍或移民的描述非常相似。例如,《衛報》最近一篇關於犰狳“圍攻”北卡羅來納州的新聞報道將它們描述為“害蟲”和“怪異”。它還對這種動物“蓬勃發展的繁殖速度”感到驚訝,這種指責針對的是人類移民,這並非巧合。
許多學者探索了人類和非人類跨越國界,或去他們“不屬於”的地方的焦慮如何對映到彼此身上。“對移民的恐懼從來都不是人類獨有的,”科學研究學者巴努·薩勃拉曼尼亞姆在《入侵生態的倫理與修辭》中寫道。“它包括以有害細菌、昆蟲、植物和動物形式出現的非人類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