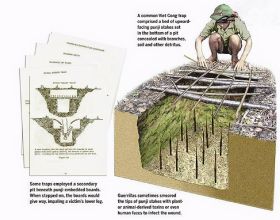朱自清何許人也?無關他的社會身份,我們最真實的經歷是揹著他的散文長大,《背影》、《匆匆》、《荷塘月色》、《春》,對於學生而言,只知道是經典的傳世好文,從未動過念頭,要質疑年少時朗朗入口的美文。
我們做過太多諸如背誦作者的身份,分析中心思想,分段總結……諸如此類的習題,但多年以後留下記憶的,還是當年為應付老師檢查而抱頭背誦的課文,且隨著年深日久的沉澱,那些遺留在腦際的文字與意象,越嚼越香,越深越美。
名家對《荷塘月色》的評價
但對於《荷塘月色》這一篇優美散文,卻有兩個名家提出了評價。
余光中曾經有一篇非常詳細地分析《荷塘月色》的文章,但令人好奇的是,他在文章中給出了極低的評價。余光中認為,雖然朱自清的觀察較為仔細,但他的想象力不足,因此文章顯小家子氣,毫無“蘇海韓潮”之勢!
余光中的評價可謂是極低,但他仍有充分的論據:一,節奏慢,情緒穩,境界不打動人;二,語言平起平落,沒有柳暗花明的寫作手法;三,有些句式太繁瑣;四,比喻過分明顯。最終他以“中學生水平”定義《荷塘月色》。
另有一位名家莫言,也對其做出了評價。但莫言的評價相較於余光中的直接,比較委婉,他認為《荷塘月色》是一種“病態的唯美”。
那從這一篇《荷塘月色》中,我們又能有怎樣的感悟呢?如何來定義、評價一篇文章呢?
特殊時代·四一二反革命的政變
我們要還原一篇文章的真實意境,就應該著眼於它所處的時代背景,對於特殊歷史時期流傳下來的精品,如果脫離其背景而單純去評判一篇文章,不是對作者有失偏頗,而是對歷史不敬,起碼,悲天憫人是每一位文人該有的覺悟。
荷塘月色開篇就是“這幾天心裡頗不平靜”。為什麼頗不平靜?
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工農運動乃至國民黨左派展開了大肆迫害,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極為殘酷的殺戮事件。在此歷史背景下,“頗不平靜”並不是作者“為賦新詞”般的呻吟。
我們深讀這句話:“白天裡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以不理。”這不是為了生計奔忙,人際關係是否協調、事業能否做得好而吐槽的個人情緒,實則是一種無聲的抗拒,或可意會為逃避。
曾參加過五四運動的朱自清曾鬥志昂揚,他的詩歌被公認為清新明快,風格並非留連於個人情緒的小我之作。
隨著五四落潮,昔人已奔東西。知識分子們空負一腔文人風骨,既對現實的國民政府不滿,又對新興的共產黨信心不足,沒有深刻的政治信仰,面對風雨飄搖的國家,前路不知歸處。
譬如曙光乍現而瞬間又被黑雲吞噬,作者的小情緒並非只為一己之憂喜。
這篇荷塘月色,其實是假以自然展現的短時美景,暫做自我消解的“桃花源”之想的。正如作者所說:“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雖是個人的情緒,卻是時代的底色
魯迅先生有一個梗叫棗樹梗,棗樹梗後面通常加一備註,曰:魯迅真的說過。棗樹梗是這樣的:“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讓我們瞭解一下這兩株棗樹的時代背景。
1924年,在《彷徨》中,魯迅曾寫道:“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新青年》散去,面對革命浪潮的湧起,魯迅既不滿軍閥的統治,又不想盲目激進。
關於棗樹的描寫,一株又一株是暗喻,實則是說自己無從選擇,無所適從的狀態,故而彷徨。這深沉複雜的思緒,若不瞭解作者當時的處境,又如何解得那空負報國之志,卻投路無門的思緒?
餘秋雨稱《荷塘月色》是個人小情緒的哀憐感傷,只是中學生水平。其實,細細讀來,荷塘月色的精雕細琢像極了白話版的宋詞,但描得過於精細,又少了宋詞的空靈。
作者欲將語言變成畫,卻被什麼抑制住,欲借景抒懷卻又沒有舒展開來。這正是作者的真實心境。他要暫忘其政治時局帶給自己的苦悶,但怎麼也拂不去它的影像。
而在這句:“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裡的蛙聲;但熱鬧是它們的,我什麼也沒有。”這裡的它們又何嘗不是指當時的政黨?只是不能明說罷了。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不能單純地以文風和寫作手法判定其作品的質量。反襯當時社會的狀況以及人物身心世界的真實反應,這也是文學作品的表現形式。
是一種真實的個人感受
也有人說荷塘月色中首尾兩處出現妻子,反射了朱自清的家庭矛盾。這一點可以體現在他在寫景時總喜歡以女子的意象來作比。
朱自清的第一任妻子是大字不識的傳統女人,當然也屬包辦婚姻,與他育有六個孩子,善良的朱自清一直沒有離棄他的妻子,直到其去世。
他雖渴望一個靈魂上的愛人,但是他把所有對於愛人的美好想象都寄託在了借物抒情上。這就是他的作品中總會以女子的美來比喻事物的原因吧?
我們在朱自清的作品中,看到的是清幽的美與淡淡的憂傷,欲舒而不得志。家庭事物的繁雜與矛盾絲毫沒有體現在作品中,沒有厚重生活的痕跡。
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朱自清能傾心遊弋於文學的世界,而負擔繁重生活的重任其實是落於妻子肩膀上的。
對於精神無比豐富的一代文豪而言,守在身邊的不是靈魂上的伴侶,而是一個搭夥過日子的人。沒有情趣,更談不上共同語言。他只是出於一份道德的堅守而不忍棄之。這也是其文風明媚不起來的一個原因吧。
而莫言評其“病態的唯美”也只是一語帶過,並沒有多作深究,我們也不必過度審視。
對於藝術之美,我們應突破名人和大師的視角,從歷史和人文環境出發,有自己的審美角度,甚至超越審美,站在時代之上去撫摸那一個個不安的靈魂。
歷史更迭下的文學世界
有人說,朱自清的歷史成就大於其在藝術上的造詣。其一,他有清華教授的光環,其二,在美國假意援助中國之時,重病中的朱自清寧可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糧。承揚了知識分子的風骨與氣節,但其文章的質量卻不及他的社會成就。
須知,百年前的文化背景是:古文漸去,尚有餘溫。白話新興,藕帶夾生,外有西式文化魚貫而入。
其時,中國的白話文寫作屬於一個襁褓中的嬰兒,如果說我們現在的水平已經是成人的階層,又怎麼能夠以現在的水準去指責前人的稚嫩,這不是自己在嫌自己小時候不夠成熟麼?是不是有點悖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