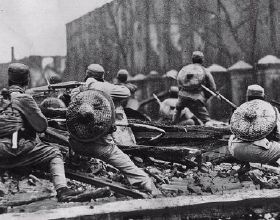越來越喜歡下雨天了,尤其是深夜時的雨。
躺在深濃的黑暗裡,聽雨聲綿綿,淅淅瀝瀝。
空氣中有溼潤的涼氣在飄,整間屋子連同自己,都好似與世隔絕,有股天荒地老的味道。
思緒載浮載沉,過往的記憶蜂擁上場,熟悉的面孔一一浮現,他們笑著、哭著、鬧著、愛著、恨著、怨著、歡喜著,眉眼間都是生動。
在夜雨中,人總愛沉溺在往事中,無可自拔。
那是元和六年(西元811年)的一個夜晚,窗外雨聲蕭蕭,白居易想念著年少時的戀人湘靈,久久無法入眠。
遂有了這一首悽美的詩作《夜雨》:
我有所念人,隔在遠遠鄉。
我有所感事,結在深深腸。
鄉遠去不得,無日不瞻望。
腸深解不得,無夕不思量。
況此殘燈夜,獨宿在空堂。
秋天殊未曉,風雨正蒼蒼。
不學頭陀法,前心安可忘。
他說呀:
我有著深深思念的人,卻相隔在遠遠的異鄉。我有著感懷的事情,深深地刻在心上。
秋天尚未來臨,屋外卻已風雨紛紛。
不曾學過苦行僧的佛法,教我如何忘記那些刻骨銘心的過往。
白居易思念的人,叫湘靈,是他的初戀。
大約在白居易11歲的時候,為了躲避家鄉戰亂,他隨著母親搬家到了徐州符離(今安徽省宿縣境內)——他的父親白季庚做官的地方。
在那裡,他認識了一個鄰家女孩。
那女孩七八歲的樣子,長得很是活潑可愛,兩人很快就成了玩伴,這便是湘靈。
世間有一種很美好的感情,叫作“青梅竹馬,兩小無猜”。
白居易和湘靈便是如此。
他看著她,一日日由垂髫的孩童,變作亭亭的少女,像婉轉枝頭的花兒,含苞待放。
她則抬頭仰望著他,一日日長成溫潤的少年郎,肩膀開始挑起八方風雨。
日日相伴,常看常新。
白居易19歲,湘靈15歲,兩人開始了青澀甜美的初戀。
少年人的愛情,不帶慾望,乾淨純粹。
她為他展露自己輕靈的歌喉,懷揣著“女為悅己者容”的羞澀心事。
他則為她寫下一首首詩詞,歌詠她的美,帶著不加掩飾、渾然無懼的赤誠。
娉婷十五勝天仙,白日嫦娥旱地蓮。
何處閒教鸚鵡語,碧紗窗下繡床前。
——《鄰女》
那時的時光,該是多麼地美好。
可是命運總要生出波瀾,它慣愛翻雲覆雨,然後看戲般,觀芸芸眾生為著一聚一散、一離一合,心神搖盪,悲喜交集。
貞元十四年(708),白居易27歲,為了生計與前程,他不得不離開符離。
“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柳永的一首《雨霖鈴》,不知寫盡多少痴男怨女離別時的眷眷與依依。
路途之上,白居易寫下了3首詩,俱是懷念湘靈。
登臨高處時他寫:“淚眼凌寒凍不流,每經高處即回頭。遙知別後西樓上,應憑欄干獨自愁。(《寄湘靈》)”
每當行到了高處,我就會回頭望著你在的方向。我想象著,此時的你會不會也在西樓之上,憑欄眺望遠方,思念著我呢?
寒夜淒冷時他寫:“籠香銷盡火,巾淚滴成冰。為惜影相伴,通宵不滅燈。(《寒閨夜》)”
夜深霜重,湘靈你呀會不會也伴著那耿耿的燈火,一夜無眠。
“人言人有願,願至天必成。願作遠方獸,步步比肩行。願作深山木,枝枝連理生。(《長相思》)”
《長相思》裡,是白居易以湘靈的口吻來訴說思念。
長相思兮長相憶,短相思兮無窮極。
眼看著一日日時光流轉,秋天走了,春天來了,我們已不見多久了呢?
不是說,人有善願,天必成之嗎?
那麼就讓我虔誠地許願,我願與心愛的人攜手到老,哪怕是做山林間的野獸,我也願與他並肩而行;哪怕是做山林間的草木,我也願與他枝枝相依。
一字字,一句句,深情地令人動容不已。
可是呀,這樣的深情,打動得了旁人,卻打動不了白居易的母親。
貞元十六年初,白居易考上了進士。
他回到符離,懇求母親讓自己迎娶湘靈。
可是母親只是不允。
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已成為校書郎,準備將家眷遷往長安。
他再一次向母親請求與湘靈的婚事,卻仍是被拒絕。
在她心中,自己的兒子應當娶一個門當戶對的女子,而不是隨便一個普通人家的女孩。
這其實也是天下間許多父母的映照吧。
他們一心一意地為子女籌謀算計,盼著自己的兒女少走一些自己走過的彎路,少受一些自己從前受過的苦。
他們總想要把自己認為最好的給子女,卻常常忽略了,子女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雙方都沒有錯,但往往許多悲劇,就這樣發生了。
白居易錯過了湘靈,這一錯過,就是一生一世。
37歲時,白居易在旁人的介紹下,與同僚楊汝士的妹妹成了婚。
他知道自己應當往前走,應當去迎接新的生活,但曾經刻骨銘心過的人,又哪裡能輕易忘記。
人都是如此,得不到的永遠在騷動,越絕望的愛情在心裡紮根越久。
它像是一束小小的火苗,白日裡靜默無聲,到了夜晚,便開始熊熊燃燒起來,燒得人四肢百骸都在痛。
從此以後,白居易的許多詩文裡,都有了那個名叫湘靈女子的身影。
是《長恨歌》,“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是《生離別》,“生離別,生離別,憂從中來無斷絕”。
是《冬至夜懷湘靈》,“何堪最長夜,俱作獨眠人”。
後來很久很久以後,據說白居易被貶到了江州,楊夫人隨行,路途之上,他遇見了正在漂泊的湘靈父女,久別重逢的兩人抱頭痛哭。
那時候白居易已經44歲了,湘靈也40歲了,可她還沒有結婚。
她是還在守著年少時的諾言嗎?還在等待著那個言笑晏晏的少年郎來娶她嗎?
可她永遠也等不到了!
看著昔日的戀人,白居易又該是怎樣的悔恨與痛苦呀。
那兩首《逢舊》,就像一個無可奈何的句讀,終於要給這段長達二十餘載的戀情,做一個收梢了。
我梳白髮添新恨,君掃青蛾減舊容。
應被傍人怪惆悵,少年離別老相逢。
久別偶相逢,俱疑是夢中。
即今歡樂事,放盞又成空。
許多故事原是這樣不堪看的,只一看,便免不得生出“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王國維《浣溪沙》)”的悲嘆。
只因,人生中何處沒有這樣的錯過,這樣的無可奈何呢?
愛別離,怨長久,求不得,放不下,生,老,病,死,樁樁件件,哪一樣不是盈滿了熱淚,哪一樣不是寫滿了故事。
人生有時候原是不能看得太執著、想得太認真、活得太明白的。
看得太執著,心會累。
想得太認真,腦會累。
活得太明白,人會累。
生如逆旅,死即小別,不過是早走與晚走的分別。
我們看淡一些,看輕一些,看通透一些,生活也便簡單一些,快樂一些、自在一些。
【版權宣告】本文作者魏無忌,新媒體人,文化公司創始人,暢銷書作者,主業創業,業餘寫文、出書、玩收藏,交流詩書與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