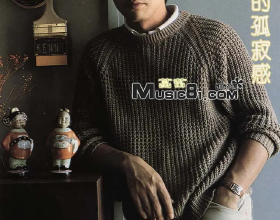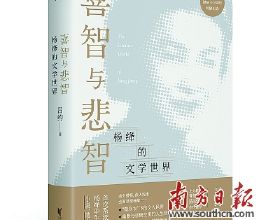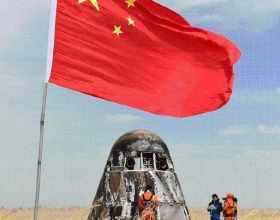一聲一聲雞鳴,似驟發的潮信,縱然稱不上轟轟烈烈,也足以教人遽爾驚悸,哪裡還能在床榻上苦捱得起。冬至後第一日,風雨漸漸歇息。“一個人不論在祈禱什麼,他總是祈禱著一個奇蹟的降臨。任何禱辭都不外是這樣的意思:‘偉大的上帝呵,請使二乘二不等於四吧。’”一個時刻清醒的人是可怕的,屠格涅夫言猶在耳。
光陰荏苒,歸來不再是青蔥少年。哪怕此後不久,春天終會販來桃花。哪怕到山裡面壁,漫坡的迎春花枝屢欲接納。哪怕烏鵲南飛。哪怕生與死。因此,奇蹟是不存在的,奇蹟只是火紅火紅逗一逗小囡囡的冰糖葫蘆,看上去無限美好,輕輕一咬,酸得倒足了胃口。沒有什麼輕裘肥馬可憶,十年文字,偶爾翻檢,皆是困頓困頓困頓困頓,困頓。但已經蠻好,聶老(紺駑)有詩,“廢書焚去烹牛肉,秋水汲來灌馬蹄”,好一個死鴨子嘴硬!明明曉得只不過是讀書人的通病,對鏡撫額,那麼多動魄驚心,你不依舊還在這裡。
昨夜臨帖到凌晨一點,收了筆墨,悄悄在木地板上逡巡。窗外淅淅瀝瀝,參不透的黑黑四面合圍,於是到木椅上再呆坐一會兒。太多的放不下舍不了依次雜沓襲至,菩提都懶得再拈,隔壁鄰人的鼾聲動地而來,滿桌的書卷如暗暗滋長的塊壘。想起老父又掛上了點滴,此前跟母親電話,一陣子勸慰。其實心裡想跟他們說呵,養兒養兒,養他幹甚?人生暮年,本應期待他承歡膝下,這回倒好,“出走”忽而七載,兩千裡相看惆悵,唯有塵寰的跌跌撞撞,每每如鯁在喉,如芒在背。公寓裡顧自清冷,無奈倒頭便睡。
夢裡城頭變幻,醒來所剩依稀。王勃在《滕王閣序》裡曾怔怔慨言,“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記得幾天前在微信裡回覆一位老師的數語中恰恰有與“興盡悲來”神髓苟同的四字——喜而復悲。一年將盡,那日看到《詩刊》最新一期的目錄,一首小詞被中詩網推薦到了子曰增刊,若是講心如古井一定是掩耳盜鈴,日日紙上躬耕,哪個詩人不為了與《詩刊》一晤?然而一次次希冀萌生,一次次泡沫破滅,到頭來望洋興嘆,欲仙欲死。此次上刊,驀然回首來路,竟已躑躅三十年。當然,無怨亦無悔。
神傷的在於不過是可憐人。從來不屑於經營人脈混跡圈子,十年前因為工作開始投稿,不同於更早時候的部落格生涯,整日裡畏手畏腳,痴痴念念,後來看著一篇篇變成鉛字,間或中個小獎,從興奮雀躍,到心如灰死,然後飲馬江淮,然後不投一字。春秋六度,終於一位相知的老兄實在看不下去,伊幾次三番鼓勵,說有什麼呢,不願意與圈中人打交道,大可將稿子往郵箱裡一扔,最不濟,中詩網要發一發吧。於是再作馮婦,重新與“虎”謀皮,到上邊的小詞登上《詩刊》,看看中詩網裡的記錄,共十八個月,計稿四百餘篇。無須講什麼悲涼不悲涼,沒有人看你在風霜雨雪裡的唱唸坐打,只看你在臺上即便是一秒鐘的假鳳虛凰。更不必吐槽人家刊物每期所發文字的水準若何,上不去就是上不去,說葡萄酸有個卵用。管自己!
“當你年輕時,以為什麼都有答案,可是老了的時候,你可能又覺得其實人生並沒有所謂的答案。”(出自電影《墮落天使》)答案是有的,不過是翻開來看的人,早便麻木不仁。在楞頭青的年紀,一位兄弟是小城報刊的主編,巴掌大的小地方,詩呵詞呵的,寫來寫去,讓人看成是神經病,只有兄弟時時採一些去,發個某個專欄上,而後周圍的噓聲漸次稀落,當然至多如此,不要期望有什麼“同志”,可以坐而論道。那時候還掙扎在“廢園”,並不曉得將要焚詩十年,一朝逃遁。春天來了寫桃花,夏末就寫一寫園中的豆角,深秋呢,為大棗樹下的青石們描個影,至於入了冬,便只有漫天的大雪來可商榷。
廢園的末路幾乎是冥冥註定,寫著寫著,便學會了湖海漂泊。到津城的天塔下數鵝呵,到鑄造廠的巨大煙囪上瞰一瞰鐵汁,到黃河的小舟上擬一隻寒蟬,到機關案牘的廢紙堆裡坐井觀天。你才發現一個很尷尬的現實在於,寫字寫字,既寫不來一家飽暖,又寂寂成了癮,推不開,戒不掉,除了順其自然,苦無它途。直至這江淮的日日月月,才明悟,至少它們讓你心安罷。就像一朵明眸善睞的白蓮,你忙了便去忙,閒下來不妨共剪西窗,磨一磨胸中的崚嶒。
還是要走下去,逝者可追,抬頭山河萬里,之前的已成了埃塵。詩刊社駐中詩網的財務姚女士來結付稿費(捂臉),諮詢了推薦老師李江湖的微信,一再表達了誠摯的謝意。再然後呢,再然後陰雨不絕,一日甚於一日。
而今雞鳴四起,公寓裡清冷如故,江淮的年末也確實沒有什麼不同,意氣風發的意氣風發,壯懷激烈的壯懷激烈。眼前一下子閃過《笑傲江湖》中的某一幕:“午馬”與“林正英”在船頭引吭高歌,真真一時瑜亮,天下無雙——
滄海笑 滔滔兩岸潮
浮沉隨浪 記今朝
蒼天笑 紛紛世上潮
誰負誰勝出天知曉
江山笑 煙雨遙
濤浪淘盡 紅塵俗世知多少
清風笑 竟惹寂寥
豪情還剩了 一襟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