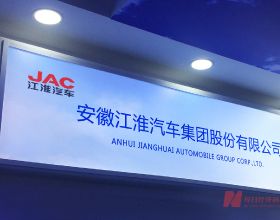本文原標題:《孔子“欲仁”、孟子“欲善”與荀子“欲情”——從當今西方倫理學“慾望論”觀儒家“欲”論分殊》,來源:《孔學堂》(中英雙語)2021年第3期。
摘要:按照西方慾望所分,孔子論欲有主觀慾望內涵,但是“從心所欲”卻走向了客觀慾望意蘊,細究起來,其欲論形成了“欲仁得仁”之混整結構,孔子沒有那麼明確的善惡抉擇意味。重“盡心”“知性”的孟子,其論欲更傾向於客觀的意蘊,因為良知良能訴諸“欲善”的道德意志。重“禮化”“化性”的荀子,其論欲基本上就是主觀的內涵,人類共通之慾與惡相通,但透過外在禮的教化和認知心的向善功能而加以濡化。大致說來,孟子所論之慾乃是激發性慾望,因為這種客觀慾望的確要為道德行動向善提供理由。荀子所論之慾乃是非激發性慾望,此類主觀慾望導致了道德行動向惡而發,所以才是跟從理由的。孔子介於二者之間,或者說,孔子之慾,雖未超出無善無惡,但並沒有明確善惡指向,這一多元可能性引發出孟、荀善與惡欲論的兩種趨向:孟子是心善—性善—情善的“自上而下模式”,荀子則是情惡—性惡—心善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中國原典儒學的欲論,揭示出本土“情理結構”的智慧正規化,它既超出了主客欲的二分法,又讓情感主義與理性主義這對矛盾得以化解,從而為人類慾望此類根基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種返本開新的綜合思路。
關鍵詞:慾望 欲仁而得仁 可欲之謂善 人情之所同欲
作者劉悅笛,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大綱
一、動機之分類:從“意動動機”到“動行動機”
二、“慾望”之型別:從動機、理由與主客方面來看
三、孔子之“欲仁而得仁”的欲論
四、孟子之“可欲之謂善”的欲論
五、荀子之“人情之所同欲”的欲論
六、結語:人類之慾所本有的“情理結構”
在中國原典儒學那裡,孔、孟、荀都談到了“欲”,但是這個“欲”卻各有其意,尤須慎思,本文就聚焦於此,卻是從比較哲學的角度觀之。中文意義上的“欲”的意蘊,乃是豐富而含混的,起碼既有“意欲”(為之)之意,也有“慾望”(得之)之義,但欲一定是有所指向的,並指向了特定的物件。關於所欲之“意”,筆者也曾撰文指出,康德曾區分出“意力”(Willkür)與“意志”(Wille),前者無所謂善惡,後者則只能向善,孔子說“欲仁而得仁”之慾更接近“意力”,孟子論“可欲之謂善”之慾更近於“意志”。[1]但這只是初步區分,還要從慾望論的角度進一步深思之。
在當今西方倫理學當中,“慾望”(desire)問題得到了深入的嶄新探討,不同的哲學家試圖給出自己的闡釋與理解。一般的理論定式就是:我們對X有慾望,我們相信透過做Y可以得到X,所以我們就去做Y。但是,這種分析哲學式的追問方法,卻仍然囿於理性解析的理路,往往把問題引向了慾望之外。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對於“欲”的各種傳統成見,也逐步受到了質疑乃至顛覆,比較關鍵的翻轉在於追問:慾望一定是非理性的嗎?有沒有潛在理性的慾望呢?這是就慾望本身的定性而言的,當今思想的主流是在為慾望的內在理性支撐做出辯護。另有一些成見就與道德直接相關:既然慾望也包孕理性,那麼,所有的道德行為皆是由並且只能由慾望發動的嗎?這就關乎慾望與動機的關係了。這的確是個不錯的切入點,我們就先從動機開始探討慾望的型別劃分。
一、動機之分類:從“意動動機”到“動行動機”
中文的“動機”,在英文當中起碼有兩個詞相對應:“motivations”與“motives”。那麼,二者究竟該如何區分呢?分析哲學家們善於在語言含義的細微差別裡找到根本性的不同:一般而言,作為複數的motives乃是指一切能夠激發出行動的動力要素,而常作為單數的motivation主要指激發行為的“心理狀態”的那部分。[2]照此而論,二者只具有“量”的差異,似乎前者能包括後者,後者只是前者的心理構成而已,但這種區分實際上相當於並未做區分,而且無論是哪種動機都可以複數出之。
到了20世紀中葉,這種定論在更新的研究當中得以改變,motivations與motives被給予了最明確的“質”的劃分。德裔美籍哲學家耶西·普林茨(Jesse Prinz)在對情感的“知覺理論”研究時就是如此為之的。他認定,motivations是使我們得以做出行動的意向或性情(dispositions),dispositions這個詞,既有意向意圖也有情性氣質的意思,的確有心理化的意味;而motives則是行為的驅動,就是所謂的“行為的命令”(action-commands)。這是由於,與motivations更傾向於感性相比,motives更理性化地給予我們以行為的理由(reason)。[3]在此確有感性與理性西方式的割裂。
所以,我們姑且將兩種“動機”做出如此大致區分:motivations乃是驅使行為的意向,motives則為驅動行為的動機,不妨將前者叫作“意動動機”,後者稱為“動行動機”——當然這是筆者的獨特譯法,用以說明二者的虛動與實動之別。因為內在性的意動畢竟不是外在化的行動,而無意識的動行未必就需有意識的意動為先導。這種劃分似乎成為當今的某種新的共識,儘管一般的論者卻並未在動機內部進行區分,從而仍落於動機與行為二分法的窠臼之內。
這就關係到較慾望更寬泛的情感,那麼,情感與動機到底是什麼關聯呢?普林茨就此認為:“情感就是動行的動機(motives)。某個人甚至能把情感描述為動機化,因為它們驅使我們去選擇行為的序列。換句話說,情感導致了意動的動機(motivations)。但是我們卻沒有被意動的動機得以確立身份。”[4]按照這種作為知覺理論的情感哲學,普林茨背後的潛臺詞就是,情感驅動了行為,但此情此感卻只與“意動動機”相系。儘管普林茨的整體理論架構並未被廣泛接受,但是這種情感動機論卻被廣為接受了,但當有論者反過來認定——“情感作為動行的動機而驅動了行為”[5]——的時候,實際上就將“動行動機”與情感勾連起來,這便與普林茨殊途同歸了,儘管他們皆認定情感為行動的內驅力,但是動機的型別卻決定了他們走的是不同的情感之路。
筆者認為,“意動動機”(motivations)與“動行動機”(motives)之分,乃非常重要的動機論上的分殊,特別是當這種動機區分與慾望之型別相匹配之時,這種劃分的價值就更被凸顯出來。當然,還有心理學家傑拉德·克洛(Gerald Clore)認為,儘管情感驅動了行為,但是,情感並不包括“行動的趨向”,因此可以退而求其次,他區分出“動機化”(motivational)與“行動化”(behavioral)的兩種效果:“情感的直接效果乃是動機化的而非行動化的……因而,情感的即刻效果可能較之行為乃是更心靈化的。”[6]
這對於我們從動機的角度來看待情感也很有啟發,如“惻隱之情”這樣的情感,作為道德動力,到底是“動機化”還是“行動化”的呢?恐怕是二者兼而有之。這意味著,在孟子提出的“孺子入井”這個特定道德情境當中,其實也潛在包含了“意欲”的存在,因為“你要去救那個孩子”,這個“述行”(perfomative)活動,就是要實現一種意欲為之或慾望實現的行為。問題是,這種去救助之的意欲或慾望,到底如何訴諸道德行為呢?這就關係到動機與慾望的深層關聯。慾望對於動機而言,乃是邏輯必要的,但其功用卻尚待考察。當代美國重要哲學家托馬斯·內格爾(Thomas Nagel)就曾給出這樣的結論:“慾望對要被確定動機的效應來說,是個必要條件,但僅是邏輯必要條件,無論是作為構成影響還是因果條件皆非必要的。”[7]這其實就把在道德動機當中的慾望之地位加以提升,但同時又對其有所限定,這恰恰說明慾望與動機的那種深層關聯,需要最終加以分殊與確立。
二、“慾望”之型別:從動機、理由與主客方面來看
一般而言,當今西方的情感哲學研究者們更傾向於認為,人類的情感更多與“意動動機”相系,而非與“動行動機”相關。普林茨就基本傾向於這種看法,這是由於,“情感經常引發意動動機,意動動機也經常為情感所引發……意動動機是被行為的命令所感情性地被激發出來的”[8]。這就意味著,這種具有心理偏向的動機,更多是與情感相互引發的,因為無須直接訴諸行為,留在意念當中足矣。然而,當某人受到某種動機驅使做出行為的話,那麼,其中情感的力量就要被理性的力量所壓倒,在道德行為當中,你如此為之要符合善的規則。照此而論,西方學者的研究仍在割裂感性與理性並始終偏倚於後者,中國原典儒學卻將情感也與“動行動機”維繫起來,從而達到了情理圓融與平衡,這也是中國思想可以“反哺”西方之處。
既然“意動動機”與“動行動機”首先被區分開來,那麼,人類的慾望型別該如何與之相匹配呢?這關係到倫理建樹頗豐的內格爾對於人類慾望的基本劃分,他並不贊同休謨及休謨主義者認定某一行為必定為某一慾望所激發的籠統觀點,而更精細地區分為:motivated desire(“激發性的慾望”)與unmotivated desire(“非激發性的慾望”)。內格爾舉例說明,飢餓屬於非激發性的慾望,即直接出現在我們身上的慾望就是未激發而出的,人的飢餓乃是由於糧食缺乏而“引發”的,卻並不是由此而“激發”出來的。反之,激發性的慾望是什麼呢?如果一個人開啟冰箱後發現其中沒有食物了,因為飢餓感,那就要做去商店購買食物的決定,這種有著行動者的決斷和慎思的慾望,無疑就是被激發出來的了。
為了闡明這種經由慎思而得的激發性的慾望,內格爾還舉例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第三卷第三節來加以說明,以證明諸多欲望都是經過慎思而得的。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論述,因為人的某些決定是在“慎思性慾望”(deliberative desire)驅動下去做某事後所做出的,那麼,這種慾望就會與人們所希望的相配。[9]當然,此類慾望與人們所要達到的願望往往會匹配起來,日常行動是這樣,倫理行為也是如此,在選擇了經過慎思而決定去做的事時,我們也會按所做的慎思而去欲求之。
依據內格爾更全面的考量:“每一個有意識的行為的後面都藏著一種激發著的慾望,我相信,這個假設依賴於兩種慾望的混淆,激發性的和非激發性的慾望。”[10]筆者認為,非刺激性與刺激性的慾望之別,此乃一種重要的劃分,前者恰恰與“意動動機”相匹配,後者則與“動行動機”相匹配,這就是從動機來看慾望的型別。“只有當激發性與非激發性的慾望都被執行時,每一個行為的訴求背後都有一種慾望才是真實的,而且,只有在某人追求任何事物的某一目標的動機意義上乃是真實的。”[11]因此,當某類慾望是可以發動行為的,這種慾望一定是激發性的,從而成為“動行動機”;而另一類不能發動行為的慾望則是非激發性的,從而成為“意動動機”,因為它不能直接化作行動。而行動與否就是兩者的根本劃分標準。
較之內格爾更早的哲學研究者,更多從理由(reason)來看到這個問題,當然內格爾也認為,發動行為的,除了慾望,理由本身也可以發動之。而此前的學者,從理由的角度來規定慾望,其實與內格爾也是如出一轍的。美國哲學家斯蒂芬·希弗(Stephen Schiffer)在1976年發表的《慾望的悖論》中,就較早提出reason-providing desire,亦即“提供理由”的慾望,它可以發動行為;而相應的,還有一種reason-following desire,亦即“跟從理由”的慾望,它不發動行為。[12]由此出發,“提供理由”的慾望與激發性的慾望大致相匹配,因為理由決定從而佔據了主導者的角色,所以這種慾望裡面就有潛在的理性參與其中;“跟從理由”的慾望則同非激發性的慾望大致匹配,因為理由只扮演跟隨者的角色,其中感性的力量還是更為強大的。然而,內格爾卻更為保守地看待慾望與理由之關聯:“慾望的現身乃是理由激發的邏輯必要條件(因為此乃邏輯結果)這個事實,並不蘊含它是理由的必要條件;而且,如慾望就由那個理由所激發,那麼它就不能成為理由之內的條件。”[13]
在強調“理由”的基礎上,另一位著名的英國哲學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在其1984年出版的名著《理與人》(Reasons and Persons)中,進而提出來一種“自我興趣理論”(self-interest theory),簡稱“S理論”。帕菲特認為:“如果這種S理論要訴諸時間上的中立(temporal neutrality),他必須提供某些理由,為何我們能夠忽略我們過去的慾望。”[14]這裡面就又提出了中立性的問題,當然還聚焦到了時間性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另文詳述。所謂“執行者中立”(agent-neutral)的那種慾望就是具有客觀性的,之所以被慾望乃是由於其是可欲的(desirable),這就是與執行者無關的慾望,從而也就貼近於所謂的“提供理由”的慾望。與之相對,那種“純屬偏好”(mere prefernces)的慾望則是主觀的慾望了,因為它提供了與執行者相關(agent-relative)的理由,那也就貼近於所謂“跟從理由”的慾望了。這就意味著,執行者越中立,那麼慾望就更加趨於客觀;反之,越與執行者相關,那麼慾望就更加趨於主觀,這是符合經驗的事實。
所以,內格爾在1970年發表《利他主義的可能性》那本倫理學名著的時候,就採取了更為簡易的區分方法,也就是將慾望的依據區分為主觀的理由與客觀的理由。由此推演,慾望無非兩類:一種是“主觀的慾望”(subjetive desire),另一種則是“客觀的慾望”(objective desire)。在此,內格爾似乎在說,主觀的慾望就是從個人立場出發的,客觀的慾望則是從“非個人立場”(impersonal standpoint)出發的。這是由於,“所有的人都處於一個情境當中,所有的觀點、期待和證據條件都與他們相關,落入單一的非個人概念之中”[15]。於是,“非個人的判斷就是由於他人關於相同境遇、相同效果的各種判斷所平等蘊含的”[16],這就引入了與他人之間平等的更復雜的問題。實際上,內格爾在給普遍理由的“普遍性”做論證之時,不只做了上面這種“客觀理由”的論證,亦即論證普遍性不受人稱之影響,而且還做了“無時間性的理由”的論證,亦即論證普遍性不受時刻之影響,而這兩方面也是可共存於同一行動當中的。
我們還是直奔“慾望分類”的主題,內格爾所論的主觀與客觀的衝突,按照帕菲特對之的解讀:所謂“客觀性的宣稱,在此,就是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的宣稱”[17]。這個關乎人稱的推論其實也沒有錯,內格爾的客觀性同時即一種“主體間性”,所以客觀的慾望亦是在主體間得以實現的。然而,遺憾的是,內格爾卻將客觀理由推向某種絕對的普遍性,認定每個人在非個人立場下都葆有行為的發動力量,由此才能為所謂的“利他主義”提供更為堅實的客觀基礎。這顯然是為內格爾的倫理學論證做服務的,因為《利他主義的可能性》這部名著就是要為“唯有客觀理由才是可接受的”做出理論上的辯護,這種辯護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功成尚待商榷,但是由此所做出的慾望劃分卻是頗有洞見的。
簡而言之,綜合以上西方諸論,從“動機”“理由”和“主客”三個方面所見慾望型別及其與動機的匹配關聯,基本可以圖示如下:
表1 從三方面所見慾望型別及其與動機的匹配關聯表
|
(從行為看) 動機 |
(從動機看) 慾望 |
(從理由看) 慾望 |
(從主客看) 慾望 |
|
“意動動機” (motivations) |
非激發性的慾望 (unmotivated desire) |
“跟從理由”的慾望 (reason-following desire) |
主觀的慾望 (subjetive desire) |
|
“動行動機” (motives) |
激發性的慾望 (motivated desire) |
“提供理由”的慾望 (reason-providing desire) |
客觀的慾望 (objective desire) |
三、孔子之“欲仁而得仁”的欲論
出自《至聖先賢半身像》
從比較哲學的角度,對當今西方道德哲學的慾望論所進行的爬梳,乃是為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此對中國原典儒學特別是孔、孟、荀的“欲”論進行反觀與深照。
今本《論語》中,“欲”字共出現42次,欲的語義也有著很豐富的向度和維度。在諸多地方,孔子所用之“欲”,大致就是意欲之義。面對某一物件,可以說“雖欲勿用”(《論語·雍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論語·八佾》);欲也與言說相關,譬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予欲無言”(《論語·陽貨》)、“欲與之言”(《論語·微子》),但這些例證皆與道德無關。
孔子之“欲”也有指主觀的慾望,也就是激發性的、跟從理由的慾望,所謂“欲而不貪”(《論語·堯曰》),與“不貪”相對的欲正是如此。孔子也反對愛惡反覆無常,這種愛惡也都是與欲相連:“愛之慾其生,惡之慾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論語·顏淵》)季康子為盜事多發之苦而求教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顏淵》)根據朱熹注說:“言子不貪慾,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18]由此欲往往與貪相通。
主觀的慾望,還有個更重要的說法則是“所欲”,著名的“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乃是指向道德的最高自由境界了。但如此高境一般人難以企及,孔子更多還是從現實出發來論欲:“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里仁》)這是肯定富貴之慾的正當性,但關鍵在於取之於道。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則是較高層次的道德追求了,這也就超越了本能慾望的限制而不可須臾“去仁”也。這是孔子在肯定人慾的基礎上卻要提升之的人為化努力,蘧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論語·憲問》)就是描述這種道德昇華的艱難過程,但有時欲也成為孔子直接否定的物件。
這就關係到孔子的“不欲”觀,“不欲”看似是對欲之否定,但問題也並不是那般簡單。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就是不要把自身“所不欲”加之於他人身上,但是關鍵還在於“所不欲”的物件到底是什麼?顯然,這裡的“所不欲”的物件乃是消極的,但是“從心所欲”的物件卻是積極的,這樣的“所不欲”與“所欲”就不是對應關係。這恰恰說明,《論語》所欲的物件既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甚至在很多語境中都是混糅未分的。再舉個近似於“勿施於人”的例證:“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論語·公冶長》)這個不欲與欲則是相對而言、彼此否定的,顯然也沒有明確指明物件的消極與積極與否。
在論述諸如“剛”這種道德品質之時,負面之慾與正面之剛就相對而出。“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論語·公冶長》)孔子批判申棖有“欲”而不得“剛”,正如《論語集註》中朱熹引程子曰:“人有欲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欲。”[19]李澤厚對之的闡釋則更具西方哲學的意味,他認定這裡的“剛”講的是“道德意志的構建”:“道德意志及力量表現為感性的行為和實踐,其內涵卻在於這種‘理性的凝聚’,即理性對感性(包括‘欲’)的絕地主宰和支配,這是道德理性之所本。不管說它是外在超越的絕對律令,或者內在心靈的‘良知呈現’,其特徵都在乎此‘剛’。”[20]事實上,這種的確是一種“過度闡釋”,如此來闡發孟子“向善”似乎更為合適,而言說孔子似乎就顯得過猶不及了。
因為在孔子那裡,欲並沒有那麼強的道德意志的力量訴求,而這恰恰是孔孟論“欲”之別。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這恐怕是孔子“欲仁”最核心的論述,但這裡的欲本身卻並無明確的“向善去惡”的道德意志訴求。孔子所謂的“欲仁而得仁”(《論語·堯曰》),當然有著“知善”的內在意思,也有著“好善”的人為追求,但卻沒有“為善”的述行性質。
所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在孔子那裡,“欲”與“仁”的關聯居於核心地位,不僅所欲乃是仁這般高階的積極境界,而且“欲立”與“欲達”皆是為了“成人”。孔子只講“未見好德(善)如好色”,這僅是個經驗事實的陳述,卻從沒說過“好德(善)如好色”,更沒有從反面言說“惡惡如惡臭”。因為此種好善惡惡,源自道德意志的力量,到了王陽明那裡更是將良知首當“是非之心”,進而才推向了“好惡之心”,[21]這便是孟子的一脈傳承了。
四、孟子之“可欲之謂善”的欲論
出自《至聖先賢半身像》
據《孟子引得》所列,《孟子》中出現“欲”字共95處。[22]按照現代慾望論觀之,孟子既關注主觀的慾望,也關注客觀的慾望,“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孟子·告子上》),但是當二者不可兼得之時,那麼儒家做出的選擇就是“捨生取義”了。這意味著,那種“提供理由”的訴諸道德踐行的慾望,要高於“跟從理由”的對生命的慾望。
孟子以一種排山倒海的道德氣勢論述生與死的兩面:“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闢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闢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闢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孟子·告子上》)生當然為人所求,死同樣為人所惡,但是有道德情感的力量卻讓“所欲”與“所惡”皆甚於生死,由此有德之人才會既不苟且也不避災,在孟子看來,這種超越生死之心不僅聖人獨有,而且也應是人人皆有的,這就訴諸一種道德的普遍性。
實際上,如此追求高階道德層次的孟子,並不簡單地否定人類的基本慾望,也就是那種口耳享受的非激發性的慾望。正如“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這就是人類基礎性慾望的共同感,但是孟子卻用這種低階慾望的共通性,進而論證人人都具有道德的高階共通性,這就形成了一種自下而上的感性化的論證方式。《孟子》諸篇大都是以“情”動人的,往往訴諸一種道德的感性力量來打動讀者。孟子總是試圖用“德”來解“欲”的難題:“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萬章上》)
孟子道德論證的關鍵之處,就是把“主觀的慾望”悄然替換為“客觀的慾望”,把慾望當中的“跟從理由”轉化為“提供理由”,只不過跟從的是本能性的理由,而提供的是道德化的理由。且看孟子如此論證:“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孟子·告子上》)每個人皆愛慾尊貴,人同此心,每個人內心都有所尊貴之處,只是沒有得以反思,他們所認定尊貴的東西並不是更可貴的“尊貴”。這就是孟子轉化之處,究竟什麼是“良貴”呢?這就需要“捨生取義”那般的道德提升,也就是讓人對道德的訴求能如對生理慾望滿足那般自然化。所謂“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這也就是要將這種天生的良知、良能作為人類的基本稟賦。
源於這種道德要求,孟子的確有某種“節慾”的傾向,但是卻並沒有“絕欲”的取向。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盡心下》),寡慾以養心為鵠的,寡慾者不存心並不多,而多欲者存心者也很少,這展示出心與欲之間的辯證關聯。哪怕是“無為其所不為,無慾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盡心上》),也往往被闡釋者歸之於“反心”的高度。《孟子集註》引用李氏之言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23]其實孟子的本意,更接近於不幹所不該乾的,不要所不該要的,僅此而已,而未必處處都昇華到“心”之高度。
與孔子更關注“欲仁”不同,孟子道德思想的主流是“欲善”,所謂“可欲之謂善”(《孟子·盡心下》),這個“可欲”就有著非常明確的道德取向了。這種“可欲”內部,定有道德意志的力量在起作用:首先,就要“知”善與不善,所以才能向善;其次,還要從知到行,乃有“為善”的動力;再次,終有“好善”的能力,由此才能環環相扣地提升道德境界:“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孟子·盡心下》)在這“善—信—美—大—聖—神”的邏輯上升環節當中,“欲善”儘管處於最底層,但它卻是根本的動力之源,這就要進而追溯到四端之心那裡。《論語·顏淵》中也有一處欲與善連用:“子欲善而民善矣”,但這裡的善卻是具體的,因為還有個對話前提便是“子為政,焉用殺”?此“善”乃是不行殺戮之類的善舉,與孟子那種對善的強烈意志訴求顯然不同。
所以,孟子的“欲”的主導用法,乃是有著強烈的“向善”意味的,“我亦欲正人心”(《孟子·滕文公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離婁下》)、“人能充無慾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孟子·盡心下》)都是如此,此乃“欲善”之故。
五、荀子之“人情之所同欲”的欲論
出自《至聖先賢半身像》
據《荀子引得》所列,《荀子》中出現“欲”字共236處。[24]這在先秦文獻當中是較多的了,但是用語的含義卻顯得更為單薄了。因為在荀子那裡,“欲”既不與“仁”間接勾連,也不同“善”直接相通,反而是與“惡”相關、與“情”相系。筆者曾指出,惡只有廣度而沒有深度,然而善卻是有深度且具有多樣性的,[25]所以荀子的“欲”論相對孔孟實更為簡單一些,而且與“性”產生了必要聯絡,那就需要“心”來加以範導。
先來看從“性”“情”到“欲”的邏輯,所謂“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荀子·正名》)。荀子非常明確地表示:“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荀子·正名》)這恐怕是在“食色性也”之後,中國歷史上較早肯定“欲”之實存正當性的思想了。但是,荀子並不是如闡釋者所論的“以欲為性”,這是因為,從“欲”通向“性”,還有“情”的中間環節,而且另有“心”功能來範導“性—情—欲”。或者反過來說,按照從“欲”“情”到“性”的發展邏輯,恰恰是荀子所見的“欲惡”,順帶了“情惡”,進而下拉為“性惡”,但是“心善”卻讓荀子之“性惡”得以轉化,也就是“欲”使人“化性”而“勉於善”,這就不同於孟子的“儘性”而“樂於善”。這恰恰是孟荀之別,也是二者能夠統合為一的交合所在。
儘管欲的含義並不豐富,但是荀子所論“主觀的慾望”中所涉及的物件,卻是相當豐富的。人類溫飽休息之類最基本慾望需要得到滿足,“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荀子·非相》),荀子對這一層次的欲進行了經驗論的肯定,認為這些慾望都是生而俱來的。在此基礎上,從外在感官到內心還會有各種享受的欲求,“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王霸》)。荀子將目耳口鼻心之慾當作人情不免者,這就把欲與情直接聯絡起來。除了這些慾望之外,在荀子看來,哪怕是精神性的慾望也是功利性的。所謂“好榮惡辱”(《荀子·榮辱》),無論是愛慕追求聲名榮譽,還是對於權勢高位的渴求攫取,都是荀子之所“好”之慾。
然而,這種人之所本有的欲,卻可以從反面成為禮之起源的動力:“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荀子·禮論》)這就是先王的制欲之道,物與欲之間的互動關聯成為禮的發源之處,所要才要“養人之慾”,禮由此才能以“養”來加以規定。關鍵在於由欲入道,“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荀子·樂論》),人皆有欲,小人“以欲忘道”,君子“以道制欲”,而到了聖人層級,“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此治心之道也”(《荀子·解蔽》),而此道乃是從“心”而發的。
由此,在荀子那裡,從“心”“情”到“欲”,就形成了一種以心“治情”“養欲”的關聯。所謂“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荀子·正名》),當然,這是從治國的結果論角度來言說的,但最終在於正面的心之認可,而負面則是情之慾氾濫。“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荀子·正名》)這就關乎荀子意義上的“心”,其所具有的主要是“思慮”的理性內涵,“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荀子·正名》)。這意味著,先天的“欲”的感性化需要後天的“心”的理性化加以擇取治理。
總體來看,荀子所論之慾,主要是“主觀的慾望”,即無須反思而具有非激發性的慾望,其所跟從的是生理與心理的共同欲求。這就是荀子所反覆論述的“人情之所同欲”,這種具有共通感的情與欲,哪怕“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慾,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荀子·榮辱》)。荀子是透過禮的方式來規範情慾,而不是直接在欲的層面上就實現了昇華。孟子則直接把“主觀的慾望”轉換為“客觀的慾望”,把“跟從理由”的慾望改造成“提供理由”的慾望,但是在荀子那裡無須這種內在的轉化,這也關乎孟子的“即心言性”與荀子的“心治情性”的根本差異。
六、結語:人類之慾所本有的“情理結構”
所謂“得意忘言”“得魚忘筌”,運用比較哲學的方法,我們使用了當代西方倫理學的思想對孔、孟、荀欲論進行了闡釋,試圖在原典儒學的語言叢林裡找到可能貫通的理路。這其實是一種互動闡釋:用西學闡釋中國思想的時候,儘管中國哲學被闡明得更清晰了,但是卻在“以西釋中”裡缺失了諸多維度,由此反觀,西方倫理學的理論缺憾盡顯無遺。所以說,哲學比較的結果乃是“雙方互見”或“互見雙方”。
為何當今西方倫理學要如此劃分慾望型別呢?所謂刺激性的慾望之出場,真實意圖就是為了反對行為的感性動力說。一般而言,慾望乃是不用刺激就能生髮出來進而促發行動的,休謨的道德情感主義及其各種當代變體就是如此,這種非刺激性的慾望乃是跟從理由而發的,所以就成為主觀性的慾望。然而,出於為理性主義辯護的目的,證明慾望也具有理性的理由,進而能夠為行動提供正當性的支撐,由此才會出現客觀的慾望之論,此種慾望不僅是主動刺激而發的而且擁有提供理由的能力。這便形成了一種矛盾,情感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的溝壑難以填平,按照西方哲學的先行割裂雙方的思想邏輯,哪怕事後彌合也是難以成功的,而中國情理平衡的智慧在此關鍵處恰可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
顯而易見,主觀的與客觀的、非刺激性與刺激性、跟從理由與提供理由的兩種慾望的劃分,乃是在主客二分基礎上的,而且慾望雙方形成了彼此割裂的關聯。不僅在孔子那裡根本不存在這種欲的裂分,而且在孟荀那裡,儘管孟子始終要把主觀慾望轉化為客觀慾望,荀子只聚焦主觀慾望卻加以內在具體分殊,這種非此即彼的劃分方式也不起任何作用。筆者以為,這種慾望區分描述的無非是人類慾望的基本趨勢,一種是與本能相關、無須理由之慾,另一種則是與諸如道德提升相系之慾,前者當然是感性主導(但也有理性潛在其中),後者看似是理性主導(但也有情感浸潤其間),從而形成了一種情感與理性的內在張力,而中國思想能貢獻給世界的“情理結構”則致力於二者之間的本然融匯與相互貫通。
按照西方慾望所分,孔子論欲有主觀慾望內涵,但是“從心所欲”卻走向了客觀慾望意蘊,但細究起來,其欲論形成了“欲仁得仁”之混整結構,孔子沒有那麼明確的善惡抉擇意味。重“盡心”“知性”的孟子,其論欲更傾向於客觀的意蘊,因為良知良能訴諸“欲善”的道德意志。重“禮化”“化性”的荀子,其論欲基本上就是主觀的內涵,人類共通之慾與惡相通,但透過外在禮的教化和認知心的向善功能而加以濡化。大致說來,孟子所論之慾是激發性慾望,因為這種客觀慾望的確要為道德行動向善提供理由;荀子所論之慾是非激發性慾望,此類主觀慾望導致了道德行動向惡而發所以才是跟從理由的。孔子介於二者之間,或者說,孔子之慾,雖並未超出無善無惡,但並沒有明確善惡指向,這多元可能性引發出孟荀善與惡欲論的兩種趨向:孟子是心善—性善—情善的“自上而下模式”,荀子則是情惡—性惡—心善的“自下而上”的模式。[26]
總之,中國原典儒學的欲論,揭示出本土“情理結構”的智慧正規化,它既超出了主客欲的二分法,又讓情感主義與理性主義對矛盾得以化解,從而為人類慾望此類根基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種返本開新的綜合思路。
[1] 劉悅笛:《儒家何以無“絕對惡”與“根本惡”——中西比較倫理的“消極情性”視角》,《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9期。
[2] R. S. Peter, “Motives and Motivation,” Philosophy31, no. 117 (1956): 121; R. S. Peter,The Concept of Motivation(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0), 27–51.
[3] Jesse J. Prinz, Gut Reactions: A Perceptual Theory of Emo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191–196.
[4] Prinz, Gut Reactions: A Perceptual Theory of Emotion, 194.
[5] Bennett W. Helm, Love, Friendship and the Self: Intimacy, Identification and the Social Nature of Perso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11–312.
[6] Gerald L. Clore, “Why Emotions Are Felt,” in The Nature of Emotion: Fundamental Questions, eds. Paul Ekman and Richard J. David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11.
[7] Thomas Nagel, 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30.
[8] Prinz, Gut Reactions: A Perceptual Theory of Emotion, 195.
[9] Aristotle, Nicomachean Ehics, 2nd ed., trans. Terence Irwin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36.
[10] Nagel, 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 29.
[11] Nagel, 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 29.
[12] Stephen Schiffer, “A Paradox of Desir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3, no. 3 (1976): 197.
[13] Nagel, 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 30.
[14] 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52.
[15] Nagel, 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 103.
[16] Nagel, 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 107.
[17]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 155.
[18] 朱熹:《論語集註》卷六,《四書章句集註》,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37—138頁。
[19] 朱熹:《論語集註》卷三,《四書章句集註》,第78頁。
[20] 李澤厚:《論語今讀》,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93頁。
[21] 劉悅笛:《作為“心之大端”的好惡本情——儒家“情本哲學”的基本情感稟賦論》,《人文雜誌》2020年第7期。
[22] 洪業等編纂:《論語引得 孟子引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77—478頁。
[23] 朱熹:《孟子集註》卷十三,《四書章句集註》,第353頁。
[24] 引得編纂處編纂:《荀子引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10—913頁。
[25] 劉悅笛:《儒家何以無“絕對惡”與“根本惡”——中西比較倫理的“消極情性”視角》,《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9期。
[26] 參見劉悅笛:《以“心統情性”兼祧孟荀——孟子“天性情心”與荀子“天情性心”統合論》,《孔學堂》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