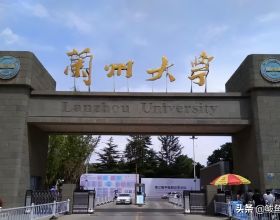母親本意不贊成家裡養狗,她並不是討厭狗,而是害怕生老病死的悲傷。我也只是聽母親說過家裡曾養過一隻退役警犬,是二爺爺在警務單位工作時領回來的,特別通人性,特別聽話,特別勇敢,會幹很多事,甚至可以下水打撈。後來害了病,送到遵義醫學院仍醫治無方,只能眼睜睜看其等死。
母親說:“年紀大了,都有生老病死的時候,狗也是一樣……有一次讓它去池塘裡撈鞋,它有些膽怯不敢下水,被揍了一頓之後奮不顧身跳進了水裡……多聰明的一隻狗,它什麼都懂,給一個眼神它就明白了……它曉得自己不行了……”
我倒是忘了問及叫什麼名字,它已經融入這個家庭成為其中一員,生活中的一些過往讓母親回憶起來感到悲傷,多年過後仍沒有完全消退。據說是得了一種怪病,身上的脂肪慢慢爛掉,身形日漸消瘦,看著那雙留念世間的眼睛就讓人心疼。警犬死的時候哭了,可能是疼的,可能是捨不得人間。
說到底,狗可以不懂人情冷暖,但人不能無動於衷。
多年後,家裡又養了一隻土狗,偷吃別人家的玉米被下了藥,從上山嚎啕著回來,叫喚著繞房屋一圈一圈地狂奔,慢慢沒了力氣,伏在地上哼哼,嘴裡吐著白沫。直至奄奄一息,喘著微弱的氣息,眼角流著淚告別了人間。
我相信動物是有靈性的,即使不如人這般會思考,落葉也是要歸根,臨死都會往家走。家裡的貓被獵人弄斷了腿,拖著殘肢往家走,不知道用了多少力氣和時間,從上山爬了回來,幾天裡一粒米也進不去,終趴在灶臺上走了。這是生命的定律麼?即使身體不能歸家也要拼命讓靈魂有歸宿,要是我將來走到生命的盡頭,會不會也要躺回老家的床板上,用盡最後一點力量來流乾淚水,告別這個世界。
我理解了母親之所以不想養貓貓狗狗,就是見不得如此的場景。
農村家家戶戶都養狗,說是防賊,村裡不乏雞鳴狗盜之事,時不時就有偷個雞摸個狗的小偷小摸之案,這種事一般發生在夜間,倏爾聽見有人高呼拿賊,繼而東南西北“狼煙四起”,雖聲勢浩大,終卻是沒逮住過一回。要是哪家丟錢丟物,父母親在聽到聲援後也便應聲前去,但凡聽到誰家說是丟了小孩,便異口同聲罵道:“又是這個把戲。”於是一動不動地看一場“烽火戲諸侯”的大戲。
開始我不太理解這其中還有把戲,後來才知道偷盜小孩竟變成了自導自演的戲碼,盜者和被盜者裡應外合,終是為了幾分錢財喪盡天良。也有那種真偷真搶的,按母親的說法是,只要自家稍微上點心,哪個強盜敢從身邊把一個活物給抱走?不過我小時候真怕被偷走,說是要被弄去搞成殘疾後幫別人乞討,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小朋友,都被“不睡覺再講話就被偷走”這樣的謊言給嚇大了。
母親說:“強盜偷弱家,火燒邋遢婆。”
我也認為賊是防不住的,許多防盜手段能防君子難防小人,縱觀村裡盜賊下手的物件,都是一些自身不硬氣的人家,不僅偷東西,還能把看家的狗一道給順走了。狗可以給人一個訊號,最終還是要人自己警覺,母親所說的“邋遢婆”,想必就是指那種懶散的人,那種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人。
我家住在路邊上,路過的人不少,母親的意思是放一把水瓢在水缸上,讓過路之人渴了方便舀水喝。有人提醒她東西放在顯眼的地方容易被偷,母親還是不信,說:“哪裡有那麼多強盜。”
過了一段時間,水瓢真的被偷走了。那天夜裡下了一點點小雨,地皮剛溼,母親隨著腳印的方向追查過去,基本鎖定了“小偷”。小偷不在家,母親也沒再追究,她認為只是一把水瓢而已,料小偷自知好歹後再不敢來。
父母在村裡為人正氣,大家這樣認為,她自己也這樣認為,所以她斷定小偷不會再來。事後凡事處處多加了小心,該收的也收了起來。
在這之前家裡也曾遭受過盜賊,倒也不是偷到了家裡來,而是將父親放在地裡的犁給偷走了,母親責備盜賊的少,反而抱怨父親邋遢的多。父親也是幹活累了,不想每日一趟趟將沉重的犁來回扛,圖個簡便放在了地裡,第二天到地裡便傻眼了,連一根趕牛的竹鞭也沒剩下,直呼大意了,早知道就該用些稻草偽裝起來,就不至於在農忙時節還要著急忙慌請木工趕製出一架犁出來。這一回父親得到的最大教訓就是多備份一架犁,而不是看管好自己的物品,因為在後面的日子裡他仍是多次將犁扔在地裡便回了家。
有一天,父親抱回來一隻小狗崽,小傢伙肉嘟嘟的很可愛,一家人你抱來我抱去,估計是家裡很久沒有養動物了,所以喜愛的不得了。只是一隻小土狗,沒人想起來給起個名字,可能是不值當起名字吧,小狗轉眼間就長成大狗,但依然是一隻沒有名字的土狗。
村裡人喚狗就是“嗷”一聲,狗會自動辨聲跑回家來,圍著人一頓轉悠,不時往身上舔,蹭夠了才離開,它覺得這是得到了寵,它對寵它的人始終搖著尾巴,整個面目表情都是幸福。
放羊的時候它跟著上山,叫它去趕羊,就像是得了聖旨一樣立馬要在主人面前表現,飛也似的奔過去,架勢很足。但羊方很強勢,幾隻公羊亮著“武器”,連沒有角的馬羊也敢正面硬剛。土狗見狀一個轉身就跑了回來,搖著尾巴裝可愛,真拿它一點折也沒有。見你正要發火,它便又再去,亦是無功而返,來來回回幾趟,沒解決根本問題。
我後悔沒給它取一個名字,狗多的時候區分起來很不方便。喚一聲“嗷”,所有的狗都回頭。不過能跟我回家的只有它,它知道有家,認識它的主人。尤其當你外出回來,它會提前到路口等著,遠遠跑過去迎接,在腿下面鑽來鑽去,得等它鑽夠了才能抬腿。有時候迎出去好幾裡地,當時我就好奇它是怎麼知道主人回家的時刻的,後來發現並沒有什麼心靈感應,它就是一直傻等,等到回來為止。有時候等不到,耷拉個腦袋很失望。
但我又認為它多少是有心靈感應的,不然它不會一直記得你離開的方向。
它很頑皮,追著牛尾巴咬,一口沒咬著,倒被老牛一個轉身嚇的夠嗆。它樂此不疲,又一趟趟追趕雞群,弄得真叫個雞飛狗跳呀。我們希望它不要去偷吃別人家的玉米,家裡不缺它一口吃的。閒暇的時候,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它在大家的腿下面鑽來鑽去,每個人都撫摸著它的頭。
……
好景不長,就在它與一家人其樂融融之際,家裡來了不速之客。威叔帶來一隻德國牧羊犬,因為其“外國”身份,還因為其一萬塊錢的“貴重”身價,所以格外受寵,很快就取得一個洋氣的名字-----派特。
派特長得很快,高大威猛。一日三餐有人照顧,還有人給洗澡,打上香香的沐浴泡泡,吃的也好。土狗在邊上只剩羨慕,它知道自己沒有這個待遇。
不僅僅是土狗羨慕這種生活,連人都覺得活得不如派特。一條土狗,一條難堪重任的土狗突然間失了寵,當身邊沒有更好的替代品時,貪玩無用的土狗也顯得可愛可親,當有了更好的選擇時,土狗變得一文不值,顯得如此的礙眼。之後,它的一舉一動都要小心,不然捱打是隨時隨地的事。
派特長大之後,土狗越是顯得無用。一起上山放羊,派特趕羊很勇猛,它巨大的身材震懾住了羊群。土狗也跟著去,羊群不怕它,反而把對派特的憤怒轉嫁到它身上,揮舞著羊角追出去老遠。土狗就是逃,它也已經習慣逃跑。
我同威叔上山打獵,派特成了得力的助手,威叔企圖把他得力的助手打造得更加強大,除了日常的起、臥、敬禮,還要教他如何捕獵。得意時甚至對它說幾句英語,可派特就是聽不懂,作為一隻純正的德國血統狗,對英語竟毫無直覺,威叔也納悶了,大概是:仙女墮入紅塵便活成了凡人。
但這並不影響它成為村狗中的佼佼者。
威叔對它要求很高,不能和普通的狗混跡在一起,尤其不能同它們一起出去吃屎,此等不顧及身份地位的舉動,回來是要捱打的。派特有專門的伙食費,狗嘛,跟著什麼樣的主人享受什麼樣的生活待遇。威叔家有錢,養只狗算不得什麼,多一隻不多,少一隻不少。
我小時候也很羨慕威叔家的富裕生活,幻想要是出生在他家該多好,人亦如此何乎狗!
土狗在派特的牙縫裡蹭到一些高檔狗糧,偶爾的時候也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讚賞,但越來越少,微乎其微。它的臉皮被磨鍊得越來越厚,沒有表揚也活得自在,想當初它是多麼的傲嬌啊,曾經也是集寵於一身,享受榮譽的時刻多麼的自豪與得意洋洋啊。
失寵之後,看不出土狗有怨恨,也毫無失落,倒是樂得拾人牙慧,這就是生活最摧殘靈魂之處。
派特的地位隨著長大越來越高,鄰居們紛紛想看一眼,但又不敢靠近,派特真是高大威猛,甚至威猛到讓人反感。每次我放學回來,派特遠遠跑來朝我撲來,我十分擔心會被撲倒,只得提前弓步準備著。我也很反感它的熱情,它伸出舌頭來舔我,它那血盆大口,真分不清那一口是愛那一口是恨。
又過了一段時間,土狗的地位低到了塵埃裡,因為又有幾隻土狗加入了大家庭,列入威叔的嫡系。威叔覺得自己調教狗的水平不得了,嫌一隻養著不過癮,企圖擴大自己的隊伍,出門的時候屁股後頭跟著一隊“人馬”,那場面好不威風。上山打獵的時候也是狗多力量大,俗話說得好,雙拳難敵四手,精兵強將不如群起而攻之。於是到處整回來六七隻土狗,畢竟是嫡系,哪怕是土狗得到的關注也多,待遇和老土狗不一樣。
自此,家裡有九隻狗。
有了調教派特的經驗,威叔以為這是觸類旁通的事兒,能教一隻就能教一隊。事實上卻讓他大失所望,土狗的悟性豈能和純種德牧相提並論,威叔慢慢也知道了並不是自己“領導”能力有多強,好狗就是好教,土狗就是冥頑不化。辛苦了兩月,最基本的敬禮和握手也做的不盡人意,氣得威叔大罵:土雞就是土雞,飛上枝頭也不是鳳凰,充其量是站的高的土雞。
威叔放棄了從軟實力上的調教,轉而專攻捕獵技能,好歹發揮一點作用。吃得肥頭大耳的土狗還不如艱苦樸素的土狗利索,不僅銜不回來獵物,自己也長乎妖妖地跑沒影了,和別的土狗玩鬧去了。
威叔簡直懷疑了人生,自己可謂是用心良苦,給他們吃好的喝好的,然半點作用沒有,要這樣的畜生有何用,一度起了送人的心。但家家戶戶都有狗,多一條狗吃飯卻不幹事,誰也不當冤大頭不是。
畢竟是內部狗員,威叔只能打碎牙往肚子裡咽。但隊伍好歹拉起來了,威叔走在前頭,派特緊隨其後,再跟著一隊土狗。派特去抓獵物,幾隻土狗跟著瞎摻和。派特吃肉,幾隻土狗在旁邊蹲著撿零碎。派特叫喚,幾隻土狗不明所以,也跟著叫喚。
威叔講究管理嚴格和調教專業,買回來一些養寵書籍。翻爛了也不會明白,土狗不是寵物,天生的野性。認為圈起來投給它一些美食,交給它些禮貌,它就會很幸福、很聽話。事實上就是當開啟狗籠,它們飛也似的奔向原野,找尋它們的夥伴,相約著開開心心吃屎去了。
……
再後來,威叔走了,返回縣城,帶走了派特,其他幾隻嫡系土狗被“拋棄”了,留在了村裡。失了寵的土狗不再那麼受待見,因為數量太多,家裡沒有閒工夫 “照顧”它們。只能一一送人,沒人要就送給那些狗販子,其的下場可想而知。
它們到底錯在哪裡了呢?一隻只被狗販子拉走,送到了別人的餐桌上。
它們的命運就該如此?
家裡就剩一隻“老”土狗了。
他還是那樣蹦蹦跳跳。等狗潮退去,才發現它初心未變,生活習慣未變,平添了歲月而已。
派特回到大城市,住進了別墅。我去威叔家的時候,派特已經忘了我,對我張開了血盆大口,這一次我看清了,沒有一絲愛。
派特被關進了大鐵籠子,鐵籠子鉚定在地上,它的力氣太大了,比在農村時更威猛些。但是不再擁有村裡的自由,扔給它什麼就吃什麼,專用經費也取消了,失去了“特權”的派特沒了曾經的“氣質”。在農村的時候,威叔說話“好使”,回城以後,威叔在家裡只是一個吃閒飯的人,一家之主是威叔的父母。
三爺爺和三奶奶不大待見派特,說它總是嚇壞來家裡的客人,教育多次也不懂得收斂,想必是慣壞了,最可氣的是它瘋起來的時候,連主人也咬。派特但凡如人一樣懂得審時度勢,也不至於被關在冰冷的“囚”籠裡。隔壁的別墅裡也養著一隻大狗,不知道什麼品種,一天很少叫喚,懶懶地在院子裡曬太陽,活得十分逍遙。
等我再一次去縣城時,三爺爺家的院子裡只剩下孤零零的鐵籠子了,已不見派特的身影。據說是咬了客人,三爺爺生氣便送了人,甚至沒有一點可惜,過了很久還聽見三爺爺咒罵“什麼畜生”。
是的,它就是一隻畜生。畜生就是畜生,穿了人皮也是人面獸心。警犬歸根結底也是一個畜生,畜生分好畜生和壞畜生。母親說警犬臨死前享受了人都沒有享受到的待遇,那時候農村沒有幾家人能去遵義醫學院那樣高檔的地方看病。
於是,土狗又獨佔了家裡的“寵”,雖不像之前那樣寵,但畢竟集於一身。
有一天,陽光明媚,母親在院子裡收拾衛生,土狗一如既往地打鬧,追一追雞,追一追鴨。母親吼它幾聲,不讓其再弄的雞飛狗跳。
但它似乎很久沒有這麼開心,不聽制止,繼續打鬧。
母親拿著掃帚追過去,它便跑,遠遠地趴在地上回頭看,母親剛轉身它又去追雞,把母親氣夠嗆,便從地上撿起一塊小石頭朝它扔過去,意欲把它趕遠一點。沒想到的是,土狗從此倒在地上沒起來。
母親很傷心。說:“我就扔了一塊小石頭嚇嚇它,誰知道打致命了。”
母親說以後家裡不要再養狗。
似乎家裡後來真的沒養狗,因為我一點記憶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