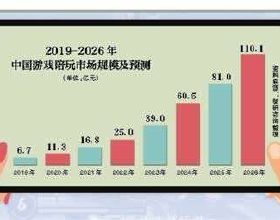我不見她已有十餘年了。
到現在我都不知道她叫什麼,他家裡人也是含糊不清。從我有她的記憶開始,村裡人都叫他啞巴。
來我們這裡的時候,她是會講話的,她的婆婆經常動不動就朝她發脾氣,進而動用工具抽打她。後來也不知道是哪一天,她就只會咿咿呀呀的,一句完整的話也沒有,她那時也只有二十左右。
我見她的時候,總是咿咿呀呀的。婆家這邊就更不待見她了,自從連續生下女孩以後,她在這個家的地位更加惡劣了。從她嫁到我們這邊,她的家裡人也從來沒來看過他,彷彿從此就是陰陽兩隔了。她從此只剩下逆來順受了。
我一直記得她生孩子的那個夜晚。在昏暗的燈光下,她的家人剛開始跑來跑去。她是被放在堆柴草的地方,然後等待著把孩子生下來。隨著嬰兒哭聲的到來,可憐,又是女孩。噓寒問暖是沒有的,傳來了婆婆的罵聲與丈夫的漠然。
這不是第一次,後來還有幾次,她都是在這個地方生孩子,仍就是罵聲和漠然。只有兩個孩子存活了下來。最終也沒有生下男孩。
這以後她的命運更慘了,徹底淪為了勞作的工具。她總是天不亮就得起床,餵豬,餵雞,到菜園裡澆水,到地裡種水稻,割小麥,摘棉花,拔油菜,週而復始,一天接著一天,好像沒有結束的時候。吃飯時是有定量的,端著飯碗坐到外面的石階上匆匆的吃完。家裡人都睡了她才能被允許睡覺。
頭髮每天都是一個樣,亂蓬蓬的。見到人總是吱吱呀呀的。她離開過婆家兩次,每次都被找回來,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
她大女兒出嫁的那天,她又不在了。家裡人也都沒有在意,晚上才發現她不在了。第二天去找也沒有找到,找了很久也沒有找到。終於,她徹底沒有找到了。
後來報警了,也沒有找到。到現在也沒有見到,也不知道是生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