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國民黨發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強令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八路軍限期開赴黃河以北。蔣介石將李仙洲的九十二軍調歸湯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團軍指揮,加上何柱國的東北軍騎二軍,馬彪的青海騎八師,加起來近20萬兵力,向豫皖蘇抗日根據地發起進攻,妄圖將剛剛成立不久的八路軍第四縱隊消滅在隴海路以南。

為擺脫不利局面,新組建的四師十旅向東挺進皖東北,力爭打通與三師的聯絡
為避開強敵正面進攻,擺脫被動局面,1941年3月中旬,奉中央和軍部的指示,剛剛由第四縱隊一部改編組建而成的新四軍第四師開始戰略轉移,其十旅由二十九團打頭陣,東進皖東北,負責打通和新四軍第三師的聯絡,把淮北抗日根據地和淮海抗日根據地連成一片。計劃二十九團完成打先鋒的任務之後,駐紮到五河縣城以北40裡的天井湖一帶,並準備將那裡建成第四師的後方基地。
十旅是由三四四旅旅部及六八八團、六八九團改編而成,共4000餘人,二十九團即原先的六八九團,代號是“浙江部隊”。三四四旅是將近一年前的1940年5月,由黃克誠率領從晉東南出發,途經冀魯豫根據地,到達豫皖蘇的。所以二十九團當時的指戰員中,除了一些從南方長征過來的老紅軍外,很多是陝西、山西人,相當一部分是有經驗的老戰士。

十旅前身是南下的八路軍,戰鬥經驗比較豐富,並裝備有少量迫擊炮等重武器
根據事先安排,由旅政治部主任兼二十九團政治委員高農斧和團長王德榮率領二十九團二營兩個連,和炮兵連、機槍連、特務連各一部以及偵察排等,共400餘人組成先遣隊,為整個團大部隊開路。先遣隊從懷遠縣沙溝集出發,到達曹老集、新馬橋一帶,準備連夜穿過敵人的封鎖線。尖兵排剛過鐵路,敵人巡邏的鐵甲車就開過來了,很遠就開啟探照燈向四面照射,鐵路兩旁如同白晝。大家趕緊就地臥倒,隱蔽在旁邊的麥地裡,雖然這時麥苗不高,但足以遮蔽身體。敵人的鐵甲車照了一陣,沒有發現目標,便開走了。
先遣隊都過了鐵路,又向著天井湖方向走了十多里地,人困馬乏,又飢又渴,天也快亮了,高農斧和王德榮等商量,正想找個村莊休息。這時,突然響起了一陣零零落落的槍聲。難道是遭遇了敵人?不一會兒,尖兵排派人回來報告,原來是前面有個叫王莊的大寨子,聚集了數百人的“聯莊會”,攔住去路,不讓隊伍透過。
原來,魯南、豫南、皖北一帶歷來多兵患匪患,為求自保,當地居民往往數百戶聚在一起居住,莊內外建有護溝、圩牆、碉堡,並置辦刀槍,因地域、宗族的關係結成鄉團武裝,以抵抗小股土匪和散兵的騷擾。到清末時,又出現了若干個鄰近的村莊結為聯盟的情況,稱為“聯莊會”,一村有事,數村一起出動。在當時,這些民間武裝一般都把持在當地豪紳大戶手中,已經變成了一種地主武裝勢力,有的還有國民黨政府承認並撐腰。王莊的“聯莊會”便是本地大姓富戶組成的,又和當地的慣匪和反動會道門相勾結,同受身為大地主的王姓會長支使,專門與新四軍作對。
尖兵排與這個王會長談判多時,對方答應天亮放行。為了不暴露我軍的戰略意圖,高、王便下令部隊停止前進,原地休息。但等到天大亮了,姓王的卻又變了卦,堅決不讓先遣隊通行,數百會眾也跟著一道鼓譟。一方面,是當地從來沒有來過八路軍或新四軍,群眾對我軍缺乏瞭解。另一方面,當時皖東北是地方頑固派(為了和國民黨頑固派相區別,稱之為“土頑”)的勢力範圍,他們擔心新四軍借“過境”之名與之爭奪地盤,加上當時國民黨反共氣焰日囂塵上,就在同一個月,二十九團一營剛剛在蒙城縣南半古店與騎八師三個團打了一場惡仗,損失很大,因此這些“土頑”認為新四軍是“兔子尾巴長不了”,既不願提供方便,甚至想借日寇之手消滅我軍。
拖延的時間越長,就越有可能被鄰近的日軍據點發現,遭到追擊甚至是合圍。對方百般刁難,又提出讓隊伍裡的“長官”過去談判。指戰員們義憤填膺,紛紛要求打上一仗,消滅這股“攔路虎”。其實,真要打起來,就像對方這百十來杆槍,一個衝鋒就解決了。但旅政治部主任兼二十九團政治委員高農斧並沒有馬上同意。高農斧原名高承訓,是陝北綏德人,當時年齡還不到30歲,卻是跟著劉志丹一起鬧過革命的老紅軍,雖然他出身於地主家庭,但是對革命無限忠誠,不僅文武雙全、作戰勇敢,而且能言善辯,政策水平和應變能力都很強。他考慮到新四軍初來乍到,如果就和“聯莊會”發生衝突,容易被敵偽利用,在政治上陷入被動,同時“聯莊會”裡也有大量被裹脅的普通群眾,部隊也會有傷亡,結果都是“親者痛、仇者快”,因此決定儘管爭取透過談判解決問題。
按道理,應該是團長王德榮去談判,高農斧卻說:“部隊處於危急情況,如果團長遇到危險,部隊的指揮就成了問題。”他解下了身上的武裝帶,連同手槍一起交給警衛員,隻身冒險進入寨子中心的王家大院,與“聯莊會”王會長談判。高農斧懷著極大的誠意,耐心向對方解釋了我軍的性質、任務和東進的目的,同時也指出先遣隊雖然帶著迫擊炮、機關槍,但沒有必要絕不會動武,希望對方不要無理攔阻,儘快為抗日部隊讓出一條路來。但王會長一直氣勢洶洶,不僅不為所動,言語中還有將高農斧扣留之意。倒是“聯莊會”的其他頭目被高農斧義正辭嚴的一番話所觸動,提出派人到我軍陣地察看一下,看看是否真的是新四軍,機關槍、迫擊炮是真是假,再考慮是否放行。高農斧見再談下去不僅沒有結果,還有危險,便答應親自帶對方三人到我軍陣地察看,趁機脫離了險境。
“聯莊會”派出的三人都是王會長的心腹,察看一圈,回莊之後,跟王會長一番嘀咕,便對著會眾大放厥詞,說新四軍的迫擊炮是“用面捏的”、“炮筒子給騾子吃掉了半個”。那些會眾信以為真,氣焰更加囂張。王會長趁機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條件,要求先遣隊放下武器,繞道透過。高農斧一聽,啐了一聲:“這‘小舅子’欺人太甚!”他找來炮兵連長關濤,命令道:“開炮!開炮!強行透過!”原來,高農斧早有準備,利用進出談判的機會,把寨子周邊地形特別是到王家大院的距離已經看了個大概。由關濤親自操炮,瞄準王家大院中心的空地,“嗵、嗵、嗵”,接連打出3發炮彈,不偏不倚正中目標。巧的是,3發炮彈沒有炸傷一個會眾,但一塊向上斜飛的彈片飛到了炮樓上,把王會長的大老婆給炸傷了。這時,“聯莊會”的大小頭目和會眾才知道上了王會長的當,新四軍的大炮真不是面捏的,眾人一轟而散,王會長也帶著自己的跟班,一併狼狽逃走了。周圍老百姓看了,無不拍手稱快,說新四軍的炮打得準,“炮彈有眼,沒打著好人”,夾道歡送先遣隊過了王莊。
勝利完成挺進皖東北任務後,1941年3月18日上午,王德榮率領的二營兩個連、炮兵連、機槍連,準備迎接十旅的大部隊東進。快到中午時分,部隊按照步兵在前、炮兵在後的順序,正在由北向南行軍途中,隊伍後方卻冒出了大股煙塵。原來是從濠城出動的數百名日寇加上少量偽軍,分乘10餘輛汽車,以裝甲車掩護,正沿沱河西岸公路進行“掃蕩”,不料在半路與我軍突然遭遇。待發現敵情時,敵人的汽車已接近擔任後衛的我炮兵連部隊,距離還不到500米。
說時遲,那時快,我軍趕緊調整方向,步兵連變成後衛,炮兵連變成了前哨。炮兵連連長關濤一聲令下,炮兵連的幾條槍先開了火,掩護其他人從騾背馱子上搶卸迫擊炮。三班班長霍賽高、副班長朱子同沒等炮座和支架卸下來,先取下一門迫擊炮的炮身,一班長白莫元大叫:“快拿炮彈來,狠狠打他們!”二班班長李繼宗趕緊拖過來一箱炮彈,人作炮架,地當炮座,把炮身插在地上,炮口朝敵方瞄準,迅速連續打出4發炮彈。4個人都是老炮兵,戰鬥經驗十分豐富,操炮技術也很熟練,4發炮彈中有3發擊中敵人行軍佇列,炸得鬼子嘰哩哇啦亂叫,有1發炮彈正好落在車隊的第二輛汽車上,頓時把汽車打著了,冒起了滾滾黑煙。我軍指戰員遠遠看到了,紛紛大喊:“打得好!打得好!”步兵連、機槍連趁著這個機會,迅速展開,全部投入了戰鬥。

白莫元等人利用迫擊炮炮身進行簡便射擊,為部隊展開迎敵爭取了時間
敵人在經歷了最初的慌亂後,也鎮定下來,架起機關槍、擲彈筒、迫擊炮還擊,子彈和大小炮彈像雨點一樣向我軍陣地飛過來。團長王德榮是陝北米脂人,身高1.85米,外號“王大個子”。他打仗有兩個老習慣,一是在原來在軍閥井嶽秀部隊時養成的,不管是冬天夏天,每次打仗都要脫光膀子打;二是用手榴彈打仗是他的拿手好戲,而且特別喜歡用閻錫山兵工廠製造的長把手榴彈,投得特別遠,別人投50米,他能投60米。這次他又光著膀子,雙手各提一顆手榴彈,在前面帶頭衝鋒。但敵人人數佔優勢,火力又猛,幾次衝鋒都未能奏效。二營教導員白常義是陝北米脂人,當時只有23歲,長得很清秀,平時打仗非常勇敢,他在六八九團二營一連“尖刀連”當指導員時,曾和戰友們一道活捉了皇協軍第二軍軍長,在河南安陽還繳獲了鬼子的一門平射炮。但在這場戰鬥中,他腹部被敵人的子彈打穿,腸子流了出來,他便用左手捂住腹部,右手拿著槍,繼續指揮戰鬥,直到因流血過多而犧牲。抗日軍政大學五期畢業的邢蘇民當時是六連指導員,也在這次戰鬥中頭部負了重傷,但堅持不下火線,繼續和戰士們一起打衝鋒。

利用迫擊炮炮身簡便射擊後來成為我軍炮兵的一項“絕技”,屢建奇功
經過3個多小時的激烈戰鬥,敵我傷亡都很嚴重。由於敵眾我寡,彈藥又將耗盡,我軍不得已向西南方向撤退,敵人在後面緊追不捨,戰場上雙方建制一度出現了混亂。炮兵連指導員張維新和一班長白莫元、三班長霍賽高和大部隊走散了,還有兩匹馱炮的騾子和拆散的迫擊炮,其中有一門的炮身不知去向,炮彈都打完了,因此只能算“一門半”。半路上,三人又碰到了機槍連的一名傷員,後者腿負了傷,不能走路,便用一匹騾子馱著他。天色暗下來了,四周都是敵人,再向西南方向撤退已來不及,張維新等4人每人手中拿著一顆手榴彈,隨時準備被鬼子發現了拼命,乘著敵人收攏隊伍時的混亂,牽著騾子悄悄穿過敵人車隊尾部,向著天井湖所在的東北方向走去。為避免被敵人發現,4個人夜間走路,白天隱蔽在破廟、樹林裡。好在當地是游擊區,群眾基礎很好,有的幫著燒水做飯、喂騾子,有的在白天幫著站崗放哨,走了三天三夜,終於回到了天井湖。

在被打散的情況下,張維新等人設法帶著剩下的“一門半”炮成功突圍脫離險境
這時,王德榮也率領部隊甩掉了敵人,回到了天井湖。張維新等人回來,大家都很驚喜,原以為這幾個人不是犧牲就是被敵人抓去了。巧的是沒隔多長時間,三班副班長朱子同揹著那根不見了的迫擊炮炮身,也回到了部隊,大家更加高興。幾個人趕緊到駐紮在上塘集一帶的團部報告。得知兩門炮都完璧歸趙,王德榮說:“你們還人模狗樣地回來啦,我還當小鬼子把你們給那個啦!”不久,二十九團在天井湖召開大會,總結沱西戰鬥的經驗教訓。由於朱子同愛護武器,獨自一人把光滑沉重的炮身從戰場上扛回來,全團大會上特地對他給予了表揚,個人記大功一次,同時獎勵新軍裝一套。

彭雪楓等根據在皖北反頑反掃蕩的鬥爭經驗,後來在岔河專門組建了四師騎兵團
十旅部隊東進開闢泗五靈鳳地區之後,旅部駐在五河縣園宅集,二十九團仍在天井湖一帶活動。1941年8月上旬,根據新四軍軍部電令,為方便指揮起見,四師十旅劃歸三師建制,三師九旅撥歸四師建制。四師在皖東北地區不斷髮展壯大,成為鞏固根據地的堅強柱石,皖東北抗日根據地也成為新成立的淮北解放區的後方基地。
最後說一下高農斧和王德榮的結局。1941年7月底,高農斧帶頭實行主力地方化,擔任淮海區中心縣委書記。1943年春,因長期積勞成疾,組織上特意將他調回延安中央黨校學習休息。但1944年10月,高農斧不幸患上急性肺炎,於當月14日病逝。中央專門在《解放日報》上刊登訃告,並在中央黨校大禮堂為他舉行了追悼大會。至於王德榮後來則非常可悲,在紅軍時代就已經當上了團長,本來當個開國少將沒有問題,但卻因為對革命形勢感到悲觀失望,直至鬼迷心竅,竟在1941年9月部隊過運河時離隊當了漢奸,1944年8月我軍收復泗縣縣城後被處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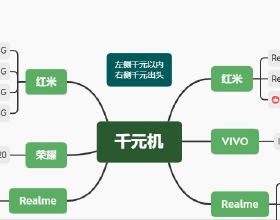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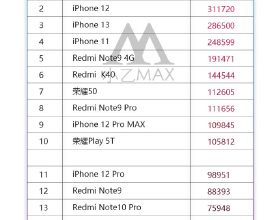



![[經典手機] 諾基亞QD:手機中的遊戲機 [經典手機] 諾基亞QD:手機中的遊戲機](http://i.kkannews.com/thumb/280x220/a/f6/af6c3aa7801f0b9b57081d48a6c302f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