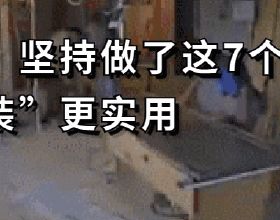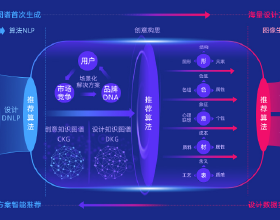文|陳所巨 來源|江淮晨報
縫隙裡有些聲音,甕甕而鳴。山的縫隙叫峽谷,這峽谷太逼仄,太幽
深,那形狀就像一個巨大而幽深的碾槽。碧透的水流似玉,在進入那碾槽之
後就被碾碎了,碾成白色的粉末和跳珠。碾玉峽,對於這山峽來說,是個形
象而恰切的名字。
峽谷兩邊皆陡峭的石壁,壁上懸生著藤蘿雜樹,蔭翳蔽日。右側石壁的
一
處突起的巉巖上有一亭,未見名字,詢問山民亦不知。無名更好,無名就
多了一份猜測與想象。“觀瀑”、“臨峽”都太普通,“聞玉”如何?甕甕然聞碾
玉之聲,就叫“聞玉”吧!
亭的左上方的石壁上,全文刻有劉大櫆先生的《遊碾玉峽記》,劉先生
乃桐城聞人,桐城派重要作家之一。同樣的桐城聞人、桐城派重要作家,曾
經在皇帝身邊當過文學顧問,後來又出任禮部侍郎的方苞曾推介曰:“如苞何
足算哉,邑子劉生乃國士耳!”方苞的文章《左忠毅公軼事》、《獄中雜記》
選在中學語文課本上,也就是說,凡讀過中學的人,沒有不知道方苞的。連
方苞都稱其為“國士”,足見大櫆先生文章的驚人之處。劉先生為人為文皆瀟
灑,只是仕途不濟,鄉試屢屢不中,一生最大的官,也只做到黟縣教諭。這
在當時冠蓋滿京華、尋常陌巷隨處可見進士第的桐城,實屬奇怪。但也正因
為如此,才增添和保留了他的靈氣與才華,進而奠定了他在桐城文派中的重
要位置。劉大櫆遊碾玉峽當在二百多年以前。峽谷依然,水聲依然,而今我
又來了,那二百多年的時光究竟改變了些什麼?大櫆先生“與二三子捫蘿涉
險,相扳聯以下”,又“引觴而酌,既醉,瞪目相向,恍惚自以為仙人也”。我
未帶得酒來,卻也有著飄飄欲仙的感覺,是什麼讓我陶醉?心清清的,靜靜
的,似乎又是恍惚的,是時光認同了我,還是峽谷認同了我?
沿峽谷上行百餘步,地勢稍平,谷已成溪,叢生著菖蒲水蓼。左側柳叢
中有一野墅。斜牆坡頂,卻是別緻。墅為兩層,小軒暢廳,該是極好的品茶
飲酒處。然而卻閒置著,空空然陡見四壁。墅亦無名,莫非也是留給遊人一
份猜測與想象罷。亭既名之曰“聞玉”,墅叫“置玉”、“留玉”如何?不,還
是“等玉”的好。人生總有一份等待,而等待總是美好的。
不知那墅的所在,是否當年大櫆先生的“引觴而酌”之地?
走近那峽的中心,鬼斧神工的碾槽便顯出翻天覆地的驚心動魄。可憐那
水,亦可以說可憐那玉,就在那碾槽中粉身碎骨了。聲嘈嘈然,甕甕然,隆
隆然。那是一種曠世的酷刑,還是某種不由分說的再造。水是能改變一切
的,山也思量著以峽谷的方式改變那水。“改變”無疑是一個不知不覺存在著
的驚人的詞彙。我想著其他一些東西,譬如社會、人生,抑或歷史……假如
我置身其中,我會吶喊嗎?我是認同,還是拒絕?
音樂從縫隙中逸出來。水和石頭的音樂,筋骨和血脈的音樂,或者二百
多年前,大櫆先生來碾玉峽“引觴而酌”那酒所點燃的靈性的音樂。當然,實
實在在的當是我被水和石頭的悲壯所激發的生命的音樂了。山與水的生命近
乎永恆,我卻是短暫的,短暫得你幾乎來不及回憶!回憶是一種功夫,想象
是一種功夫,那深深窄窄龐大的碾槽中的苦刑和再造更是一種功夫!世事無
常,總歸讓你把持不住,而你卻無時無刻不在把持著,這就是痛苦!大櫆先
生喝了一罈酒就走了,我站在這裡,在山的縫隙裡,像一粒細小的鐵屑,被
強大的山的磁場吸附。我不能改變山,難道不能改變自己嗎!
金黃的雨點落下,是兩側山崖上野杏樹上熟透的杏子。杏子紛紛到峽谷
裡來,也是想要尋找一種特別的感覺麼?山不動水動,我不動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