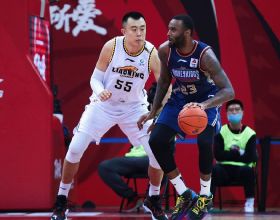來源:光明日報
絲綢之路是一條溝通古代東西方諸文明的橋樑。自從張騫通西域以來,中國與遠至地中海和印度洋的絲路沿線國家、地區和民族建立了直接或間接的聯絡,古代世界各主要文明地區也因此成為一個相互聯絡的整體。
在絲綢之路開通之前,不論是歐亞大陸公元前兩千紀印歐民族的南下與東進,還是以斯基泰人為代表的草原遊牧民族的遷徙,都帶來了遊牧文明與定居文明的碰撞與交融。公元前一千紀中期在伊朗高原崛起的波斯帝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大帝國,西起埃及、愛琴海和多瑙河,東至中亞、印度河,北抵黑海、裡海、鹹海,南瀕紅海、波斯灣、阿拉伯海。波斯帝國幾乎將古代除中國和西地中海地區之外的所有古代文明都聯絡在了一起。隨後的亞歷山大帝國幾乎取代了波斯帝國的全部領土,還增加了巴爾幹半島的希臘本土,其中就包括其發祥地——馬其頓王國。雖然亞歷山大帝國曇花一現,但他開創的希臘化世界卻奠定了未來絲綢之路西段的基礎。希臘化世界的主體就是亞歷山大的部將們瓜分其帝國遺產後形成的三大希臘化王國:埃及的托勒密王國、安提柯王朝統治下的馬其頓王國和亞洲的塞琉古王國。後者的地盤最大,也最難控制。塞琉古王國前三任國王與亞歷山大一樣,致力於希臘式城市的建立,以此來鞏固對當地民族的統治,同時加強對交通要道的掌控,這就無形中拓展了波斯帝國留下的道路系統,從而使得張騫一旦進入中亞,也就意味著踏上了通往地中海和印度的道路。那些分佈於印度西北部、中亞、伊朗高原和兩河-敘利亞地區的希臘化城市,後來之所以有相當一部分轉化為絲路重鎮,它們之間的路線能夠成為後來絲路的主幹道或支線,正是由於此前希臘化世界的存在以及這個世界內外各地之間聯絡的擴大與深入。
然而,絲綢之路的真正出現還是與中國秦漢王朝的崛起以及漢武帝抗擊匈奴、開拓西域的雄韜大略分不開的。秦漢時期,統一的中原王朝出現,可以舉國之力對抗匈奴。但不論是秦朝的蒙恬修築長城,還是漢初的和親政策,都是防禦性的,並不能從根本上遏制匈奴的侵襲。當漢武帝聽聞匈奴同時與它的西鄰月氏人為敵,就想趁機遣使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張騫毅然應募。雖然他輾轉十多年,無果而還,但其西域之行,卻宣告了絲綢之路的正式開通。以張騫為首的中國使者帶回了有關西域的資訊,其中就包括希臘化世界的遺產,比如關於當地眾多的城市、“如其王面”的錢幣、可以“相知言”的通用語、“畫革旁行”的書寫材料和方式,這些與古典作家筆下希臘-巴克特里亞“千城之國”,以及當地考古資料所顯示的希臘化錢幣、通用希臘語、小亞希臘化王國帕加馬的特產羊皮紙、希臘人的書寫方式等頗有契合之處。同時,他們將西域的葡萄和苜蓿帶回長安,將汗血馬的資訊帶給了漢武帝,於是有了遠征大宛之舉。絲綢之路也由此挺進中亞,繼而向西亞和印度發展。從這個意義來講,張騫出使西域不僅標誌著絲綢之路的全線貫通、中希文明接觸的開始,更是古代中國與埃及、兩河、波斯、印度和北方草原文明大交流、大匯合時代的開啟。
張騫先後兩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公元前138-前126年)親歷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同時對印度(身毒)、安息、條支、黎軒等地也有所耳聞。第二次(公元前119-前115年),他坐鎮烏孫,派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地。他的副使抵達安息時,受到盛大歡迎,國王派兵兩萬護送。副使返回時,安息國王又派使節隨同前往,以觀漢之富饒廣大。這些使節帶來了條支的大鳥卵和黎軒的“眩人”(雜技演員),開始了中國與安息在外交、文化與商貿方面的正式往來。中國與印度的交往始於漢武帝時期,接觸的主要是印度西北部的罽賓和烏弋山離。罽賓王甚至接受了漢廷的印綬,成為中國的藩屬。絲路南道也因此新開了一條支線——罽賓-烏弋山離道。至此,“南道極矣”,並可轉道去安息、條支、大秦。公元97年,甘英奉西域都護班超之命出使大秦,走的可能就是這條絲路南道。他本來“臨大海欲渡”,卻被安息西界船人恐嚇而止,中途返回,但至少到了可能位於波斯灣(還有另說)的“條支城國”,應該還經過阿蠻、斯賓、於羅等安息西部的城市或屬國。
大秦可能是中國人對當時“海西之國”犂鞬——羅馬帝國的另一稱謂。因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稱為大秦。儘管漢史中關於大秦的記載是傳說與想象的結合,但其基本的位置、城邑、制度、部分出產與當時的羅馬帝國或者羅馬的東方可大致勘同。公元166年,當自稱大秦王安敦使者的羅馬商人從海路來到中國南端的日南郡時,也就意味著歐亞大陸東西方兩個大國之間有了直接的聯絡。當然,這個事件也標誌著羅馬與中國之間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
公元之後的中亞地區興起了一個新的王國——即統一大月氏五部的貴霜。其全盛時,地跨興都庫什山,連線中亞與印度。它的祖先來自中國西北部“敦煌、祁連”一帶,與中國淵源很深。兩國圍繞對中國西域地區的控制權展開了一系列的外交與軍事活動,中原文明與貴霜文明及其所攜帶的希臘化文明的遺產都在此地留下了交融的印記,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集希臘、印度和中國三種文明因素於一體的漢佉二體錢。
至此,以羅馬、安息、貴霜和中國四個文明並立為特徵的絲路文明互動格局形成。其中,橫亙於中國與羅馬絲路之間的安息帝國,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以及較早與中國進行絲綢貿易,擁有天然的絲路壟斷地位。羅馬帝國對絲綢的大量需求,無疑刺激了安息人的慾望,使其對陸路絲路的壟斷進一步加強。但只要有需求,就會有交換。漢史中關於安息和天竺(印度)、大秦(羅馬)交市於海中的記載反映了絲路貿易的繼續,只不過變更了交易的地點與方式而已。公元前後,由於季風的發現,從紅海可以直航印度,海上絲路初具雛形。從此之後,貴霜統治下的印度,與其相鄰的中國和中亞草原地區,都可以藉助於海上絲路與羅馬通商。
海上絲路的開通,不僅促進了古代諸文明之間商品的交換和流通,而且促進了文化上的交流與融合。希臘化的羅馬藝術就是透過海上絲路從東地中海傳到印度,推動了以希臘羅馬藝術之形表達印度佛教精神的犍陀羅藝術的形成。其後,佛教及其犍陀羅藝術沿著絲綢之路首先傳入中亞,然後進入塔里木盆地,隨後再傳入中原。據說有一位安息王子安世高放棄王位,來到中國傳教,翻譯了佛教經典。漢明帝還派人到印度請回佛僧、經卷和佛像,此為佛教入華的濫觴,從此揭開了中國本土文明與外來宗教文明融合的序幕。公元3世紀以後,薩珊波斯和粟特地區的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傳入中國,其中祆教、景教在中國暫時立足,但信仰者主要是外來的胡人;摩尼教在中國民間的影響似乎長期存在,但唐末之後依附於佛教、道教,蛻變為一種民間秘密宗教。它們與漢文化之間的接觸、磨合、揚棄,實際上也是文明互動的過程。
上述各個文明之間的互動,特別是域外文明與中國文明的接觸和交流,都是圍繞絲綢之路而展開。我們可以看到,西漢王朝為抗擊匈奴而與大月氏建立聯絡,其結果是中國文明與希臘化文明及其遺產在中亞的相遇。東漢王朝與貴霜帝國的接觸,帶來的是佛教的傳入與漢化。兩漢到隋唐時期,中國與安息和薩珊帝國的交往,帶來的是部分佛教經典的漢譯和三夷教的傳入。中國、貴霜、安息與羅馬之間的交往,帶來的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全線連通。因此,不論是絲路的出現、形成,還是它的延伸、拓展,都與沿線文明的互動有關,同時沿線文明的興衰、發展也都與絲路的存在、變化、暢通與否息息相關。也正由於此,研究文明互動視野下的絲綢之路,無疑會給我們今天的“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鑑,那就是互惠互利、平等交流,相互促進、共同受益。
(作者:楊巨平,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