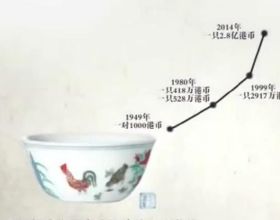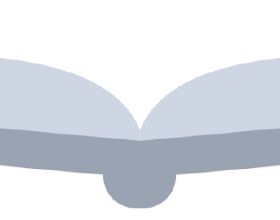田間被掄鋤追攆的“收債主”
那年,有個向爸爸討要升學費的13歲女生,穿著快斷邦的塑膠涼鞋在田埂上奔逃,身後幾根田埂外是怒火中燒,掄著鋤頭要砸死她這個“收債主”的爸爸。
當身後的怒罵聲逐漸停息後,她的耳旁還響著呼呼的風聲和稻穗在雙腿繞絆的哧哧聲。
她試著停了下來,用盛滿驚惶和淚水的雙眼望向爸爸。爸爸杵著鋤把,倚著李子樹,血紅的眼睛在胸口明顯的一起一伏下漸漸潮溼。
一望無垠的深綠色稻田把幾所房屋圍在了中間,其中有一所最破敗的土牆半草半瓦房就是她們家的。隨著木板門急促地“咯吱咯吱”來回晃響,一個又黑又“胖”的中年女人揮舞著一根玉米杆向她們追來,“啪啪啪”地猛抽在男人腿上。
“你要砸死她嗎?啊?別家的娃兒考不上初中想出黑市價還讀不成呢,么女那麼會讀書,你就不能想想辦法嗎?”
男人低垂的頭一動不動,就像是釘在了鋤把上。
“胖”女人走過去拉住女生的手說:“么女,走,跟媽回去,我們慢慢想辦法湊那500元學費。”
窮爸爸的苦悶
那個女生就是我。那個“胖”女人就是我那位人稱“虛胖”的腎病媽媽。她連續幾年都被腎炎折磨著,還患過“歪嘴風”,一直難以痊癒,歪著的嘴說話也不是那麼聽使喚。
我家裡還有一個沒考上初中出不起高價,12歲不到就輟學在家勞作的姐姐。但是她生得俊秀又特像小姑媽,所以深得有眼病的奶奶的偏愛。
她們都說我憑什麼要比姐姐優越,要花費那麼多錢去讀初中?在這滿是老弱病殘滿是負擔的家庭裡,我這個以優異成績考上初中的女兒,就是“收債主”,就是爸爸苦悶的跟源之一。
每年秋收時節,別家是無盡的喜悅和滿足,而我那寡言少語的爸爸卻總是在惆悵、憂思。
每當滿地壩的穀子曬乾後,爸爸總會一擔又一擔地挑到和鄰居們合租的拖拉機上,送去上公糧。
每年媽媽治腎炎和奶奶醫眼病會欠下很多醫藥費;開學後我和姐姐要繳學費;下一季農田需要備肥料、農藥……
所有的開支都寄託在那七畝田的穀子裡,而豐收季節卻是大米最廉價的時候,爸爸總是站在倉口看著那越來越低下去的谷堆,無奈地嘆氣:“到了來年,糧食又是不夠吃了。”稍頓一會,又必須翻進倉裡去把穀子刨出來,挑到鎮上去換了錢,又換作沉重的肥料再挑回來。
人窮親疏
那一夜我聽到我媽一會兒在打哈欠,一會兒又起來上茅房,一會兒又在雞舍豬圈旁走動。
第二天她告訴我:“么女,我算過了,我們家的豬太小還賣不得,但是把雞鴨鵝和豆子全都賣了,再賣點穀子就夠150的學費了,那350的壓金我出去借。”
去哪借?鄰居哪個不是供兒養女的?我媽只有去孃家。我的外婆扯開話題地把那定規矩要壓金的校長痛罵了幾遍,卻沒開口借一分錢。
教書的舅舅把頭昂得老高地吐著菸圈,把我媽訓得無地自容:“怎麼搞的?連個學費都掙不到……”
幾天的疲勞奔波,每一次我媽都是一手撐著腰窩,一手推開那扇陳舊的木板門走進屋,那“咯吱咯吱”聲伴隨著她的低嘆。
我媽的腎炎更厲害了,一整夜她沒排出過一次小便。第二天清早,她整個人就像一塊被髮酵了一夜的大面團,腫脹得變了形。
會“撿錢”的媽媽
爸爸的眉頭皺得越來越緊了,就在他扶著媽媽去赤腳醫生家的時候,我丟下了手裡的活跑了過去,貌似輕鬆地說:“媽,我不想去讀初中了,你看姐才不讀書幾年就長那麼高了,我也不想再愁心只想長高點。”
沒想到我的話卻並沒有舒展開他們的愁眉,反而讓他們更是難過了。
赤腳醫生無能為力地搖著頭把我爸媽打發走了,就這樣他們才愁上加愁地去了鎮上的醫院。
在醫院裡彷彿發生了什麼奇蹟,住了三天回來的媽媽簡直變了一個人。她不但炎症全消體態恢復了,而且還春風滿面地哼起了歌兒。
媽媽說:“么女,放心吧,媽有辦法給你湊學費了!”
從那開始,我媽每天微微亮就提著編織袋,拿著綁了撈魚網的長竹竿,打著電筒出門了。
到了晚上回到家時,她總是一坐下就咕咚咕咚地喝它一盅水,再一臉興奮地讓我們看她倒出編織袋裡的東西——溼漉漉的鴨毛鵝毛。
看著簸箕裡晾出的毛,媽估量著說道:“五角錢一兩,我今天的該賣六七塊錢啦。那個收荒的老頭兒叫一天,還沒有我掙得多呢,哈哈哈……”
原來在醫院裡,我媽遇到了一個拔鵝毛賣的病友。她說自己就是太愛錢,給鵝灌了白酒就活拔它們的羽毛賣給做羽絨服的。現在得了重病要行善,再多錢也不活拔鵝毛了。
我媽多聰明的腦袋啊,她瞬間想起了去舅舅家路上的那條小河,那裡有成群遊放的鴨和鵝,河岸上全是白花花的鴨毛鵝毛,根本就沒人知道可以賣錢,自己幹嘛不去撿呢?
我幸福地踏進了初中校門
報名那天,我一直膽顫心驚地捂著那幾百塊錢。也許天生窮命吧,我居然覺著揣多了錢是一件那麼惶恐的事情。
結果錢還真被我給“捂住”了,原來350的壓金是根本沒有的事,是那些喜歡“造緊張”的家長們瞎編出來的。
雖然好像“大賺”了一筆,可是入學後的生活費、住校費、班費、雜費……也是會時不時地給爸媽壓力的。我媽依然不停歇地天天跑出去撿毛。
有一天中午,我媽到鎮上賣了鵝毛後特意在校門口等我,她想給我買雙鞋子。當我端著飯盒歡快地奔向她後,她難過地看著我說:“么女,她們碗裡的紅燒豆腐幾角錢一份?”
“兩角啊。”
“那你飯盒裡的酸蘿蔔多少錢?”
“酸蘿蔔便宜又下飯,才一角錢”。
媽媽的眼淚就忍不住地嘩嘩流了下來,她拉著我到飯堂裡,硬是要打菜的師傅給我打了一大瓢豆腐。然後又給了我三塊錢,讓我以後不要再打酸菜吃了,每頓都吃上一瓢炒菜。
而且她還對我說在學校晚飯吃得早,夜裡餓了會睡不著,放了學就再去食堂花兩角錢買一個包子吃了再睡。而當時,我要沒吃飯的她買一個饅頭吃,她卻說還沒感覺到餓。
在住校的日子裡,活兒幹得少了,伙食也豐富了,我發現鏡子裡的那個黑丫頭居然也白白嫩嫩了。我就開始想我那黑“胖”的媽媽,腦子裡總是浮現她汗涔涔地穿梭在鵝群中,一小片一小片地撿毛的畫面。然後我就緊緊地捏著手裡的每一角錢,怎麼也捨不得用。
初二催繳學費的時候,被點名站起來的同學裡面第一次沒有我。看著那十來位恨不得鑽入老鼠洞的同學,我感慨萬千地追憶著——在那間小學教室裡,我總是面紅耳赤地拼命低著頭,告訴老師:“我媽說再過幾天就繳……”
雖然老師會盡量地顧及我們這些優生的顏面,不發火逼問,但就光是那樣站著,被一雙雙眼睛緊盯住議論紛紛的感覺,都太抽臉。
在老師安排去給差生講題的時候,我也從來沒有其他優生的那種張揚。原來因為年年繳不起學費而受到的羞辱,真的已經厚厚地壘起了我的自卑。
“撿錢”路上風雨多
初二下學期,出了一個事故,我大聲哭著喊著:“媽,我不讀書了!讓我回來幹活吧!”
有個星期天,我一回家門就聽到媽媽嘶聲裂肺的哭叫,那個悽慘,讓我的心像背上的書包一樣咚地摔到地上。
我推開木板門,一眼望見媽媽那條血淋淋的腿。爸爸跪在地上用顫抖的手給她清洗、搽藥。媽媽使勁地抓捏著椅子扶手,失魂落魄地放聲痛哭著。
“媽,你怎麼呢?為什麼一條腿上全是傷全是血啊?”我心碎地跪在媽媽身旁,驚慌失措地哭嚎著,追問著。
“你媽在去撿鵝毛的路上,被兩條大狗給圍著咬的……”爸爸哽咽了。
我才發現從地壩那頭一直延到屋簷下的血跡,媽媽在被狗咬成重傷後,她是怎樣無助地拖著腿回到家裡的?
“媽!別再去撿鵝毛了吧!我不讀書了,讓我在家幹活吧!”我的良心就像在被人一刀一刀地剮著,那麼痛,痛得那麼深。
星期一的早上,我還是去讀書了。只因媽媽講了一件讓我很受振驚的事。
她說這幾十年裡,從來就沒有人看得起她和我爸。可是就在我以288分(滿分300)的成績考上初中後,周遭的人看她們的眼神都變了,他們充滿了氣憤和羨慕。
很多人都問她:“就你們兩個黑眼窩,咋就生得出那麼會讀書的女娃兒呢?”
很多時候在鎮上,在幹活的田間,媽媽都常會聽到那些人八卦:“喂,你知道嗎,就那個女人,她家裡窮得叮噹響,她倆還是一字不識,可她們卻有個女兒可會讀書啦……”然後就會是一片片的驚歎聲,還有不敢相信、羨慕、研究、偷偷打量的一副副眼神。
原來,我也可以讓爸媽抬得起頭來?
繼續讀書以後,我常常擔心媽媽再遇到意外。可越擔心卻越是起反作用。
在初三的時候,有一次我媽被一群人叫囂著狂追。她嚇慌了,莫名其妙地就逃,他們更加蠻橫地追攆。等把我媽按倒在地後,才聽到一個聲音說:“原來她只是撿了一些鴨毛,不是在偷魚啊?”
還有一次,我媽被放鴨的人臭罵了半天,說她的長杆把鴨子給嚇跑了,和到別人的鴨群裡了。我媽也只有低聲下氣地說,不是故意的,馬上就走。
我常對人說:“我的初中是我媽撿鴨毛鵝毛供出來的。”可是“撿錢”的路上卻風雨太多。
我媽每天來回要走上60多里路,那一小片一小片的羽毛,至少要讓她彎一百多次腰。三年的費用,等於是讓媽媽走了兩個25000里長徵都不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