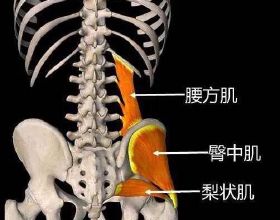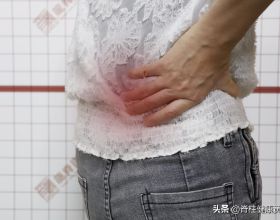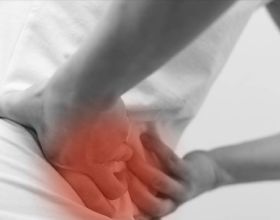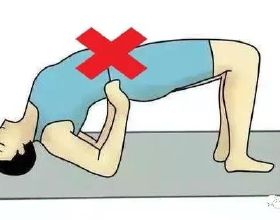一九三四年夏末,繼江西原中央蘇區廣昌縣的高虎堖戰鬥以後,紅三軍團在廣昌以南的驛前地區組織防禦,阻擊向我中央根據地節節迫進的國民黨軍湯恩伯和樊松甫的兩個縱隊。
當時,我們紅四師第十團第三營守在一個名叫“蠟燭形”的高地上。營的右翼是團的主陣地,左翼“保護山”是白軍的主要進攻方向,由軍團的模範團紅十二團防守,他們以全軍團聞名的紅五連控制陣地的要衝。
這個連隊曾經在防守太陽嶂的戰鬥中打垮了敵人一個旅在十二架飛機掩護下的多次攻擊,因此取得了“以少勝眾,頑強防禦模範連”的光榮稱號。
我營守的蠟燭形陣地是由三個高地組成的,我們遵照師、團首長的指示,把稱為全師模範的第八連擺在最前沿的一個高地上,營部率機槍排和第九連守八連側後的高地,七連作為營的預備隊,集結在營指揮所附近的掩蔽部內,準備實施所謂“短促突擊”。
當我們開始構築工事時,師長洪超同志還親自到陣地上來具體指導。他那可親的風度和一口湖北鄉音,至今還鮮明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這時,敵人大概接受了高虎堖的經驗,雖然爬近我軍陣地,但卻沒有立即向我們大舉進攻,只是拚命地修“烏龜殼”。我們也只有抓緊時間趕修防禦工事。就這樣與白軍“堡壘對 堡壘”地對峙了一個多月。
兩軍陣地只隔四、五百米,八連陣地與敵人只隔了一個小山溝,敵人喊吃飯、換哨、修工事的聲音都可以聽清。我們就利用這個條件,向敵人進行宣傳:
“白軍弟兄們!你們是工農出身,工農不要打工農呀!”
“打死壓迫你們的官長呀!拖槍過來當紅軍呀!”
“紅軍是工農的軍隊,你們也是窮人出身,窮人不打窮人呀!”
在我們喊話時,白軍士兵也答話;有時還相互約好,大家都不帶槍在敵我前沿會面,我們送他們豬肉和宣傳品,他們有時也給我們香菸和食鹽。有時正在相互對話,忽然敵人打起槍來。事後他們馬上宣告是朝天空打的,因為他們的官長查哨來了。
當時,紅軍非常重視瓦解敵軍的工作,並把它作為政治工作的任務之一。效果也非常明顯,戰鬥中,有些白軍士兵拖槍過來之後,還特別宣告,他是沒放一槍就投降的,還要我們驗槍哩!
當時我軍的口號是“不放棄蘇區一寸土”,打法是以“堡壘對堡壘”,“頑強防禦,短促突擊”。因此我們的工事也必須做得堅固:支撐點蓋得很厚,有泥土、木頭、柴束、石頭,堆得像小山一樣;各陣地間有交通壕互相接連,前沿還埋有竹釘、鹿砦,利用陡坡挖了峭壁,準備頑強固守。後方也動員得很好,各級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對前方部隊是全力支援的。
在被敵人嚴密封鎖的困難情況下,後方人員只能吃到定量的“包子飯”,而前方卻盡大家吃飽。 但是困難卻日益增加著。尤其是食鹽成了珍寶。當時,如果你出錢買一口豬,我能想法弄來鹽,那就等於是我請客了。生活上苦些可以熬過,最困難的就是彈藥無法解決。
由於打陣地戰,和敵人拚消耗,繳獲少了,只能在敵人遺棄的屍體上搜集少許彈藥。在高虎堖戰鬥時,曾發生過這樣一個笑話:紅十三團打過一天之後,晚上趁黑到陣地前沿去摸敵人屍體上的槍支彈藥,白軍的傷兵忽然哼叫起來,我們有一個戰士嚇得沒命似的跑回來,惹得敵人一陣射擊。
我們初到陣地時,還接受了這個經驗,專門向戰士們進行了一次“有沒有鬼”的教育,好使大家壯起膽子去敵前蒐集彈藥。但是,因為我們一直打的消耗仗,打得多搜回來的少,所以主要還是靠後方少量的補給。敵人欺侮我們火力薄弱,公然爬到離我們陣地二、三 百米的地方修築“烏龜殼”,我們簡直沒法奈何他們。
在這種嚴重的困難情況下,我們指戰員的革命意志絲毫沒有動搖,大家都抱著“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戰鬥決心,堅決守住陣地,準備流盡最後一滴血。但是大家對這種打法卻越來越糊塗,都感到眼前形勢與第四次反“圍剿”以前完全不同了。
那時我們打一仗,部隊擴大了,裝備改善了,地區擴大了;眼前我們與敵人堡壘對堡壘地打了大半年,雖然也打了幾個勝仗,但陣地還是丟了,部隊老是減員,根據地老是縮小,這樣打下去會有個什麼收場呢!大家逐漸對“不放棄蘇區一寸土”的口號發生了懷疑,對與敵人拚消耗的“堡壘戰法” 發生了懷疑。
我們給當時作為戰術方針的“短促突擊”作了一個比方,叫做“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 這幾乎是大家一致的內心話,但誰也不敢在公開場合下提出來,因為在當時 “左”傾路線領導下,很容易因此而被扣上一頂“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
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就產生了一種反常的情緒:每當打仗前夕,總是把所有的錢拿出來買東西大吃一頓。人們邊吃邊說道:“準備拚吧!死了也要做個飽死鬼!”雖然是在說笑話,實際上是表現了對當時軍事路線的不滿。
但是,紅色的戰士們還是以無比的英勇,迎接了防守蠟燭形的最後一戰。
這天,白軍陣地上忽然沉寂起來,每天照例的射擊也減少了。我們在前沿觀察了一下,敵人新修的公路上運輸忽然頻繁了,但陣地上來往的行人反而減少了,白軍士兵忽然向我們喊起來:
“你們辛苦了,我們就來換防呀!”
這分明是暗示我們,他們要進攻了。
當天夜裡,前沿潛伏哨向我報告,聽見敵人前沿有洋鎬聲;我到前沿查哨時,又發現敵人陣地上有閃動的菸頭火光。這許多跡象說明,敵人就要進攻了。我當即把這些情況報告了團首長。
“看來,敵人的主攻方向可能是你們防守的陣地!”
聽聲音,我知道接電話的是團政治委員楊勇同志。楊政委指示了我們應該注意的問題,最後說道:“團決定由其他營調一挺輕機槍給你們,加強你們的前沿火力!”
一挺輕機槍,在當時是多麼寶貴的支援呀!我們全營也不過只有兩挺重機槍和三挺輕機槍呢!
拂曉,幾顆寒星還懸掛在天空,微風吹來,已覺得有幾分秋意,晨霧瀰漫在山間,戰士們已經飽餐並進入陣地。忽然一片馬達聲打破了清晨的沉寂,幾架轟炸機從高空掠過,山間爆炸聲接連傳來,沉重的回聲在山谷裡滾動著。
飛機剛剛扔完炸彈,炮彈就連續飛來,震得掩蔽部裡的土塊紛紛落下,射擊孔也就打塌了。這種猛烈的炮火是一向少見的。原來敵人一個勁的修路,是把重炮隊調來了,這說明他們進攻的規模不小。
我想報告團裡,一搖電話,電線被炸斷了;打算問問前邊八連的情況,電話也叫不通。正在著急,營指揮所又被打坍了。我們只好把指揮所搬到交通壕內去。
透過煙霧,依稀可以望見八連陣地上的情形:他們的支撐點有的已被轟垮,敵人正憑藉前沿的堡壘,以機槍和抵近炮火猛烈射擊我們的陣地;大隊的白軍士兵正像螞蟻般地往上湧,可是他們一衝到我們鹿砦跟前,就趴下不肯起來了,只有那些揮舞著大刀的“法西斯”(我們對敵軍督戰隊的稱呼)還在嚎叫著衝上來。
八連的戰士們英勇地抗擊著敵人。他們從倒塌的支撐點裡鑽出來,依託著交通壕,用手榴彈,用刺刀殺退了敵人一次次的衝鋒。
戰鬥一直持續到中午,我們的彈藥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好子彈都打完了,自己翻造的子彈根本不能裝進機關槍裡打,火力顯著的減弱了。敵人卻以兩個團的兵力,漫山遍野地連續蜂擁而來。炮火打得更兇了。
一看這形勢,我們立即決定調七連上來實施“短促突擊”,便命令司號員吹號。司號員卻不吹號,只是瞪大著眼睛傻里傻氣的望著。我意識到他的耳朵是被炮彈震聾了,就打手勢告訴他。
他恍然大悟,舉起號就吹。只看到他把號放在嘴上,就是聽不到聲音。我焦急地問他:“你吹呀!”原來我也震聾了。他急得把號一摔,自己冒著炮火跑下去,才把七連調來。
七連連長帶隊跑上來。他正接受任務,忽然負重傷倒下了。這時敵人已經衝上八連的陣地,通我們的交通壕也被切斷了,幾個“法西斯”正站在八連的支撐點的頂蓋上,用駁殼槍朝裡邊射擊。七連立即跳出交通壕向敵人突擊,但因遭到敵人側射,剛把敵人趕出交通壕,就已經傷亡過半了。
在這萬分危急的時候,八連戰士們沒有辜負他們模範連的榮譽,奮勇地從工事裡衝出來,把爬上陣地的“法西斯”消滅了。我望見一個戰士端著刺刀,接連刺倒了兩個敵人,當他衝向第三個敵人時,卻被敵人打倒了,另一個戰士馬上又衝上去。
肉搏戰一直打到下午,工事完全被打垮了,我們只能憑藉著交通壕用手榴彈和刺刀迎擊敵人。這時,我們營指揮陣地已成為第一線了,營部的通訊班也投入了戰鬥。
通訊班都是在廣昌戰役後才補充的新兵,打仗沒有經驗,只有通訊班長是第三次反“圍剿”中解放來的。他在白軍北方部隊中學了一手打手榴彈的本事,來我軍後進步很快,打仗非常勇敢。
當時我見許多新兵不會打手榴彈,就從犧牲的同志身上把手榴彈蒐集起來,統統交給他一個人打。他索性赤著胳膊,直起身來,冒著吱吱尖叫的子彈,把手榴彈接二連三地扔進敵群裡。可惜這些手榴彈質量太差,有的還不響,所以雖然打的很準,但仍然不能打退衝來的敵人。最後,只有依靠拚刺刀了。可是有些刺刀也不濟事,捅不上幾下就彎了。戰士們用腳把彎了的刺刀踩直,再端著去刺敵人。
這樣殺過來,殺過去,反覆衝殺了幾次,漫山遍野都躺滿了敵軍的屍體和傷兵。我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最後,八連連長帶著僅剩下的二十幾個戰士從敵人包圍中突圍回來。我們全營就守在一條交通壕裡,準備用刺刀和敵人作最後的一拚。
但是最後我們並沒有和敵人“拚”。由於敵人不顧大量的傷亡,以三、四個團一擁而上的羊群戰術攻佔了我們左翼的“保護山”,打到了我們的左後方,我們這個蠟燭形陣地已經處在極為不利的地位,於是團首長命令我們主動轉移了陣地。
此後不久,我們紅軍被迫進行長征。
多少年來,蠟燭形高地上的防禦戰,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中。它深刻地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關於“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教導,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
在第五次反“圍剿”的那些艱苦日子裡,每當激烈戰鬥和戰壕守備的間隙,紅軍的幹部戰士總是議論紛紛,對這種“堡壘對堡壘”的打法不滿意,想不通,當時,大家是多麼想念毛主席啊!
我記得第一次反“圍剿”時,毛主席帶領我們在運動中調動敵人,從江西的清江向遊擊根據地退卻。隊伍來到永豐,群眾熱情地歡迎我們,但因時機不成熟,我們沒有在這裡打擊敵軍,群眾很不理解,有的甚至在路邊罵我們,問我們“為什麼不打”。部隊繼續退卻到小布,佔領了陣地,做好了打敵人埋伏的一切準備,等了一個星期,敵軍不進,我們又退。
後來,毛主席選擇了龍岡作為殲滅敵人的戰場。戰役開始後,毛主席親臨前線指揮,他站在龍岡後山的半山腰上,親自作宣傳鼓動工作,高聲喊著:“勇敢衝鋒,拚命殺敵,多繳槍炮,擴大紅軍!”大家聽了毛主席的召喚,渾身增添了無窮的力量。
在毛主席的指揮下,我們一舉消滅國民黨軍第十八師主力,活捉了師長張輝瓚,接著,又打垮了敵人三個師,奪取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
從此以後,我們只要見到毛主席來到部隊,就知道要打大仗,就堅信能打勝仗。第二次、第三次反“圍剿”都是這樣。根據地的人民群眾也瞭解和懂得了這種打法,以各種方式配合紅軍行動。敵人來了,我們就堅壁清野,以地方部隊和赤衛隊與敵軍保持接觸,牽著敵人鼻子走,爾後,選擇有利戰機集中紅軍主力各個殲滅敵人。這就是毛主席總結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打法。這種打法,使敵人受到削弱,我軍得到補充,根據地不斷擴大。部隊走得痛快,打得也痛快。
但是,到了第五次反“圍剿”時,情況就截然相反了。走也走不成、打也打不好,部隊天天在減員,消耗得不到補充,撤離中央根據地時,不得不來一個“大搬家”。
那時,紅軍廣大指戰員的心頭都堵塞著一個大疑團,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以後才解開。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擁護者和推行者,剝奪了毛主席對紅軍的領導指揮權把中國革命引向危險的邊緣。他們全盤否定了毛主席關於紅軍建設、作戰指揮的一整套方針原則,強制推行一系列錯誤作法。他們公然撤消士兵委員會,建立所謂“列寧室”,專搞文娛活動,不允許搞三大民主。他們在“反對遊擊主義”的幌子下,把紅軍三大任務,限制在打仗一項上。
他們盲目照搬外國經驗,把適合於山地游擊戰、運動戰的小師、小團、改為大師、大團,削弱了部隊的指揮和靈活機動能力。他們打亂紅軍、地方部隊、游擊隊的三結合體制,取消地方軍,把一些地方部隊改編為正規紅軍,又讓紅軍分散活動,這樣使得地方沒有部隊堅持,紅軍主力疲於奔命,戰鬥消耗無法得到地方部隊的補充,戰鬥力無法得到及時的恢復。
在作戰問題上他們也大搞瞎指揮。在戰略上,他們不承認戰略退卻,誘敵深入,實行所謂“禦敵於國門之外”;在戰役上,他們不承認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極“左”的面貌出現,把所謂“不放棄蘇區一寸土”用於作戰指導,處處分兵把口,以“堡壘對堡壘”,把紅軍置於被動挨打地位;在戰術上,他們不承認殲滅戰,一味搞消耗戰,把陣地防禦中的反衝擊當成殲敵的主要手段,錯誤地誇大所謂“短促突擊”的作用。
蠟燭形高地防禦戰的血的事實,不正是對王明等人最有力的批判嗎? 第五次反“圍剿”我們終於失敗了,這完全是當時“左”傾機會主義領導的結果。
而我們的紅軍戰士們,特別是在戰鬥中與敵人拚到最後一口氣、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英雄們,他們忠實地履行了自己作為一個革命戰士的職責,他們應該是問心無愧的!
張震同志簡介:(1914年10月5日—2015年9月3日)湖南平江縣人,1930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10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張震同志一生歷經紅軍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1985年受命創辦了國防大學,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將軍銜。張震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中央軍委原副主席。2015年9月3日17時,張震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 抗日戰爭勝利時,張震參與領導建立的豫皖蘇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全國19個著名的敵後抗日根據地之一。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張震同志任華中野戰軍第9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部參加隴海路徐(州)海(州)段破擊戰。 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率部參加了朝陽集、泗縣、兩淮、宿北等戰役。 1947年1月,張震率第9縱隊與第6、第7師和第2縱隊一起,在沭陽地區阻擊由鹽城、漣水北進的國民黨軍,有力保障了魯南戰役的勝利。 1947年2月任華東野戰軍第2縱隊副司令員,先後參與指揮了萊蕪、孟良崮、南(麻)臨(朐)、膠東等戰役。在孟良崮戰役中,張震和韋國清同志指揮第2縱隊與兄弟部隊一起頑強抵抗向孟良崮增援的國民黨軍第7軍、整編第83師等部,有力保證了華東野戰軍主攻部隊在孟良崮殲滅國民黨軍“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編第74師。 1948年3月起,任華東野戰軍第1兵團參謀長、華東野戰軍副參謀長。 1948年6月,協助粟裕同志指揮豫東戰役並取得重大勝利,殲滅國民黨軍9萬餘人,改變了中原和華東戰場的戰略態勢,為解放戰爭轉入戰略決戰創造了有利條件。 1948年8月至9月,張震協助粟裕同志指揮濟南戰役,殲滅國民黨守軍10萬餘人,開創了人民解放軍奪取國民黨軍重兵堅固設防的大城市的先例,中共中央在賀電中稱濟南大捷“是兩年多革命戰爭發展中給予敵人的最嚴重的打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