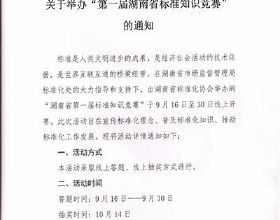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1、在白區工作的黨員如何找到失散黨組織?
1927年4月13日(或14日),陳延年、李立三、聶榮臻自漢口抵滬,找到中宣部鄭超麟,要見羅亦農與趙世炎,原來中央免了羅亦農江浙區委書記,之職,派陳延年來接替。三人從漢口出發時,還不知道“四·一二”。從羅亦農家出來,鄭超麟陪李立三上街買棉被,更重要的是買一副墨鏡。
一旦失去組織聯絡,缺乏經濟基礎的黨員就會很難。
尋找黨的辦法之一竟是十分原始的滿大街去“碰”,大街小巷不停轉悠,遇到同志就接上頭,但若碰到叛徒或特務,那就被捕,接著有可能犧牲。明知危險性很大,仍然只能去“街碰”,因為,別無它徑。
1928年2月,湘潭工委書記羅學瑣(1893~1930),與兩位同志奉調上海,抵達後發現接頭機關被破壞,三人只好站在街頭尋候熟人,巧遇李維漢,給了三人幾十塊錢,才入住小旅館。
同月,湖南省委委員夏明翰(1900~1928),赴武漢尋找組織,每到一處機關與同志家,不是門貼封條就是“已遷別地”。2月7日,總算在街上碰見謝覺哉,夏明翰激動萬分:“省委機關多被破獲,許多同志不知下落,我每天在街上走,指望碰著自己人,真是眼睛都望穿了呵!”
次日,夏明翰因叛徒出賣被捕,旋即就義於鸚鵡洲。
找租房也是“找組織”的方式之一。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後的羅章龍,從東北搞暴動失敗回滬,住在唐山路底,不肯露面。
“非常委員會”女主任張金保帶了幾個人去找,以尋找租房的名義,挨家尋找。當看到一家後門掛著一串紅辣椒,馬上明白是湖南人的訊號,羅章龍乃湖南瀏陽人,說不定就住在這兒。
張金保用生硬的語氣揚聲道:“屋裡有房子嗎?”一人伸出頭:“沒有!”她一看正是羅章龍:“沒有房子嗎?有你就行了!”羅章龍一抬頭,見是“同志”,嚇了一跳,攔著不讓進屋:“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領著一行人上弄堂老虎灶喝茶、接談。
南昌起義隊伍南下潮汕,廣東省委為策應而舉行潮汕暴動,建立了駐存七天的紅色政權——“潮汕七日紅”,後立的紀念碑上刻著1250名犧牲者姓名。部隊最後在湯坑失敗,賀龍與劉伯承逃到香港。
下船前賀龍胖,扮主人;劉伯承稍瘦,扮僕人。上岸後找旅館,茶房引劉看房間,一間又暗又小的房間,劉伯承很生氣,說這也不好那也不行。當他站在鏡子前一看,臉又黑又瘦,一身破軍裝,鬍子頭髮那麼長,這才連忙說替主人來看房間,“差點就露出馬腳……哈哈……”
師黨代表顏昌頤率南昌起義殘部千餘人參加海陸豐蘇維埃。1928年8月顏昌頤受傷,省委指示赴香港療傷,到港後發現省委機關搬走,生活陷於絕境,只好進香港難民收容所。11月,顏搭船赴滬,傷勢更重,身無分文,為尋找組織,拖著病體踟躕街頭月餘,才邂逅相識的同志,接上關係任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軍委秘書,協助彭湃工作。1929年4月,因叛徒白鑫出賣,與彭湃、楊殷、邢士貞一起被捕,8月30日被殺於上海龍華。
尋找黨組織還有一個辦法是登報尋人,用內部化名尋找“哥哥”“妹妹”,外人不明白,同志則一看就知道。
1927年秋,陳碧蘭就是用這種方法在漢口刊登尋人啟事,長江局宣傳部書記鄭超麟代表組織找到她,送上赴天津去會合彭述之的旅費及到上海後的接頭方法。
2、女黨員找黨組織為何更難?
女性找黨組織又多一重困難,五四女性剪辮以示“鹹與革命”,天津南開“覺悟社”回族女青年郭隆真(1894~1931中共烈士),剃光頭表示“不滿現實”。1921年底中國共產黨開辦上海“平民女校”,入學第一項程式就是剪去長辮,改成齊耳短髪。
大革命時期,紅色女性更是剪辮,短髪短辮,湖南白軍流諺:“巴巴頭,萬萬歲!瓢雞婆,遭槍斃,男女學生一頭睡,養出個兒子當糾察隊。”巴巴頭指舊婦腦後的髪髻,“萬萬歲”是說留有舊式髮髻沒事;“瓢雞婆”指禿尾巴雞,短髪女性抓住要殺頭。1933年春,紅四方面軍撒離鄂豫皖不久,王樹聲髮妻胡靜賢,雖已另嫁,但因剪髮、放足,白軍認定是共產黨員而殺了她。
1930年1月,留蘇歸來的朱瑞(1905~1948)在上海街頭遇到兩位莫斯科中大同學,均已“消極”(脫離黨組織),漂流在上海,以寫文稿費度日。
“我們會面時已二、三日不食,餓得面色蠟黃,仍在等他寫作之《墨子問題研究》的稿費以解決食住問題。”
朱瑞回國時在莫斯科領得六七百元路費,“為爭取他(怕他們可能出賣自己),給了他們一些錢,結一下感情。“
1929年6月,1926年國共合作期間的留俄生開始回國,國民政府刊登廣告,以月薪200銀洋招募他們向國府報到。谷正倫﹑谷正綱兄弟就是此時進入國民黨中樞;張如心等為追求馬克思主義,回滬後住棚戶、當碼頭搬運工,甚至吃不上飯,過了一年艱苦生活,1930年才與黨接上關係,1931年6月入黨,8月參加紅軍。
為了隱蔽與不暴露,黨組織要求地下黨員在集體參加國民黨、三青團時,不要硬頂,順大溜加入,調訓也應參加,然後再向組織彙報。
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秘密黨員加入國民黨問題的指示》:
凡服務於國民黨軍政教育機關之秘密共產黨員遇強迫加入國民黨時,就即加入國民黨,但事後必須呈報黨組織追認。
黨組織明確“這是實行革命的兩面政策”,兩面是兩面了,但對思想純潔的紅色青年來說,參加“反動活動”的內心相當煎熬。
3、地下黨員如何接頭?
真正按暗號接頭,程式複雜。1936年初,劉少奇從瓦窯堡赴天津找北方局,化裝成茶葉商賈,身穿緞袍頭戴禮帽,入住日租界北洋飯店。
河北省委秘書長王林去接頭,暗號手持《益世報》,須將《益世報》三字露出;對話:“你是×××先生嗎?”對方:“是×××。”王林再說:“我是李先生介紹來的。”對方讓入房間,將《益世報》放在桌上,這才完成接頭全套“規定動作”。
北滿抗聯一位交通員,從黑河到哈爾濱送情報,到了規定時間,接頭的人沒來。交通員的錢花光了,又不能擅自離開。他便裝病臥床,硬餓了四天,接頭的人第五天才來。此時,等接頭的交通員差不多都快餓死。
反應靈敏是白區幹部的基本素質,1935年春,上海地下黨遭大破壞,夏衍去找田漢,一腳正踏上樓梯,房東家保姆拉了一下他衣角,夏衍立即會意,馬上跑出脫險。周揚、蘇靈揚夫婦得訊只得當即離家避險,身上只有四角錢,只能借宿小旅館樓梯間過夜,“徹夜的胡琴聲和下流笑聲,至今猶在耳際。”這一時期,女青年蘇靈揚的主要任務是“聯絡員”,包括將魯迅從北四川路“內山書店”帶至一家小咖啡店,與周揚會面,以及為剛出獄的鄧潔送衣服等。
茅盾妻弟孔另境(1904~1972),1925年畢業上海大學中文系(與戴望舒、施蟄存同學)同年入黨。“四·一二”後任中共杭州縣委宣傳部秘書,1927年12月14日,縣委於西湖飯店開會,佈置暴動。孔另境留守機關。次晨,不見宣傳部長池菊莊與沈資田回來,便約另一同志上西湖飯店去找,剛入走廊,茶房遠處搖手。茶房並不認識他倆,但能看出他們要上哪個房間。兩人大驚,知情不妙,分頭逃命。“全靠那位茶房搖手示意,否則兩人一定會落入敵人的蹲守伏擊之中。”一個多月後,這次被捕的六七個人全部犧牲。此時避居戴望舒家的孔另境從街頭得知凶訊。
一日,他(孔另境)外出至近西湖的一條馬路上,突見有短工十餘人,抬了七八口白色薄皮棺材,沿湖濱而來。駐足而觀,見每棺材頭均有黑字標明共匪XX之姓名,其中除池菊莊、沈資田、馬東林(杭縣組織部長,農民),還有一個是張秋人(中共首任浙江省委書記)。
孔另境後與組織失去聯絡,從事文教,抗戰後期被日本憲兵逮捕,1949年後為上海文化出版社編輯。這一時期,周揚要用相當時間“找錢”,他向章漢夫、夏衍、羊棗(楊潮)、譚林通、梅雨(梅益)等借錢,借的最多的是周立波、沙汀。有時僅有的一塊錢得上菸紙店兌開,幾人瓜分。史沫特萊支援過他們50元。由於有革命與愛情,“同志們來到我家,談笑風生,從無倦意,我們的工作和生活總是熱氣蒸騰。”兩個口號論爭停止後,周揚不再擔任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兼文化總同盟書記,冷清下來。周揚、蘇靈揚夫婦“卻一點也不覺得輕鬆愉快”,他們往的是“沸騰的生活”。
4、假夫妻
地下黨員有時需要扮演假親戚、假夫妻,因為當時租房,“有房出租”招貼上多附四字——“非眷勿問”。尤其上海房東認為單身漢大多是共產黨員,結過婚的人,較為可靠。柔石與馮鏗也扮過假夫妻去租房。
影片《永不消逝的電波》李俠原型李白(1910~1949),湖南瀏陽農民,1925年入團並轉黨,參加秋收暴動,上過井岡山,參加長征,紅五軍團無線電隊政委。1937年10月,李白由延安來設立電臺。組織為他物色“太太”以便租房,先後找了女中學生、女教師。見面後,李白覺得都不合適。這才找到23歲綢廠女工裘慧英,最初,裘慧英十分不習慣與陌生男人同居一屋,太尷尬了,要求回廠,李白用“大道理”壓住她,兩人由假成真,1940年成婚。
另一對上海地下電臺夫妻秦鴻鈞(1911~1949)、韓慧如,也是組織“撮合”,先假後真。1949年5月7日,秦鴻鈞“犧牲於黎明前”。
1928年春,無錫農運領袖嚴樸(1898~1949,“六大”代表),組織滬郊奉賢千餘農民暴動,後從事法南區黃包車伕工運,組織決定小腳女姜兆麟(1893~1971)以妻子名義入住“機關”,嚴樸扮黃包車伕早出晚歸,不出門時穿西裝充少爺,姜兆麟在機關內做會計兼秘書。一段時間後,假夫妻成了真夫妻。
1929年秋,叛徒告密,嚴樸被捕四十多天,胞兄花500大洋贖出,10月調任松江中心縣委書記兼青浦縣委書記,1930年,嚴樸出任浙南軍委書記兼紅十五軍政委,參加進攻溫州之役。1931年冬,嚴樸調中央機關擔任掩護工作,後攜妻進入中央蘇區,嚴樸參加長征,姜兆麟因小腳無法隨行。六天後,姜兆麟被捕,嚴刑審訊,始終偽裝小販,八個月後獲釋,行乞返滬,與中共失去聯絡。1949年後,重新入黨,先後在松江人民醫院、松江地委供給科、專區婦委工作。
1931年3月,李伯釗由上海轉道香港入閩贛蘇區,連絡人送來兩張去汕頭的船票,與“交通員”扮南洋回鄉的假夫妻,路上儘量少說話,一切由會說客家話的“交通員”打理。
電視連續劇《夜幕下的哈爾濱》主角王一民原型李維民(1900~1976),吉林特支書記。1933年9月,李維民與吉林女師學生秦淑雲在哈爾濱組成“家庭”,租居道里商鋪街21號,兄妹相稱,以補課升學為掩護,秘密印刷發行傳單。後搬到道里端街,夫妻相稱,一屋兩床(各靠牆角),李維民職業家庭教師,秦淑雲打字學校學生。秦淑雲1936年初病逝。1949年後,李維民歷任鞍山公安局長、市長。
1936年2月,北京市委書記林楓(1906~1977)調任天津市委書記,老同學幫忙找了兩家鋪保,幾經周折才租下一間房。房東久久不見林太太,不信任林楓,老懷疑他是共產黨。30歲的林楓只能一次次推說家眷快來了。組織很快派19歲的郭明秋(1917~2010)出任“林太太”。從事秘密工作,既得與親屬、同學、朋友斷絕來往,也不能去看電影、外出散步。林楓經常不在家,在家不是看書就是看報,郭明秋煩悶極了,要求調工作。林對她既講“職業革命家”的大道理,又講“請你做我保護者”的小道理。是年夏天,他倆正式結婚,但不能拍婚照。
最著名的假夫妻是“刑場上婚禮”的周文雍(1905~1928)、陳鐵軍(1904~1928),周文雍乃廣州市委組織部長兼工委書記、廣州暴動總指揮部行動委員會委員兼工人赤衛隊總指揮。陳鐵軍是廣州市委幹部,他倆遵照組織指示,假扮夫妻租,房為秘密機關。1928年1月27日(除夕),兩人被捕,旋判死刑,法官問有何要求,周文雍要求與陳鐵軍合影。2月6日,兩人一起就義於廣州黃花崗。
彭詠梧、江竹筠(江姐)也是由假夫妻轉真。
1943年4月,組織找江竹筠談話:“江竹筠,給你一個艱鉅的任務。“江竹筠說:“越艱鉅,越有幹頭!”領導笑笑:“這個任務呀?,不大好辦羅!”市裡一位領導急需助手跑交通,江姐:這有啥不好辦,行!領導:還有照顧他的生活。江姐說:怎麼照顧?煮飯、洗衣,我會,我樣樣都會!”領導:他是個單身漢,你去扮他的太太,好掩人耳目。”這……”江姐低下頭,臉上瞬間通紅。領導:怎麼樣?任務艱鉅吧!她和彭詠梧的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
1941年夏,南方局安排女青年李冠華攜電臺隱蔽起來,日後必要時起用。南方局組織部秘書榮高棠將李冠華送到李莫止同志家。李家有老母、弟弟,沒有妻子,李冠華便成了“老婆”。四十年後,榮高棠(1912~2006):“後來他們真的成了夫妻。…...這也是組織上怎麼安排就怎麼辦,沒有二話的例子。黨員絕對服從組織。”
地下黨員另一麻煩是不斷搬家,挑選地點就很費神。首先不能獨門獨居,得有後門,便於撤退。附近最好有便於躲避之處;前面得有窗戶,便於觀察;四周還不能有敵特或“政府人員”居住,也不能與同志住得太近…...1927年7~8月間,夏明翰、鄭家鈞夫婦搬家十餘處。
1929~1931年,陳賡、王根英夫婦搬家五次。地下工作另一規矩是不能告訴孩子自家門牌號碼及父母真實姓名,更不能在孩子面前談工作。1931年,中央特科領導人陳賡三歲孩子悄悄上街玩,見“紅頭阿三”(英租界印度巡捕)挎著槍,一邊走近一邊說:“紅頭阿三的槍,沒有阿爸的槍好。”
巡捕便跟著孩子回家,問王根英:“你們家有槍嗎?”1925年入黨的王根英接答:“有,有支槍,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給他買的玩具槍。”幾句話支走紅頭阿三,原來,前幾天陳賡將槍藏在枕頭下,讓孩子看到了。
5、組織紀律大於天
夫妻有可能是假的,組織紀律則是真的。即便假夫妻成了真愛人,不該知道的事堅決不問不談。蘇靈揚1938年才在延安入黨,1934~37年還在黨外,與周揚同床,但還不是同志。許多黨內活動周揚不能告訴她。
周總理和鄧大姐也是如此,總理聯絡的人,鄧大姐不知道;鄧大姐聯絡的人,總理也不具體知道。“我們也是這樣。那時,我們住在紅巖辦事處樓裡,房間很小,大家住在一起,每天進出走一個門,吃飯、生活都在一起,熟極了。但是,他乾的什麼我們不問,不知道,現在,沒有哪個人可以知道當時的全部情況。
再舉幾則“組織大於天”的例項。1925年,上海團中央負責人任弼時準備回湘陰看望闊別五年的父母,並將未婚妻陳琮英帶出來。買好船票行李也搬上船,正在為即將見到父母、未婚妻激動,突接組織通知,要他赴北京開會,任弼時二話不說,馬上將行李搬到另一條船,改道赴北京。
1931年1月7日六屆四中全會,瞿秋白被免去政治局委員。散會後,有同志問瞿今後怎麼辦?瞿答:“聽中央的分配。”是年6月,河北省委遭破壞,7月間中央決定瞿出任河北省委宣傳部長,瞿表示:“堅決服從。”後因考慮他在平津熟人較多,不利於他和組織的安全,另派他人,才未成行。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西撒,通知瞿秋白留下。陳毅見他長期患病,身邊又無人照料,看不過去,將自己的一匹好馬送給他,勸他趕緊去追大部隊。瞿謝絕了:“組織上沒決定,我不能擅自前去,要服從組織決定。”
長征出發時,沒人願當婆婆媽媽的家屬隊長,後點到董必武(時任中央黨校校長、最高法院院長),50歲的董必武一口應承,一路出色完成任務,董必武后憶及“家屬隊長”一職:
“叫我去做,我就去做,工作總要有人去做的嘛!我常說我是一塊布,黨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
1935年春,中華全國總工會白區執行局在上海法租界建國路一帶,執行局主任夏爵一與李維漢妻女住在一起,李妻扮夏爵一“岳母”,李女則為“小姨子”,組成一個家庭,三人均靠組織經費生活,生活費、書報費、交通費加起來,每人不過十多塊錢?日子仍算過得去。抗戰後期,白區工作有了較成熟的經驗,提煉出一些口訣。
如對學運,要求學生黨員“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對地下黨員提出“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鬥爭策略“三有”——有理、有利、有節。
1939年夏,清華生榮高棠在川東特委,沒有職業,羅清在重慶沙坪壩省女職校教英文,初中課程,九十多元薪水分一半給榮高棠,1940年8月,榮調入重慶城裡工作,需要在城裡找職業電力公司的張瑞芳幫他在業務科找了一份抄表員差事。榮高棠(後為部級高幹)抄了一年電錶。毫無怨言。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於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