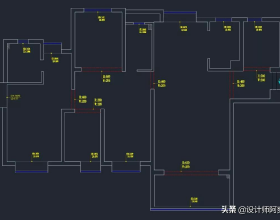作者:式 微
女性與寫作,是一個經久不衰被討論的話題。無論是抑制女性寫作,還是探究女性作家的生活,都始終是引人關注的。當然,關於這個話題,不能忽略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作品《一間自己的房間》。
與其說這是一本書,倒不如說是一篇講稿。1928年,伍爾夫在劍橋大學發表演講,圍繞女性與小說展開,這本書便是在當初演講稿的基礎上擴充而來的。伍爾夫寫作偏向意識流,這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也是很明顯的,當中包括許多潛意識的描寫,引導讀者跟隨伍爾夫的思想與目光走。伍爾夫認為,一間自己的房間與五百英鎊年金是女性寫小說的必要之物。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這都是一個新鮮卻無從辯駁的觀點。但自己的房間與金錢,無論何時,對女性來說都不那麼容易。
伍爾夫在書中設定了幾個虛擬的“真實場景”,幫助女性看到她們身處的環境。比如,牛橋大學(由牛津和劍橋各擷取一半連綴而成)的圖書館,藏書豐富,聞名遐邇,卻拒絕女士的進入,“女士只有在學院研究員的陪同下或持有引薦信,才能獲准進入”。這並非誇張,19世紀下半葉英國才開始逐漸為女性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20世紀初英國政府加強了對高等教育的干預,同時促進了女子高等教育的發展。即便如此,女性在當時的大學中仍處於少數且特殊的地位,薪資與待遇大幅低於男性。這樣的現實,無疑扼殺了女性的知識與見識,使其創作更加艱難。
在後面的敘述中,伍爾夫虛構了莎士比亞妹妹的故事。既然莎士比亞是文學天才,那如果他有一個妹妹,想必其天賦也不會太差。這樣一個擁有文學天賦的女性,但如果離家前往劇院尋找演出與寫作的機會,只會被拒之門外,即便被人收留,最終也只會被困於婚姻與生育。“詩人的心禁錮在女人的身體內,誰又能說清它的焦灼和暴烈”——實際上困住詩歌與小說的並不是女人,而是女人被強加的生育使命與愚拙的刻板印象。這樣的壓迫下,不僅男人覺得女人寫作匪夷所思,就連女人都覺得自己寫作是一種罪過。
18世紀以前,女性創作的文學作品幾乎一片空白,哪怕在戲劇與詩歌無比活躍的文藝復興時期,仍然沒有女性參與。直到19世紀,才開始出現婦女創作的身影,譬如我們熟知的簡·奧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喬治·艾略特。但伍爾夫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當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她們的形象,總是在與男性的關係中得到展現”。這個問題,即使是在近兩個世紀後的今年,也是依然存在的,諸多文藝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偏向於透過男性的視角甚至作為其附庸而出現。
伍爾夫在探討了諸多女性寫作面臨的困境後,再次提出了一間自己的房間與五百英鎊年金。今日我們已經明白,無論對於女性的寫作還是其他生活,經濟獨立都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但在當時的英國社會看來,尤其是那時已婚女性剛剛被允許獨立支配自己的財產,這卻是一個相當超前的想法。正如魯迅在散文《娜拉走後怎樣》中談到的,婦女出走之後,如果口袋裡沒有錢,最終“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只有掌握了經濟大權,才能自由。
在書中,伍爾夫做出這樣一個總結,“五百英鎊的年薪象徵了沉思的力量,門上的鎖意味著獨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可以說,“自己的房間”意味著一個獨立不被打擾的空間,它使寫作者擁有思考的可能;“五百英鎊”則意味著一定程度脫離被壓迫的辛勞,令寫作者擁有思考的時間。這二者的結合,不僅僅是指女性所完成的經濟獨立,更意味著女性擺脫世俗強加的束縛,開始思考自己自由的新人生。我們已經見過太多女性角色,無論是藝術作品中,還是現實生活中,她們即使擁有思考的意識,也尚未得到獨立的能力,這使得她們的天賦早早被扼殺在搖籃裡。
儘管伍爾夫用了一本書來闡明經濟的獨立對女性來說有多重要,但若說這本書僅限於此,恐是狹隘。伍爾夫本身就是一名女權主義者,對於女性主義,她有著自己的完整且獨特的看法。《一間自己的房間》從歷史、偏見、詩歌戲劇等角度講了女性與小說的發展,且從更宏觀的角度論述了男性價值觀的主導,並認為,“任何寫作者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別都是致命的”。
哪怕有些問題如今已經不存在了,但伍爾夫提到的諸多關於女性獨立的觀點,於今日之我們仍有廣闊意義。女性的獨立應該從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開始,但僅有此是不夠的,從獨立思考到獨立的價值觀,再到自己的話語體系,女性創作之路還有很長。(式微)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