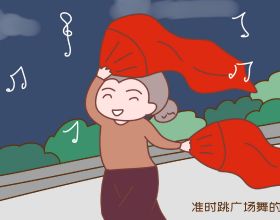作者|程 怡
編輯|秦安娜
微信公眾號:略大參考(ID:hyzibenlun)
騰訊天美工作室的企業微信,群組內的“李逍遙”頭像將永久的暗下去,它的使用者毛星雲,於上週六從騰訊科興大廈躍下,為年僅30歲的人生,寫上終點。
這並非個例,近年越來越多的大廠員工,疑似因為抑鬱困擾,結束生命。
2018年,一名海康威視員工在杭州總部跳樓身亡。公司通告稱,初步懷疑為抑鬱所致。今年1月,入職拼多多不到半年的員工譚某林,請假回家,次日跳樓自殺。拼多多說會對事發原因進行調查,並在公司內部開通心理及特殊緊急事項諮詢通道。
5月,騰訊科興大廈光子工作室一位實習生墜樓,他於微博留下的個人遺書中寫道,自高中以來,就體會不到正常人的喜怒哀樂, 似乎僅僅21歲,我的心就死掉了。
上個週末,同樣在騰訊科興大廈,騰訊天美工作室的引擎組組長毛星雲,選擇跳樓結束自己的生命。
相關報告顯示,抑鬱症已成為僅次於癌症的人類第二大“殺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9年釋出的資料顯示,全球抑鬱症患者總數超3.5億例,中國泛抑鬱人數超過9500萬人,每年約有20萬人因抑鬱症自殺。
10年前,富士康的13連跳,輿論將這些生命的逝去,歸類為流水線工人的苦痛,那些機械化的,超時長工作所帶來的超出身體和心理能力的負荷。以及富士康軍事化的管理風格,將人當做機器一樣,要不停歇的,分毫不差地重複做著同一件事。
但是,當這些有著體面工作的大廠員工,選擇結束自己生命時,外界都無法摸索到壓垮他們生命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
本文的主人公墨菲說,抑鬱症就像是有人在你頭上套了一個黑色的塑膠袋後,對你進行一頓暴擊,你感到很痛,但是根本不知道兇手是誰。
01
霍營開往西二旗的地鐵不過三站,運營時間12分鐘。而墨菲鼓勵自己搭乘早高峰的地鐵去上班,所耗費的時間至少20分鐘。
從起床階段,她抗拒去上班的“內心戲”就已經展開了,從8點25分開始,鬧鈴每隔5分鐘震動一次,但直到8點45分——保證她上班不會遲到的最後時刻,墨菲才會真正從床上坐起來,關掉鬧鈴,走向衛生間。
作為打工人的生活需要,喚起了她應該去工作的身體本能,但心理上的擰巴還在繼續。坐在梳妝鏡前,墨菲在心裡對自己複述,不想見人,不想去上班。其實,她自己也清楚,上班沒有什麼可怕的,同事們都挺熟悉的。
從去年7月份開始,墨菲明顯感覺到自己開始逃避工作和社交的諸項事情,每天都卡在10點進入公司,晚上下班也要9點之後。注意力很難集中,工作越拖越晚。每天的工作時長提升了,工作結果卻在下滑。她在月報中提交的專案進展,越來越緩慢。
跟同事溝通的頻率也在下滑,溝通對接基本上都在電腦上完成。這個時刻她很感謝自己在網際網路企業,溝通、彙報都可以透過線上完成,只要她刻意避免,可以減少很多言語上跟同事之間的交流。
但有兩件事情無法迴避,一是午飯,公司有食堂,所以同事們都會在中午時間段相約去食堂就餐。通常這是“做自己”的時刻,同事之間可以聊聊新追的劇或者是綜藝,附近新開的菜館,相約一起去健身房等等非工作話題。但是墨菲現在卻感覺到想要逃離,她不想談論自己的事情,也不想聽別人講述自己的事情。她就想躺著,大腦一片空白的躺著。為了逃避跟同事一起吃午飯,她會假裝手頭有工作,要晚一會兒吃。這樣的逃避又不能很多次,會顯得自己太不合群,而且太晚食堂也沒什麼好吃的菜了,她只在心情特別低落的時候才會使用,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開會,每週的例會,成為她工作上的困難,她會突然說著話,就忘記下一步要說什麼。有一次開會的時候,提到客戶的一款產品“打滷麵”,墨菲突然之間就忘記了中間的“滷”字要怎麼念,慌忙之中她說了一句“打zhen……”,然後她聽到整間會議室都在鬨笑,坐在對面的女同事用手比劃了推動注射器的動作,大笑的跟她說,打針,墨菲你怎麼想的。
後來怎麼樣,墨菲說她記不清了,她不記得自己有沒有哭,但她記得大家的笑聲,記得自己想飛速逃離那間屋子,卻只能尷尬的坐在那裡,等著笑聲散去,鼓起勇氣繼續講她的方案。
等到去年9月份的時候,墨菲感覺到自己情緒低落的狀態不會是暫時的情況,她的症狀變重了,早起上班前,她有時候甚至會坐在梳妝鏡前流淚,在抹粉底液的時候,看到眼淚從眼眶中湧出,心裡非常的“空”,覺得所有事情都沒有意義。
低落的情緒來的莫名其妙,沒有任何來由或者是鋪墊。墨菲問自己做的一切是為了什麼呢?她不知道,但她也清楚,生活中很多事情沒有變化,變的是她自己。
02
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墨菲早晨上班前,都想要哭泣。所以,在看到醫生開具的診斷書上寫著中度抑鬱和重度焦慮的結果,她沒有覺得意外。就好像你心裡已經知道會是這樣的結果,只是在那一刻有人幫你承認了它。
醫生經過病情問詢,給出的病因是工作不規律,強度高。墨菲在一家網際網路企業負責偏sales的工作,空中飛人,一週至少出差一次,有三到五天的,也有需要當天往返的。墨菲通常趕早班或晚班的飛機,機票便宜一些,到財務那裡審批也方便許多,而且領導也是這樣。
週末經常性會加班,只是地點在家裡還是公司。兩年前,墨菲的媽媽來北京看她,當時她在跟進一個專案,天天加班,沒有時間帶她去北京逛一逛,媽媽只待了7天,就決定提前回老家,臨走送媽媽去車站的,還是她男朋友,她沒有時間去送行。墨菲知道媽媽這趟來北京不開心,但是她已無暇顧忌。她不敢在工作上有絲毫懈怠。
墨菲28歲進入到這家企業,在後廠村員工平均年齡26歲的平均數里,算不上年輕。後續進來的員工,包括校招進來的新人,幾乎都有著非常光鮮亮麗的履歷:985名校、碩士學歷、海歸……大廠員工的工作就再是擰“螺絲釘”,也是一堆兒的高知群體在擰螺絲。
網際網路大廠等同於海淀高校的校友會。在一些部門聚會,或者是新同事的歡迎會上,之前在工作上沒有交集的同事,聊著聊著,突然發現是同一個學校的,一句師兄師姐,兩個人之間的距離拉進了很多,後續的工作對接也容易一些。
但墨菲不是,她畢業於北京普通的一本院校,非211,也非985。夾在一堆高學歷群體中,墨菲有她的尷尬。跟同學相比,她混的還算不錯,跟同事一比,她就有些普通了。入廠2年多,沒有升過職級。三年的勞動合同,即將到期,也不清楚會不會有續簽。
人到30才真真正正感受到外界對一個人的認同,需要經過全方位掃描,教育、工作、資產、人脈等等。年輕時覺得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生活就很有奔頭,隨著年紀的增長,需要的東西越來越多,房子、車子、票子、孩子,缺一點、慢一步都不行。
在數十個失眠的深夜,墨菲想的都是這些事情,還要不要在北京待下去,繼續留在北京要在哪裡買房子,去往二線城市,沒有熟人,怎麼展開新生活,親戚朋友會怎麼看她離開北京,畢竟大廠的工作,讓她在親友眼中,有了光環。
而在墨菲失眠的時刻,她總能聽到隔壁書房,傳出的男友打遊戲的聲音,喊話隊友“上上上,快衝”,或者是輸了之後的國罵,以及扔滑鼠的聲音。
當然,墨菲思考這些,也想不了太久,抑鬱症讓她沒有辦法長時間集中注意力,很多時候墨菲只是想了個開頭,便沒有思緒了,睜著眼聽著書房傳來的打遊戲的聲音。有時候她會在微信上給男友發信息讓他小聲點,後來資訊也不發了,反正也是睡不著,何必攪了別人的興致。
03
確診為抑鬱症之後,墨菲沒有告訴任何人,醫生給開的藥,她也是放在包裡,在上班路上偷偷的吃掉。
她不知道要如何開口,怎麼跟家人說自己得了抑鬱症,病因是什麼?這些她都說不清楚的,她也不知道。
她經常問自己為什麼會抑鬱,對生活哪裡有不滿足嗎?男友除了愛打遊戲,懶散一些,沒有什麼壞毛病。工作上同事之間也沒有什麼爭鬥,大家都是負責自己OKR之內的事情,領導也沒有PUA、職場暴力等行為。
墨菲的直屬領導性格很寬厚。沒有公開批評過組內的任何同事,都是叫到會議室私下說。人也很有耐心,他不會說“你應該做什麼”類似帶有支配性質和命令性質的話語,對待下屬對於工作中的疑慮,總是會耐心的聽完,然後一步步的講清楚,為什麼需要做這個專案。
曾經有一次,墨菲不想跟某進個專案。領導把她叫到小會議室,跟她分析如何爭取客戶,這個專案對部門的OKR和個人的年終考核會有什麼幫助。
最終墨菲妥協了,週五下班後,繼續坐在電腦前,敲出要給客戶的方案。她一邊打字一邊在流眼淚,默默的流淚,同排最右側對面的工位,還有一位男同事也在加班,墨菲不希望他注意到自己。回家的計程車上,墨菲也在流淚,默默的掉眼淚。她不想在陌生的司機面前落淚,但她無法抑制住淚水。
多年之後,墨菲回憶當時的瞬間,她覺得自己的身體早於頭腦捕捉到情緒上的負能量,如果她能更早的注意到情緒上的問題,及早干預,會不會遠離抑鬱症。
但是,生活沒有如果。
即便墨菲沒有開口講過,身邊人也會發現她的變化。她變得不愛穿搭,不喜歡收拾屋子,這以前是她最愛做的事情,不愛吃飯,更不願意外出就餐,也不願意去旅遊了。對生活的熱愛,正在遠離她的身體。
每年的十一和年假,墨菲和男友都會準備旅行計劃,經常是假期還沒到,兩人已經按耐不住遊玩的心情。但去年的十一,墨菲以疫情為理由,說想待在家裡。十一期間,墨菲躺在沙發上刷手機,偷偷看張進老師的《渡過》,頁面翻得很慢很慢,她沒有辦法長時間閱讀。
抑鬱症也影響了她的閱讀品味,她以前喜歡看人物傳記,正能量的雞湯文,喜歡看別人是如何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生病之後,她對於情緒低落的內容,更容易共情。
有一次,墨菲聽到多抓魚創始人貓助,在講座中分享在閒魚工作時的不開心經歷,說她不喜歡那份工作,有一段時間,每天上班前都會哭。那一刻,墨菲從貓助講述的內容中看到了她自己,不過,她沒有貓助離職創業的勇氣。墨菲只是請假,年假、病假、事假請個遍,有一次不知道找什麼理由,便說“不想離開家裡的貓”,她自己都覺得很牽強的理由,但是在OA系統裡,領導也同意了。在請假的事情上,領導沒有多問過,這一點墨菲很感激。
其實,不想離開家裡的貓,並非完全是請假借口。而是很長一段時間的真實寫照。去年9月,墨菲終於養了貓,成了有貓一族,而離家工作變得更困難起來,她捨不得家裡的小貓咪,它那麼小,那麼可愛。
墨菲想過離職,但是沒有底氣。她28歲進入大廠的時候,工作的奔頭便是從三年的勞動合約,換成六年的勞動合約,以及無固定勞動期限的合同。這裡有她喜歡的大廠氛圍,自在,沒有人多在意你,因為人很多,沒有人強制你要做什麼,因為牛人很多,能夠做同樣事情的人很多,外面等著進來做同樣事情的人也很多。
04
獨自承受近半個月的抑鬱困擾之後,墨菲的男友發現了她情緒上反常的消極和突然出現的脾氣,飯桌上,男友半開玩笑、半試探性的問她,是不是抑鬱呀。墨菲繃不住了,放下筷子,哭了起來。男友沒多說什麼,繞過桌子抱住了她。
此後這個家庭發生了些變化,墨菲在廚房找不到刀了,客廳玄關的置物架上,也找不到剪刀了,導致她每次拆快遞都需要用牙籤在膠帶上扎很多小洞,費力的、很暴躁的大力扯開。她跟男友說,沒想過自殺,沒動過這個念頭,對方應承著,但是消失的東西也沒有回到原位。
男友也有了變化,打遊戲的時間減少了,墨菲上床休息,他也會跟過來。兩個人各自想著不同的事情,墨菲閉著眼睛想著人生意義的問題,男友刷著手機瀏覽抑鬱症陪護方面的內容,或者是看Up主打遊戲。週末的娛樂活動也從兩個人出去吃飯、看電影,變成了去醫院接受心理治療,或者參加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的心理疏導活動。
以前,墨菲一直覺得男友不太成熟,缺少責任感。生病之後,男友的變化,讓她意識到,還是要給對方承擔責任的機會。
抑鬱症的“副作用”逐步顯現。服用抗抑鬱藥物氫溴酸伏硫西汀後,墨菲身體出現了不良反應,時常有噁心和乾嘔的情況出現。
去年12月,她想購買一份重疾險,卻被保險公司拒保,因為她的中度抑鬱症和重度焦慮症。她原本是因為得了抑鬱症,才意識到健康和生命的脆弱性,想到要去買保險。但是,代理人說抑鬱症患者終身無法投保重疾險和醫療險,即便治癒也不可以。
今年3月,墨菲的抑鬱症狀變成了輕度,焦慮症狀也是輕度。她渡過了困難時期。情況好轉之後,墨菲覺得自己更自信了,她覺得自己一輩子的負面情緒,可能在生病期間被消耗掉了。她將自己的抑鬱經歷,看做一場30歲危機,在她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迷失在外界對中年人的評價體系裡。
不過,今年合同期滿的時候,她收到公司不予續簽勞動合同的通知。她最終還是離開了大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