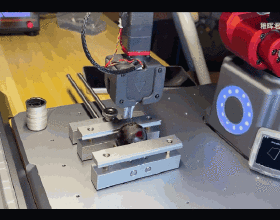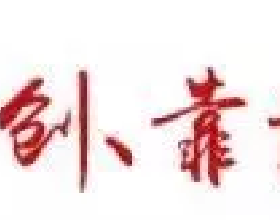來源:嘉興日報-嘉興線上
河蚌,嘉興話稱之為“水產”,是老底子江南水上人家餐桌上的美味佳餚,被譽為“河中鮮”。但是將其從河中一個個摸上來,過程並不輕鬆。
小時候沒有空調,放暑假了,小夥伴們解暑的最佳去處即是環城河。吃過中飯熱得難受,便頭頂木腳盆,相約三兩夥伴去河裡玩水、摸螺螄、踩河蚌。膽大的從橋上飛身往河中一躍,極是瀟灑自豪。我不敢從橋上往下跳,怕摔“大板”。到了河裡,踩水的踩水,扎猛子的扎猛子,仿若鷹擊長空、魚翔淺底。
我游水吃力稍歇時,常會踩著河底的淤泥,緩緩移動雙腳去踩河蚌。那些埋在淤泥中的河蚌,或多或少總有部分貝殼露在泥外,埋得較深的,往往都是大河蚌。我碰到尖尖的或圓圓的蚌殼,就深深地吸口氣,屏住呼吸潛入河底,可正想用力挖出腳底下的那隻河蚌時,卻往往屏不住氣,失去了平衡,腳用力一蹬就浮出了水面。
水性最好的要數堂哥。堂哥雖然只比我大幾十天,但釣魚、捉蝦、踩河蚌絕對是高手,比我強多了。特別是踩水,他在環城河裡能把肚臍眼露到水面上,我們沒一個能超過他。每次摸河蚌,也是堂哥門檻最精。他不是摸,而是踩。堂哥動作乾淨利落,先是在水中輕輕移動,踩到河蚌,屏氣緩緩下沉,水面上泛起幾個碩大的氣泡,只剩下一隻孤獨的腳盆,幾秒鐘後他手中抓著一個帶淤泥的河蚌浮上水面,然後洗淨淤泥,很得意地丟進腳盆裡。
直到太陽快要落山,大家抬著一大腳盆河蚌,趕在大人下班前屁顛屁顛上岸。雖然臉上、身上都曬得黝黑通紅,但心裡卻興奮無比,那一隻只河蚌,扇形的硬殼長著一圈圈的波紋,在陽光的照耀下閃耀著墨綠色的光澤,這就是我們的“戰利品”。拍水聲,浪花聲,嬉笑聲,溢滿河面,構成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夏日城市裡少年的戲水圖。
回到家裡,河蚌大的剖開燒菜,小的送給前面的娘娘家,她家養的好幾只鴨子等來了難得的美餐。“水產”也是肉,可以燒來吃,特別是燒鹹菜吃,很鮮。我拎過一隻小凳,拿來菜刀,剖開一個個河蚌,熟練地取出蚌肉,用鹽漬,洗淨汙物。“蚌病成珠”的故事當然聽到過,於是每剖開一個河蚌,我總希望能有奇蹟出現,見到那光澤閃亮、圓潤晶瑩的珍珠。雖然從未有珍珠出現過。
父親下班回來,開始露一手他的烹飪手藝。只見他把河蚌肉用開水氽燙好,將其放入冷水中,然後瀝乾水分,用刀背將河蚌的硬邊敲松,切成小塊。待鍋裡菜油冒出青煙,把薑絲爆香倒入河蚌肉炒,略加黃酒,再下自家醃的鹹菜煸炒,待燒出鹹菜鮮香味時,加適量清水,大火燒開後轉為小火慢燉,個把時辰就好了。燒好後,院子裡香氣四溢,這頓晚飯小菜絕對的有滋有味,那味道現在想起來舌頭根還會溼潤。
時間像流水般無聲流過。如今城市大了,不僅有一環,還有二環和三環。馬路也寬了不少,還有綠化分隔帶,一脈的綠色,氣派很大,只是汽車太多、太吵、太熱鬧。環城河則清靜了起來,原來漆著綠漆的客輪不知什麼時候退出了歷史舞臺,運貨的拖輪也繞到三環外面去了,鄉下賣稻穀的水泥船早已不見了蹤影。沒有了竹排、沒有了水草,河裡看不到游水的人,更沒哪個愣頭青在大洋橋上燕式跳水入河了。當然,也不會有哪家小孩在河裡游泳,或頂個木腳盆在河裡踩河蚌了。就是膽大的敢下水,估計也沒有“水產”可踩。河水太靜,我倒覺得少了一種原生態的生活氣息。
“棲身淤泥不合汙,堅殼柔體育珍珠。常與河水共翩躚,化作佳餚伴豆腐。”不僅反映了河蚌孕育珍珠的價值,也體現了它是餐桌的一道美食。
我偶爾嘴饞,大熱天的想吃“水產”肉,就約幾個同學到小飯館聚聚。斬盤白雞,再來份油爆河蝦、紅燒鯽魚、“罐頭肉”,再炒份素三絲、蒸碗臭豆腐,小酒咪咪,天南地北地聊,古今中外地吹。吃到最後,上一份久違的河蚌鹹肉篤湯下飯,極是樂惠。
店主將篤了好一會的河蚌鹹肉豆腐湯端上來,雪白濃稠、香氣四溢,蚌肉味美,鹹肉鮮香,豆腐滑嫩,湯鮮味濃,舀一口送到嘴裡,實在是不能錯過的夏夜美味。
河蚌鹹肉湯,屬於夏的味道,它與暑的酷熱一起來到人間,併成為江南的一道美食。至今,它仍然回味於水鄉人家的舌尖,讓人縈繞於懷,我也是。
本文來自【嘉興日報-嘉興線上】,僅代表作者觀點。全國黨媒資訊公共平臺提供資訊釋出傳播服務。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