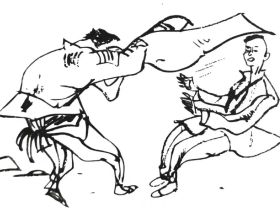絕大多數的人都吃過桃酥。聲稱沒吃過的,八成是忘了,或者桃酥換了一副馬甲讓他認不出來。
一般而言,點心當中帶“酥”字的,都離不開油酥,比如,叉燒酥、牛肉酥和核桃酥、杏仁酥。它們從名稱上看差不多,呈現方式、觸覺口感則完全異趣。前者,一層一層,蓬鬆;後者,嚴嚴實實,酥鬆。其最大公約數是“松”。
“松”,便是採用油酥的結果。
油酥是由麵粉、食油或者還有水,根據不同的需要按比例調製而成的。
蓬鬆和酥鬆,區別在於是否做了摺疊的動作。摺疊數量越多,層次越趨豐富,自然越蓬鬆。
桃酥不是千層酥,毋需反覆摺疊形成多層酥皮以至於蓬鬆,所以比較敦實;然而,敦實並不代表堅硬,輕咬或輕掰,馬上能感覺它的酥鬆。如果桃酥沒能達到這樣的效果,那是往剛剛摘下的黃桃的方向走了,嗑牙;又彷彿被汽車碾過,它沒事,輪胎倒凹陷了。
很難多人以為桃酥既然沾個“桃”字,當與水蜜桃、黃桃、蟠桃有關。這是誤解。
新鮮桃子的果肉想要在點心裡擔任一個角色,我當推薦它去水果奶油蛋糕上試試。不過,據說那款蛋糕上獼猴桃早就佔了半壁江山,它是否允許既不同目又不同科、再加長得像屁股似的“兄弟”跟自己一起走秀,真的難說。
接下來,桃子只能向葡萄看齊,把自己“瘦身”成“幹”。苦惱的是,幾乎所有烘焙產品都不待見桃肉乾。但,機會總是青睞有準備的“仁”,鹽津系列裡,桃肉的位置就很顯赫。
我們在桃酥上看到星星點點的“果肉”,不是來自桃子,而是西瓜,是西瓜的籽裡的“肉”。
“吃瓜群眾”中的“瓜”,並不是指吃瓜瓤,而是指吃瓜子;那麼,能不能把桃酥叫做“瓜酥”呢?試試,除你之外哪怕還有一個人表示認可,我以為可以考慮為《辭海》立個條目。
都說桃酥與桃無關,那麼,桃酥的“桃”,出自哪兒?
一說,江西景德鎮燒陶瓷的窯工,在燒製陶瓷的同時為了不浪費柴火,把摻了油酥的麵餅一起烤了,結果竟然烤出“冰裂紋”效果,成了可吃的“陶瓷”。因此,說桃酥的前生是“陶酥”,通的。
一說,桃酥上面原本撒滿核桃碎,因為輾轉遷移,落戶於不產核桃的地方,沒轍,只好改成撒芝麻。從此,“掛核桃賣芝麻”跟“掛羊頭賣狗肉”,成為妥妥的一對。舊時規矩大,崇尚從一而終,雖然換了食材,但名稱一仍其舊,堅決不改。
還有一說,認為桃酥是陶工烤制的上面帶核桃仁的酥餅。其嚴謹得把人的想象空間徹底封死,沒小弄堂可穿,令人絕望。
千萬別說“陶酥”沒道理,至少如今景德鎮周邊,樂平桃酥被奉為“桃酥之王”;鷹潭被稱作“桃酥之鄉”;即使大名鼎鼎的“宮廷桃酥”,也是明朝兩個江西籍的首席大學士夏言(貴溪)和嚴嵩(分宜)血腥纏鬥之後,夏氏後裔把宮廷裡的桃酥技術偷出,傳到江西鷹潭一帶,堪稱“肥水不流外省田”的範本。
鷹潭有兩塊響亮的牌子——眼鏡和桃酥。鷹潭人賣眼鏡的真實意圖,或許是想叫顧客看得更清楚一點——“天下桃酥哪家強”?當然“老子天下數第一”!
沙縣有六萬多人在全國各地經營“沙縣小吃”;鷹潭則有十萬人在全國各地經營“宮廷桃酥”,其桃酥產業規模有多大,可想而知。
為此,我曾特地求證於鷹潭朋友,回答是,“實有其事,並非虛飾”。
話說一日中午,我們一行將從井岡山乘動車去南昌,考慮到下午要打卡江西省博物館等網紅景點,時間過於緊張,一本正經組個飯局實在浪費時間,但又不想吃鐵路快餐,便請江西老表家埠兄買些點心來果腹。哪知他居然提來一馬甲袋桃酥!可以想象,不是家埠兄對桃酥一往情深,便是商店裡桃酥“一騎絕塵”。
之前,吃了多少年桃酥,我對它的印象一直不太正面,嫌甜,嫌油,嫌香精,但始終沒能收手;品嚐了井岡山出產的那種黑乎乎又較粗糙的桃酥,倒覺得一股鄉野的自然氣息撲面而來,別有丰姿,頗堪咀嚼玩味。
江西老表能把不起眼的桃酥做到極致,我們不得不由衷欽佩。
桃酥好像是中國的通食,到處有賣。
北京人對桃酥很有感情,老北京周簡段先生在《老滋味》一書中寫道:“提起北京糕點,南味以稻香村和桂香村著名,清真以大順齋為最。可談及正宗的京味糕點,那就要算正明齋了。”他特別拈出該店的“桃酥”等,稱讚“其製作之精細,非一般糕點所及,就連芝麻也要去皮後再用。”
北京最具特色的糕點是“京八件”,那是個系列產品。有個版本說,其中的“大八件”共25個花樣,分為頭行、破皮、酥皮三種。“頭行”是指排在前頭、必須先做的品種,桃酥名列第一,可見其地位之高。
在上海,改革開放前後三四十年,各色點心層出不窮。有興趣盤點的話,能真正沉澱下來、至今還在熱賣的不多,桃酥算是難得的一種,說明有人嗜好那一口,並且是一貫的。
馬齒徒增,胃納變差,一隻像大餅大小的桃酥,我已不太吃得下了,而傾向於五六枚封裝一卷的蔥油小桃酥。現在,我又轉戰那種鑲嵌堅果或莓果或巧克力顆粒的全麥或雜糧小桃酥。推想,崇尚養生之風正健,可能“吾道不孤”吧。
唉,畢竟,形勢比人強啊!(西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