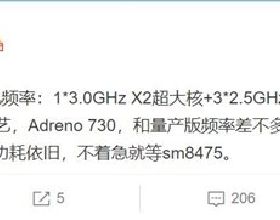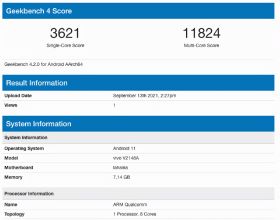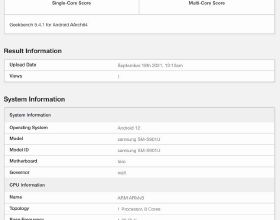1937年10月,正值中日戰爭白熱化之際,日本東京商業區新宿掛出橫幅,上書“中國空軍之勇士閻海文”,櫥窗內陳列著閻海文的飛行服、降落傘、手槍、子彈殼等遺物。參觀的日本民眾絡繹不絕,延續了二十餘日,崇尚武勇的日本人對這位不相識的敵方軍人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那是8月17日上午,淞滬地區水汪汪的稻田映照著萬里晴空。多日陰沉著的天一下子變藍了。這是種田人高興的天氣,也是最忙碌的季節,早稻已經黃了穗,晚稻也該育秧,綠塘裡的菱角鼓脹了肚子急等姑娘們採摘。然而千畝曠野不見人蹤,萬里碧空沒有鳥跡,唯有無數彈花圍著一架霍克飛機四下裡進裂。
只見一條帶狀黑煙從霍克身上冒出,機尾竄起巨大的火柱。接著,一個小黑點從飛機上落下來,轉瞬變成了一隻美麗的大傘,渾圓、潔白、姿態柔和,徐徐飄墜下來。
立刻,田埂上、竹林裡、橋墩後,蜂湧出許多身材短粗的日本兵。他們指天劃地,嘈成一團.不顧長官的呵斥,朝降落傘飄落的方向奔去。
“看中國飛行士!”
“叫他爬著投降!”
……
一邊跑,一邊喊,甩著短的腿。
中國飛行士出現了。他是很年輕的一個小夥子,只有22歲,嘴邊的鬍子還沒有長壯。他不應該是個軍人,彎彎的月牙眼裡黑白分明,透著他的多情,光潔寬展的額頭給人一種書卷之氣。唯有嘴巴稜角分明,不大,緊緊地抿著,一種堅毅和倔強掛在上面。
他的飛行服撕破了,手裡握著一把左輪槍。鬼子朝他喊話,他笑著,眼睛彎彎的,隱蔽在一個墳丘的後面。
“砰!砰!砰!”
三個跑過來的鬼子應聲而倒,粗腿亂蹬亂撓。剩下的臥倒在地,有的跑回去搬援兵。
小夥子把屁股倚在土丘上休息,吹了吹槍口冒出的青煙,整個墳丘像盾牌擋住了他。
今天上午10時,他隨同隊長董明德攜炸彈六枚,與八架霍克三編隊,轟炸上海虹口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敵人的炮火猛烈異常,以至機身在硝煙聲浪中不時震動,他將機身半滾旋轉成倒飛狀態,然後垂直俯衝地面,把攜帶的炸彈向敵人傾瀉下去,全部命中目標。
正在這時。敵軍的高射炮打中了他的座機,機尾冒煙起火,他被迫跳傘。因風向偏了,落於敵軍陣地。
小夥子一邊休息,一邊往槍膛內上滿子彈,然後欣賞著遠遠的那幾個鬼子放空槍。那發出嘶嘯聲音的是劃空飛過的子彈,噗噗的聲音是打在土丘附近泥地裡的子彈。
他想起早上爭任務時他留給隊長的一句話:“讓我飛吧,我是東北人。”
鬼子打了半天,不見他這兒的動靜,以為他被擊中,於是又爬起來,鬼喊鬼叫著向墳丘跑來。
“砰!砰!砰!砰!”
小夥子突起發難,四顆子彈又放倒下四個鬼子。這種槍法,簡直是神槍手。飛行員在戰鬥中最緊要的是把握時機,一舉擊落,否則敵機還過手來,就是自己的性命交關,這要靠射擊準確。現在,小飛將折了翅膀,可是苦心練就的槍法還在。
墳前頭已經躺著橫七豎八的一片屍體,他笑了笑,想起平時大隊的人都說他太奢求,他曾在地靶射擊考核中,獲得過空軍軍校史上第一次百分之百命中的最佳成績,因此一鳴驚人。他仍不滿足,把空中打靶的尺度也定在百分之百以上。
他有一個信條——有奢求的企圖,才能有成功的希望!
鬼子還沒有進入最佳射程。
他瞄了一眼時下的墳,土虛虛的,新拱出的草才寸把高。新墳。他想。墳裡埋著老人?青年?男的?女的?也許,跟自己一樣,是個還沒有結婚的小夥子吧。
“夫人的安慰是怎樣的?”他曾經很認真地問過大隊裡有家室的老大哥。老大哥笑而不答。曾經和他在一起的單身漢,一旦結了婚,也是這樣笑嘻嘻的樣子,好像一下子變了個人。他愈加難以瞭解,也就愈覺得結婚確實是一件神秘而又神聖的事情。
大隊裡有老婆的還不多,大家都住在光棍樓裡,有時大夥談起女人,同屋的“含羞草”總把話題引開。可是夜裡囈語,常是叫著女人的名字。喊醒他,他就漲紅了臉不承認。於是,大夥送這傢伙一個綽號———“含羞草”,那麼大塊頭的含羞草。
小夥子忍不住又笑了笑。
家——這個名稱,怪有味道的。一定很溫暖,那些有家的人,每天完成任務回來.所有休息的時間都消磨在家裡,老大哥雖然笑而不答他的提問,但臉上已經敝了回答,老是掛著甜蜜的微笑,雖然還是老粗,可粗得有了分寸,遇事也細細想,不再那麼魯莽——這是老婆的感化力量嗎?
他又笑了笑,笑彎了眼,像兩牙純淨的新月。
人生,僅僅是旅途的無限延續。偶然在泥濘的路上踏下一個深的痕跡,那就是記憶。
那個記憶是沉重的。在航校,一個同學飛行失事,死了。
祭奠的儀式簡單而莊重。校長獻花圈,一位同學哽聲讀完祭文,樂隊又吹一遍哀樂,全體學生靜默致哀。音樂的節奏,一緩一重振動著每顆跳躍的心,一切便結束了。棺木在緩緩行駛的汽車上,捆著長蛇似的繩子。這黑色器具裡永眠著壯志未酬的勇士……
近了,近了,一排鬼子向他壓來。
“中國空軍的朋友,你現在完全是孤立無援了,趕快丟下武器,我們對你的生命絕對保證安全,我們會像朋友一樣的待你……”
“砰!”
喊話的漢奸抽成一團,咚地栽在那兒了。
“砰!砰!砰!砰!”
又有幾個穿黃皮的踹著粗腿。
現在,槍膛裡還有一顆子彈。敵人又圍了上來,高喊著要活捉中國飛行士。
面前是黃潮一般的敵人,抬頭是祖國的青天.低頭是祖國芬香的田野。
死,那是一切生命的歸程。對於一個常常和死神打交道的人,死,撼動不了他的神經。
死,不是終結,如同秋收並非稻的滅亡一樣。
小夥子把身體蹭滑的墳土用雙手捧上去,細心培好,站了起來,舉起彎彎的雙目,深情地又望了一眼藍天,持起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嘣——
……
下午,在那個新墳旁邊,又堆起一個新墳,木製的墓碑上寫著“中國空軍勇士之墓”。日本士兵列隊脫帽,站在新墓前。
9月1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登出了關於閻海文悲壯殉國的通訊。作者署名:大阪《每日新聞》上海特派員木村毅。木村氏過去是一名知名的文藝工作者。他對閻海文悲壯的殉職,非常感動敬仰,發出“中國已非昔日之中國”的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