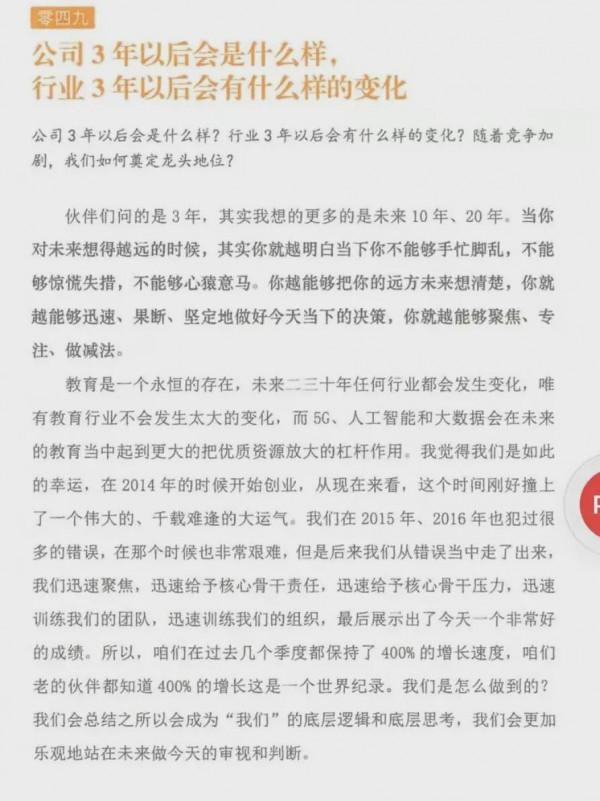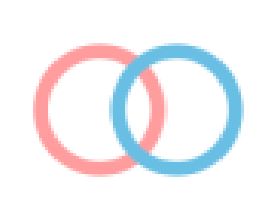這裡的故事都不算新鮮。中國網際網路幾十年發展過程中,風口變幻,高途用很短的時間演示了一家發現藍海,投身而入的公司又如何被迅速拋下。在它的故事裡,可以看到“大佬”的創業情懷,和瑞幸相似的被做空,ofo與摩拜、滴滴與優步“燒錢遊戲”的縮影以及政策突變帶來的釜底抽薪。當然,也少不了一群坐在財富過山車上的人,所經歷的人性的考驗和掙扎。
文 | 徐晴
編輯 | 金湯
運營 | Trixy
陳向東終於“震怒”了。
這是“雙減”巨雷打在線上教育行業後的第四個月。高途仍在災後重建,創始人兼董事長陳向東每天都會關注其他同行正在做什麼,“老大爺一樣碎碎念”。在職員工告訴每日人物,有一次他聽說,公司裡幾位主講老師正帶著高途的學生“出走”,自立門戶,嘗試直播授課。
陳向東動了氣。幾個高管更是較起了勁,他們的解決方案是,蹲守在直播間,一看到這幾位主講老師直播,就立刻舉報。
原本,一位留在高途的員工觀察到,這幾個月,陳向東的狀態已經從忐忑轉向平靜,再變成滿懷希望。他想了諸多舉措應對政策帶來的巨大改變。比如做硬體,但又覺得這是重資產,容易積壓庫存。他也想讓高途直播帶貨,“反正就是不用花太多錢的、有人力就能做的事,他都想嘗試一下”。
最近幾天,已經有幾位主講老師被拉去試水直播帶貨。但陳向東又不想效仿俞敏洪,什麼都賣,他跟員工說,“如果有一天我不做教育了,我就退休了”。
這位高途的絕對控制人開始變得樂觀。近期的一次全員會上,陳向東說“現在是公司最好的時候”,他用一種輕鬆的語氣調侃自己:“我也經歷過股價140多美元的時候”“我也是登上過富豪排行榜的人”……試圖告訴現今留在高途的九千六百多位員工,兩塊多美元的股價和低谷並不可怕,高途有東山再起的可能。
每隔一陣子,高途就會有一次鼓勵為主、講述戰略為輔的會議在不同部門召開。有人看到,陳向東的眼睛裡多了些紅血絲,相較從前,他的頭髮也白了不少。
去年公司被連續做空的時候,他的朋友圈像一個對外傳聲的話筒,熱鬧、激烈。現在,他的朋友圈僅一個月可見,點開只剩一條橫線。但至少,陳向東表現出來的振奮和輕快仍然感染了不少員工,他們也振作起來,試圖忘記頭頂那一片仍未消散的陰霾。
7月24日,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這份被簡稱為“雙減”的意見對教培機構的投融資、業務型別、經營時間都做出了嚴格限制。高途的股票應聲而落,一部分員工被迫離開,大課直播間陸續關停。
這家曾經名為“跟誰學”、後改名“高途”的線上教育公司,是首個抓住線上教育風口的公司之一。它依靠“all in線上直播大班課”而迅速崛起、率先上市,站上了線上教育行業的巔峰。
但很快,藍海變成紅海,更多的公司和金錢滾入行業,靠情懷構築的美好願景被拉回到現實,化為一片巷戰和肉搏。在尚未分出勝負時,紅海變為“死海”,曾經風頭無兩的行業標杆要重新探索未來。
▲ 陳向東演講之後,走下講臺。圖 / 視覺中國
“把命注入”
巨雷在今年8月的一天落下。那一天,陳向東在高途全員會上宣佈,全國十三個地方中心只保留三個。每個中心人數過千,裁員涉及上萬人。緊接著,所有人都停下了工作。大家漫不經心地坐在工位上玩遊戲,辦公室裡響起此起彼伏的“timi”。
一週之前的7月24日,“雙減”落地,辦公室的氣氛開始變得不同:電話銷售的聲音越來越小,從同事工位走過,有人會馬上護住螢幕。零星有幾位員工手足無措又無所事事地等到晚上——加班已經成為肌肉記憶,11點,他們收拾東西離開公司。
阿明是博彥科技大廈的安保。他記得,辦公區沒幾天就沒了人。到了8月底,司機和搬家師傅進入大樓,搬走辦公用品。他們徹夜不休,桌椅被搬上車時“叮叮咣咣”。9月2日早上7點,阿明叫醒了一位睡在一層大廳的司機,告訴他,高途與博彥的租約已經在7個小時前正式到期,搬家到此為止。
9月的一個晚上,前員工林一再一次進入了高途在博彥科技大廈的辦公室,塑膠袋、礦泉水瓶、裸露的電線和一些零散的垃圾散佈在各處,還沒搬走的椅子像超市的手推車一樣堆疊在一起,只有綠色的應急燈陰慘慘地開著。附近安靜得可以聽見蟲鳴。他神色黯然,難以相信高途的寥落。
▲ 高途原辦公區的寥落。圖 / 徐晴
時間像是被7月24日那一天切割成兩塊。在這之前,這裡總是喧囂。
網約車司機不喜歡這裡。從晚上十點或更早開始,進入這個區域的路會堵得像一鍋粥,滿處都是車燈的光亮和喇叭的響聲。這個由博彥科技大廈、東軟北京研發中心、軟體園網際網路創新中心、文思海輝、中關村新興產業聯盟圍成的區域,曾是高途在北京的辦公地,隨著公司的快速發展相繼被租下。
沒人能輕易在這裡打到車,滴滴總是顯示,前面還有兩百多位乘客在排隊等待。幾棟樓下,永遠停留著十幾位外賣騎手。由於外賣數量太多,容易丟失,高途允許美團在大樓門口設立了一整面牆的外賣櫃。
阿明曾經在大廈一層攔下十幾位信用卡推銷員,還曾發現數家裝修公司員工戴著鴨舌帽、懷揣照相機走進大廈一通拍攝。——這兩年,不少中小型線上教育公司會向裝修公司提出“按照高途(跟誰學)的風格來”的要求,迫使他們來學習經驗。
樓裡也是嘈雜的。辦公區裡,輔導老師們戴著降噪耳機給學生講題,沸騰得像高三無人看管的自習室。激昂又整齊劃一的聲音會突然從各個角落裡傳來——會議室或是走廊的過道。
也許是口號。高階教研楊可經常看到“烏泱泱一堆人進入一個大會議室做(關於)自信的鍛鍊,一個個站在桌子上說我是最棒的”,“就像傳銷機構經常做的事”。也許是三次×三下的擊掌聲。在高途,一旦有家長報名了短期班,小組長會帶著輔導老師們“九連拍”來慶祝業績。
只有一些地方是安靜的。比如博彥科技大廈的五層,這裡密集地分佈著十幾個正方形格子間,主講老師在這裡直播。房間門外貼著告示,“禁止在直播間附近喊口號,禁止在直播間走廊開復盤會,謝謝體諒!”但主講老師鏡頭的對面,也許是幾萬人在聽大班課,喧譁在別處。
▲ 高途原辦公區牆上的標語和告示。圖 / 徐晴
主講老師是這家公司的核心,其他的人員,包括輔導老師、教研組和運營人員都要圍繞著他們來。在幾年,風頭最勁的幾家教育培訓機構裡,高途一直以名師和高價精品課程與其他的公司劃分界限。
從2017年年中開始,陳向東就將全部的賭注押在了名師直播大班課上,這是他選擇all in的“最小單元點”,後來成為了這家公司迅速崛起的第一把秘鑰。——2019年上市之前,跟誰學已經達到了連續四個季度的規模化盈利。
盈利帶來了膨脹與擴張,員工這兩年越來越多,林一看著企業微信人數從一萬變成兩萬,然後被隱藏。辦公桌像沒有隔板的大通鋪,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從一臂,逐漸縮短到不超過兩個拳頭,伸手打哈欠的時候,能打到旁邊人的頭。
每隔幾個月,林一就聽說有新的地方中心建成。合肥中心的板塊負責人張淼曾負責英語學科的招聘,“實際上招人的速度是原本設想的三倍”,6個月的時間裡,合肥中心的人數從20變成800,狹小的辦公室變成三層的辦公區。
一座座大廈裡的高途人忙碌又驕傲。甚至,不少人發現自己在離職時還有假沒休完。比如張淼,還剩28天。對此,他毫無怨言,甚至引以為傲。高途提倡“將心注入,全力以赴”,壓力最大的時候,他和員工開玩笑,“將心注入不行了,我們要將命注入”。
“有情懷的教育家”
一個典型的高途員工大概是這樣的,學經歷不算突出,骨子裡有一些自卑,渴望證明自己,當他們遇到公司或是時代提供的機會,會毫不猶豫地抓住,一步步向上爬升。
林一的老家在東北,當地的平均月收入是2000元。他在這家公司做輔導老師,每個月算上獎金可以拿到20000元以上。他的家人一度十分擔憂,多次詢問:“你到底在北京做什麼?”
汪四維在這裡工作僅僅一年半,很快升任部門負責人。離開高途後,他跳槽到網際網路大廠,直接進入管理層。他驚訝地發現,同級別的同事,每一個都比他大十歲或者更多。
高光和柔光曾經一起打在高途人的身上。林一感慨,“趕上一個風口,可能你本身也不怎麼厲害,但是在這個風口上你也飛起來了”。
兩年前的6月,一百餘位員工站在紐交所的大廳裡參加上市敲鐘儀式。時間一到,金屬圓盤在電路控制下發出有規律的響聲,大家一起甩開膀子拍手,在半空中畫出儘可能長的弧線。在整個紐交所227年的歷史上,那一次參加敲鐘儀式的人數排第一。
▲ 跟誰學上市合照。圖 / 陳向東微博
想起那個情景,前聯合創始人王大強(化名)語速加快,音量跟著提高:“可能是很多人的人生巔峰。”回國後,答謝晚宴在國貿大飯店舉辦,幾個聯創跟陳向東坐在一桌,設想未來公司可以達到“千億市值”,王大強開玩笑:“兄弟們努力推一把,把Larry推到中國福布斯前十!”
現在回想起來,王大強覺得這句話“太狂妄了”。不過在2020年10月釋出的胡潤百富榜上,陳向東已經位列第47位,相比過去一年,他的財富增長662%,是上榜企業家中財富漲幅最大的一位。公司也在隨後抵達了頂點,2021年1月,公司股票漲至149.1美元,市值超過380億美元。
做教育當然不只是錢,幾乎每個人都會提到“Larry的教育情懷”。
在內部,他們叫陳向東Larry——創業前,43歲的陳向東決心適應網際網路風格,第一次給自己取了英文名,自此之後,他說話不再用“我”,只自稱Larry,“就像李佳琦稱呼自己是佳琦一樣。”上海的員工芊芊說。
對於這家公司而言,陳向東是絕對的精神領袖,也是絕對的偶像。有人曾在凌晨一點的公司樓下看到Larry離開的背影,為此專門發了一條微博,紀念這個“奇蹟一般的夜晚”。王大強了解Larry,“他不管幾點起、幾點睡,不管連開多久的會,從來沒有見過一次他打瞌睡、打哈欠。睡午覺、打個盹都從來沒有過”。
Larry樂於把激情傳遞給員工,像一個佈道者,反覆描繪教育和努力對一個人命運的改變。
他曾計劃讓所有的輔導老師轉型為“二講老師”,不再只承擔銷售任務,他們也要接受培訓,定期考核,考教師資格證。他也說過要做“本地化”,讓輔導老師瞭解當地的政策和教學情況,為學生提供更適配的服務。
這顯然是一系列偏離商業、成本高昂的設想。楊可跳槽到跟誰學後,發現Larry情懷的一面要大過商業的一面,“我知道他是帶著內心的一些焰火在跟我對話”。直到如今,一位被裁掉的員工仍為Larry辯護:“Larry不是資本家,他是有情懷的教育家!”
如果說直播大班課是跟誰學的第一把秘鑰,那麼情懷就是第二把。Larry的情懷給瘋狂湧入的年輕人們穿上了戰衣。他們在公司大聲喊著口號,私下讀著Larry的《心流》,跟著他去延安、遵義團建。情懷甚至激發出了每個人的隱藏潛能,許多人做出了超出自己責任或者是能力的事。
▲ Larry的《心流》,高途人必備。圖 / 受訪者提供
一位英語學科的輔導老師,為了讓學生感受到高途的服務,把學生沒有買課的數學家庭作業一併給檢查了;高途一開始技術不完善,輔導老師時不時就要應對系統崩潰:可能是老師正講著課,直播卡頓了,或者是學生用華為的平板打不出字,家長用蘋果的手機用不了優惠券……細小的問題都可以由人去解決,比如給用蘋果手機的家長單獨生成一個優惠碼,一個個發過去,再一個個收錢。
沒有人覺得麻煩,也沒人覺得難。
2020年年底,線上教育公司學霸君倒閉,許多學生維權無門。當時,陳向東決定,公司免費給這些學生上課。那一陣子,合肥中心的張淼反覆向員工強調,“我們要向每個學生負責,這是我們做教育的初心”。他沒說的是,公司也要靠這次機會把新客戶收入囊中。有的主講老師一天上三節課,帶不同的年級、不同的班型,輔導老師的工作量也猛增好幾倍。但轉化率還是變成了一個難以相信、極低的數字。
接下來的一期,每個人的壓力都極大,覆盤會開了一場又一場。最後,有幾個主管主動說,“要不我們幾個自己帶頭上?”他們扭頭去做輔導老師的工作。張淼說,有一個主管不太會英語,他說可以負責大家的後勤,每天訂飯。最終,這期課程取得了800%的增長。
▲ 學霸君因資金鍊斷裂倒閉,這一年,線上教育公司風起風落,倒下的亦有不少。圖 / 微博截圖
劉小海覺得,高途這些年能做起來和人有很大關係,“真的是非常拼,你在別的公司根本就找不到這麼拼的人”。巔峰時期,每個人都7×24小時待命。“如果說一個人是這種工作狀態不可怕,團隊100多個人全都是這種工作狀態,那就非常可怕了。所以大家一直說高途是一家洗腦的公司,這個公司文化確實非常牛。我還沒遇到過一家公司是人人都願意這麼玩命工作的。”他說。
王大強說,高途人最常說的口號之一是“努力到無能為力,拼搏到感動自己”。
而且,高途提倡“夥伴文化”,大家資源共享,所有策略、方法、路徑一經驗證可以立刻複製。林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一季度的銷冠站在臺上,把自己耗費時間、精力,好不容易才總結出來的銷售話術,和盤托出。那次他相信,大家並不是對手,而是並肩作戰的“夥伴”。
“你不相信美好嗎?”
只有一處少了一些“夥伴”的情誼。
直播大班課的方式跑通以後,公司內部有兩個部門關注K12(從幼兒園到高三)業務,一個是由阿里中供鐵軍出身的祁秀平帶領的跟誰學好課,包括K12和成人、興趣課程;另一個是搜狐影片銷售中心出身的劉威負責的高途課堂,專做K12。
兩個業務線打法有快有慢,但總體來說高途課堂的營收更為可觀。當時在跟誰學好課部門的劉小海覺得,好課團隊更加關注營利性增長,高途課堂更加關注“生命週期價值”,考慮“長線盈利”。
儘管兩邊都受重視,但公司給予的資源是完全不同的。劉小海直觀的感受是,“一個是親兒子,一個是乾兒子”。親兒子是高途課堂,無限投入的人力和財力讓它成長為一個巨人,儘管營養不良,始終在“戰略性虧損”,但它的龐大體量決定了它在公司裡的地位。相比高途課堂,好課投入的資源不多,體量增長速度也慢,但卻一直在盈利。
“高途課堂和好課的兩撥人互相不服。好課的人覺得高途課堂是資源喂大的;高途課堂的人覺得你量這麼小,你跟我說話幹嘛?”更重要的是,晉升的速度也顯著不同,“在好課肯定比不上高途課堂,一些管理層實力相差不大,但有的升到了經理,有的還是主管。”劉小海說。
這也證明了當時的跟誰學,陷入了一場以量取勝的比拼。如今看來,這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與真正的教育普惠情懷背離,情懷只關乎公司。
當公司有負面資訊的時候,無論什麼部門,高途人對公司的信任不會減弱分毫。
2020年2月25日,第一簇閃電劃破了天空。做空機構灰熊釋出報告,指出這家公司的七個經營實體在2018年誇大了74.6%的淨利潤;跟誰學曾要求入駐的教育機構用虛假賬號刷單,平臺流量和學生人數嚴重造假;除此之外,還有關於鄭州三座大樓的價格爭議,以及大股東和核心員工頻繁套現等等。
這之後,從4月開始,針對跟誰學的做空報告如同網路上的連載帖。之後的12個月裡,跟誰學被多家機構做空15次。
確實有一些隱而不宣的問題。比如天蠍在2020年5月釋出的做空報告中指出,有員工在入職諮詢群中表示,主講老師入職之前不必有教師資格證——這與公開資料相悖;另一位在跟誰學官方介紹中的高階漢語教師李格,她所公示的教師資格證編號顯示,所有者是李盼盼,任教學科是音樂。
屢遭做空以及實錘漏洞引來了股價的幾次震盪和雪球使用者的嘲諷。他們稱陳向東為“拉總”,說“拉總的愛好和特長是拉股價”。每逢有負面新聞釋出,就會有人在評論區反諷:“你不相信美好嗎?”——這是因為陳向東曾發了一條朋友圈,說“因為信任,所以簡單;因為相信,所以美好。您相信了嗎?”
▲ 陳向東朋友圈截圖。圖 / 受訪者提供
關於做空,陳向東的回應多是關於他的初心、情懷、理想、格局。比如,有人質疑跟誰學刷單,他解釋,跟誰學是一家把誠信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公司。再比如,陳向東去年12月接受《晚點LatePost》採訪,被問到被做空14次是一種怎樣的體驗時,他回答,天大的運氣,這創造了世界歷史。
作為精神領袖,陳向東的態度直接影響員工的心態。張淼在休息日到北京總部加班,看到陳向東和高管一起開會。前一天晚上,灰熊的做空報告剛上新聞頭條,眼前的這些人卻有說有笑。他一下子放心了。回到合肥,做空報告已經有了6個版本,新入職的員工問,怎麼回事?張淼說,習慣了。
整個公司的情況是,外界越做空,每個人越放鬆。大家看著股票在震盪中上揚,從40、50、60美元漲到100、120、130、149美元。一句公司內部廣為流傳的玩笑是,“你不要擔心有人做空,你要擔心的是你的工資買不起公司的股票”。
那陣子,公司拿著手機計算器算數的人多了起來。休息時間一到,會聽到北京的員工們討論在哪個區買房,他們計劃在期權兌現後果斷上車,在房價動輒數百萬的城市裡安家落戶。
未來一片光明。只是直到此時,閃電後的驚雷還沒有真正落下。
“資深教師”
每個高途人都記得一位“老奶奶”。
去年,一個語氣權威、短髮泛白的“資深教師”,突然出現在4家線上教育的資訊流廣告裡。她的身份一直變化,“40年英語老師”“一輩子小學數學老師”“專家”……廣告上方或下方,logo也在變,高途課堂、作業幫、猿輔導、清北網校輪番登場。
顯然,這是一位廣告演員。在她的背後,正在進行一場線上教育的燒錢大戰。
▲ 四家線上教育用同一“老奶奶”。圖 / 抖音截圖
從2019年開始,K12+直播大班課是一門好生意,成為行業共識。線下元老學而思、新東方,後起之秀猿輔導,還有位元組家的新人“大力課堂”都在當年全力投入。毫無疑問,這個過熱的行業,一條跑道已經擠不下了,他們最起碼需要兩條公交道。
等到2020年,2億學生轉到線上,這一年教培行業一共發生了111起融資事件,金額超過500億元。投資者名單裡都是最頂級的機構。
資本帶來了更廣闊的市場,也帶來了新的打法。
縱觀網際網路發展史,每一個風口上都伴隨著一場燒錢大戰。有的錢“燒”出了基礎設施,比如電商的物流和外賣的規模;有的錢直接“燒”成了使用者補貼,培養出使用者習慣。但線上教育這一次,錢直接“燒”在了營銷,讓廣告商、節目製作方、平臺賺得盆滿缽滿。
把錢“燒”在營銷上也並不少見,前有凡客燒錢砸線下廣告,後有瑞幸請來湯唯、張震讓小藍杯深入人心。在藍海里燒錢是為了培育市場,在紅海里燒錢是倚賴資本的力量撬動市場份額。
為了市場份額,線上教育的戰場選在了2020年暑期。暑假之前,猿輔導、學而思、作業幫、跟誰學的營銷推廣預算,分別達到了15億、12億、10億、8億。
在過去,跟誰學曾是戰役的旁觀者,這家公司的起勢一方面是因為專注三四線市場,另一方面對微信流量的運用嫻熟,這讓跟誰學在前端的獲客成本很低,不必燒錢。
也正是因此,2020年年中接受《人物》採訪時,陳向東覺得教育不該靠營銷。“歷史上拼命砸廣告做營銷的教育公司,後來都退出了歷史舞臺。”他說。
但在2020年的一個全員會上,陳向東宣佈“轉型去做規模性增長”。劉小海回憶,上市前和上市後公司是兩種狀態。上市之前跟誰學追求盈利性增長,上市之後要追求在資本市場的估值,大面積的廣告也在上市之後的2019年第四季度開始投放,“公司開始對標競品了”。當時,劉小海負責品牌投放,每天一睜眼就發愁要怎麼把上千萬的預算花出去。
陳向東不是一個盲從的人,他有自己的堅持。但當他站在山頂,對手們一個個滑下,同行者們的裝備已經除錯完畢,每個部件都已經潤滑到整裝待發,他沒有喊停的權力,只能跟從。
林一在跟誰學辦公樓的電梯裡看到了猿輔導的廣告。他拍了照片發給同事,同事見怪不怪地笑了笑。陳向東接受《人物》採訪時說,跟誰學和競爭對手在同一輛公交車上貼廣告,跟誰學在門的正面,對手就在背面。
員工把投放廣告當作一種實力的證明。林一記得,去年秋天,負責高途課堂的CEO劉威在公司群裡發了訊息,“我們在公交站牌都已經投了廣告了”。底下接連彈出幾十條微信訊息,大家刷屏回覆,“相信高途!”
▲ 高途課堂、學而思在公交站“燒錢”。圖 / 視覺中國
但真實的情況是,巨大的營銷帶來了巨大的虧損,“燒”走的是自家的盈利和公司的市值。終於,在保持連續8個季度的盈利後,2020年第三季度,跟誰學虧損達9.33億元,同時,使用者面臨負增長。
可這個戰場,只要踏進就很難退出。
戰爭還在繼續,其中最強有力的燒錢工具是短影片平臺。9月初,猿輔導日均投放927萬元,跟誰學達到434萬。到10月中旬,這兩個數字變成1397萬和713萬。資訊流廣告採用競價機制,戰爭最熱的時候,一個有效獲客線索從幾十、幾百變成了1300塊——這個價格來自跟誰學。
情懷包裹著的教育平等是一個美好的概念,但掉入競爭的現實,燒錢營銷成了跟誰學的第三把秘鑰——和任何一個線上教育公司,或者說任何一個風口上的公司沒有兩樣。
負責高途課堂的劉威在此時拍了桌子。他叫來了汪四維和另外幾個負責人,說自己感到“痛心”,同時又覺得“可怕”。他留下任務,一天之內,獲客成本要降到700塊。那個會從前一天晚上開到凌晨,負責人們沒有回家。
可獲客成本剛降下沒多久,當年10月22日,陳向東在一次內部全員會上宣佈,高途課堂和跟誰學好課的K12專案將要合併,最主要的原因是營銷費用花得太多。前高途師訓部門負責人宋新記得他語氣嚴厲,說“我們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合併的決定下來之後直到今年官宣,有人覺得那是劉威最絕望的時候。
在高途,劉威像一個“真正的CEO”,他永遠保持著一種嚴肅和精益求精的態度,不像陳向東看起來親切、和善。但實際上,作為一個從主管成長起來的職業經理人,劉威無條件聽從陳向東的號令。相比舵手,他需要做的是讓這艘大船上的每個零件都正常、持續地執行。
在汪四維看來,劉威是“一下子把問題戳破”的人。“他甚至不在乎這個人是誰,他就事論事,也不會給人面子。”
他覺得,劉威“可能會造成內部一些高層的不滿意”。汪四維甚至隱隱感到,劉威與Larry之間“會有一些沒有那麼和諧”。在他看來,劉威在經營公司、孵化人才、搭建公司體系上能力強悍,但這種強悍有時會跟Larry的情懷相牴觸。在公司,大家普遍認為“劉威代表了商業的那一面,是實幹家,Larry代表了情懷的那一面,是精神領袖”。
此時,“精神領袖”痛心疾首。但對外,他保持著一貫的掌控感。年中一次演講,陳向東提到:“那些競爭使得我們做出的決策,往往都會是錯誤的決策。”12月接受《晚點LatePost》採訪時,陳向東說:“我到今天也不覺得燒錢做生意是正常的。但市場被重構,資本大量進入,我的想法發生了變化……在戰略投入期的時候我們可以忍受虧損。”
只是這時候,線上教育的風口已經雷雲密佈。
▲ 陳向東。圖 / 視覺中國
“和你共進退”
惶恐和不安開始籠罩這家公司,這個行業。
今年1月,“老奶奶”事件招來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的發文批評,跟誰學下架了廣告和低價引流課程。
4月,教育部印發《關於大力推進幼兒園與小學科學銜接的指導意見》,禁止校外培訓機構對學前兒童違規進行培訓。5月末,陳向東關停了公司的資訊流業務,裁員20%,同時關閉針對學前兒童的小早啟蒙業務。
再往後,陳向東表示“不動中臺了”。HR小魚鬆了一口氣,但7月底,“雙減”落下,所有人都被高速列車的強大慣性摔在了地上。
陳向東哽咽了。
“雙減”之後的全員會上,他的語速放慢了。宣佈裁員後,所有人都收到了一封來自陳向東的內部信,3個排比句重複出現了5次:非常非常抱歉,我們不得不做出如此艱難的決策。非常非常難過,我們的不少小夥伴將不得不離開。非常非常傷心,我們必須割捨那麼多不得不割捨的情感……
▲ 高途內部信。圖 / 脈脈截圖
在眾多員工眼中,Larry的信情真意切。他們再一次受到感召,在被裁掉後,把“感激Larry,感激高途”設定為內部溝通軟體“靈犀”上最後的簽名。
辦公室的人開始變得稀稀拉拉,HR小魚在走出辦公室時回望,同事們的名牌還擺在桌子上,由於太過密集、工整,遠遠看過去,她甚至覺得像是一個個紀念他們曾經存在過的墓碑。
林一這些輔導老師,對高途的情緒很複雜,其中最多的是惋惜。陳向東過去的願景,不管是“二講”還是本地化,都還沒有落地。在以規模性增長為目標的背景下,業績排在了第一位。
在續班期,輔導老師如果沒有達到業績,就算已經報名教資考試也不允許請假參加;向家長推課的時間,輔導老師只能打電話,不能給學生答疑。為了完成KPI,輔導老師向家長承諾有提分、放解題“大招”,甚至道德綁架,常用話術是“別讓你的猶豫耽誤孩子進步”。
即便是在“雙減”落下的前後,夜裡依然有輔導老師留在公司給學生講題,他們也在調整話術,反覆詢問家長續課的意向——就像不知道將軍的命令已下,還想再衝一把計程車兵。一位家長當時接到電話,問對方“不是雙減了嘛”,輔導老師嘆了口氣,掛了電話。
在輔導老師身上,可以看到情懷與商業的博弈。當情懷佔上風時,輔導老師更像一位老師;當商業更被看重,輔導老師就成為銷售。
亦有人對高途失望。
在“老奶奶”被點名批評之後。公司宣佈整改,規範廣告,減少資訊流投放。但曾經負責師訓的宋新發現,廣告還在。內部有一個專門的廣告詞違禁庫,成績、考試相關的詞彙都不能出現,相關部門會換著方法修改表述,比如把“提分”改成“怒漲300詞”。“還是在鑽政策的空子”,他認為公司並沒有真正反思。
大愚基金經理、雪球上的認證使用者“倉又加錯”劉成崗認為,“國內線上教育公司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沒有一家公司是利用了網際網路,利用了科技,讓教育變得跟以前不一樣了。網際網路跟科技只是用來作為獲客的工具。”這些公司包括高途。在他看來,“Larry是隨著時勢去走的,他在這個行業裡面沒有做出顛覆性的東西。”最重要的是,“他為什麼一面講情懷,一面又把課程價格定得那麼高,收割的還是下沉市場的使用者?”
▲ 高途公交站廣告。圖 / 視覺中國
“是夥伴是夥伴”
8月下旬,CEO劉威“因為個人原因”離職。後來的員工大會上,陳向東說:“出乎我的意外(料)。”他說自己原本以為大家是依靠做教育的情懷走到一起。“他覺得自己看錯了人。”劉小海說。
此時,陳向東也放棄了all in,甚至轉向變成了in all。
“雙減”之後,陳向東在高途Q2季報釋出後的電話會議上表示,高途將加大投入已有的成人教育業務板塊,比如財經、公職,同時拓展新的成人業務板塊,例如考研和出國留學,並開始探索智慧數字產品和職業教育。
如今,為了直播帶貨,MCN緊鑼密鼓地做起來了,成人業務的素養課和程式設計課也有了眉目。由於之前裁員裁得太徹底,高途甚至有些缺人,不少部門正在重新招聘,或是讓被裁的員工迴流。——但顯然,如今還看不到這家公司盈利的第二曲線。
現在的高途在北京只有一處辦公地,文思海輝大廈的南邊五層、北邊兩層。最近,一位仍在職的員工發現陳向東已經很久沒有出現在成人業務在的那層辦公區了,反而是中小學部的員工看見過他許多次。他認為,這是因為成人業務逐漸穩定下來,Larry更多要去操心變化更大的業務。
11月,在“營轉非”的壓力下,學而思和新東方宣佈正式關閉K9業務。高途也緊跟著宣佈,將停止K9業務——這是按照規定,每一個線上教育公司該做的事。
但對於陳向東而言,K9仍然要做的。他準備成立一個公司,在符合“營轉非”政策要求的情況下申請牌照——在北京,35人以上的大班課每小時價格不能超過政府指導價,有人估算是50元——繼續做K9的業務。陳向東相信,只要大班課人數夠多,50元“這個價格一定是賺錢的”。
仔細分析過政策之後,陳向東甚至更加樂觀了,跟主講們單獨開會的時候說這是“好事”,“巴不得這樣”。他相信有了辦許可證的要求,許多機構會退出市場,這意味著競爭對手變少,燒錢營銷也不存在了。他覺得現在的情況恢復到了2018、2019年的樣態,可以“迴歸教育的本質”。他的目標是,讓高途的股價恢復到30美元,是2018年上坡時候的30美元,不是今年跌下來的30美元。
陳向東還是當年那個大佬,只是一年融資5000萬美元重新整理紀錄的風頭過了,參與制造的線上教育風口也過了。在各個會上,他評價那些曾經的同行者、線上教育前“大佬”們的努力,“哎呀,怎麼能這麼搞呢?”“啊,早知道我們也這麼做了。”他說,自己不會放棄教育,除非退休。
▲ 新東方董事長俞敏洪直播賣瓜助農。圖 / 抖音截圖
做教育是陳向東的夢想與堅持。就像他在農村長大,夢想在北京買大房子,再建一個游泳池。隨著財富增長,他的夢想早已實現,但游泳池總是空著,陳向東的媽媽看不過去,說要填上種菜,他不同意。夢想總要實現的,但不一定一切都可以匹配,就像如今,游泳池沒有種菜,荒在那裡,陳向東至今也沒有學會游泳。
離開高途時,汪四維反思了很久,他覺得公司發展太快了,有些“老人”掌握著很大的話語權,但實際上已經駕馭不了那個位置。“當一個公司從幾個人到兩萬人,肯定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他說。
有人感受到了變化。在2020年下半年,不少人已然懈怠,但增長可以掩蓋很多問題。在全面滑落的當下,有些人呈現出了與以往不同的樣子。“現在的高途,就是‘冰火兩重天’。”走進辦公區,可以一眼看出兩種人和兩種工作狀態。有人經歷了大起大落,極度悲觀,每天在公司裡無所事事,一位仍在職的員工覺得,“他們唯一還沒離開高途的原因是出去不好找工作,在這裡等著,說不定能等來N+1。另一批人還保持著在2017、2018年的那種工作激情”。
這位員工目前負責成人業務,今年的工資只是去年的一半,福利都被取消。他覺得自己在這家公司“經歷了K12從單月一百萬營收到兩個億的過程,現在正在經歷成人業務從單月營收兩三百萬到一個億的過程”。“第一次做起來可能是趕上了,如果第二次能做起來,那就是實力”。就像這家公司一樣,他憋著一股勁兒,想要證明曾經走上巔峰的原因是實力而不是運氣。
在放棄燒錢營銷之後,高途正在重新做非標準化投放,一些只有一部分人能看到的廣告,比如私域流量。還有一小撮人,如今被派去做最原始的投放——到各大學校門口發傳單。
沒人再談論股價了,“都是傷心事,被套的同事太多了”,有人買了40萬的股票,現在只剩下3萬,他原本想買房,現在房子直接沒了。
一個時代終於在迷茫中潦草地結束了。
回望前兩年,線上教育的所有人都沉浸在興奮中,如今,影響超出了一個行業。高途、新東方、好未來股價狂跌時,中概股跟著一起跌。一位高途主講老師手握公司期權,他的愛人攥著騰訊股票。“雙減”那一天,一家人跌沒了上百萬。如今,高途的股價還在2美元左右徘徊,大盤的漲落在它身上,也不過是幾十美分的變化而已。
迷茫的還有那些被裁掉的夥伴。他們的人生曾經被拋上高點,如今要繼續適應高點之下的生活。小魚曾以為找到新工作很容易,可在她休息的幾個月裡,新東方裁員4萬,學而思線下155個教學點只剩下53個,位元組教育開啟了本年度第二輪大裁員,據媒體報道稱,在12月將有近2000人被裁,其中有超過 1000 人來自瓜瓜龍、清北網校,精銳教育、學霸君暴雷……線上教育賽道里湧起的巨浪讓數萬人才流回了市場。直到現在,小魚還沒有找到新工作。
但高途的烙印還在,他們的生活曾經被真切地改變著。張淼離職之後跟曾經的兄弟們吃了頓飯,他們難免聊起過往,被一個人緊急制止,“如果聊這件事情,我們今天晚上誰都回不了家”。社交平臺上,一個女孩在某個帖子下留言,講述自己的經歷,提到“以前都是將命注入的”,有人立刻回覆她“是夥伴嗎?”她答,“是夥伴是夥伴”。就像茫茫曠野上兩頭相遇的小獸,他們依靠氣味和暗號識別出了彼此共同的身份。
林一徹底換了個賽道。即便如此,在9月面試時HR還是不經意間提起,最近來面試的人,十個裡有八個是高途員工。他的新工作,薪水折半,但工作量超出想象得低,“一週的事情也就相當於高途一天的工作”。
一個工作日的下午6點,林一走出公司。在高途的幾百個日夜,他沒有看過一次夕陽,他曾跟同事開玩笑,“我們是星光下的趕路人”。
站在高途已經貼上封條的樓門口,林一看著北京的西邊,太陽一點點沉下去,晚霞燒紅了半邊天,林一說,“離開高途之後我才知道,原來太陽是會落山的”。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實習生鄒雨沁、周鑫雨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章為每日人物原創,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