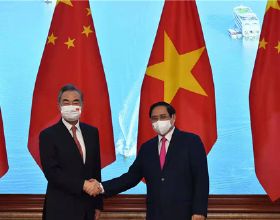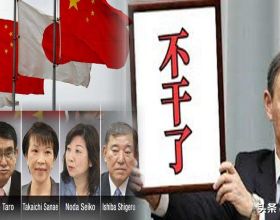獲悉外公去世的訊息,並沒有想象的那麼晴天霹靂。也許是在這之前,他已經數月纏綿病相了。在家鄉,家裡的老人過世了,常常會說老了人,喪事也常常會稱為喜喪。而這,是不是說,死亡本身也本非如此悲悽?
送葬的那天,我們從外公家出發,隨著抬靈柩的隊伍繞著小鎮的街道走一圈,遇到擺路祭的人家點燃炮竹,舅舅就抱著外公的遺像向那人還禮,布禮的人遞上毛巾裹起東西以示感謝,隨後隊伍繼續前行。外公的老家在江對岸,祖墳亦是如此,包船的事宜提前就預訂好了。
乘船過江,江風刺骨,那時候,我穿著一雙不合腳的薄皮鞋,走過泥濘曲折的路,腿早已凍疼得沒有知覺了,後來母親體貼,同我換了鞋,可刺骨的疼痛並沒有得到緩解。母親是個堅強的女人,自外公去世以後,她一直很傷心,即便如此,她也不甚表露,彷彿忙碌地操持各項事務就能讓她片刻忘記失去父親的痛苦。換上我的鞋之後,她又不知跑到哪裡去處理事情了,好在還有父親從旁周全著。
下船後,又是一段長長的泥濘路。葬禮的儀式要求半路上我們也要跪在靈前哭喪,但在這樣老舊的路面上,幾乎找不到合適跪拜的地方,大家一路還要負重前行,所以能免的就免了。到祖墳山的時候,地上、樹上已經積了厚厚的雪。我們撐著傘站在這荒無人煙的天地間,積雪沒多久便把重量傾覆在傘上,大家不得不收起傘,抖落積雪,再撐開。我撐傘的手在寒風中凍得通紅,身體也禁不住瑟瑟發抖。幾位稱之為“八仙”的抬靈者,提著鋥亮的鐵鍬,開挖墓地。我們站在風雪中等待著,有時候凍得實在不行了,蹲下身子,幾個人撐著傘圍縮在一起。偶爾說話的時候,空氣中呵著白氣,一股冷流立即順著張開的嘴巴沒入到胸口,撕裂般地疼痛。
那些壯實的漢子,身上的絨衣差不多都解了,只留下一件單衣,仍是汗流浹背,不時地用已經半髒的毛巾揩著汗,吐幾口唾沫後,一起加緊使力。在他們的幫助下,一個漫過人高的深坑很快就挖好了。新挖的墓坑很溼潤,裡面鋪了些乾草。由於下雪的原因,帶過來的乾草也都有些潮溼了,焚燒的時候白色的濃煙直冒,待乾草燒盡相對乾燥時,再在裡面鋪上一層厚厚的石灰。
天氣實在是太冷了,雪似乎越下越大了,等候的人實在吃不消,所以開坑完畢後,儀式加緊開始了,掛名的道士口裡帶著特有的腔調吟唱著似往生咒之類的道語。即使是本地方言,大家也著實聽不懂。“八仙”合力將棺木抬進墓中,隨後,開始向跪著的披著麻巾的人群扔土,聽母親說這寓意著“財”,多少要接點。由於天氣的原因,泥土變得又溼又硬,他們稍稍用些力氣,打在人身上就特別疼,舅舅提前同他們打了招呼,不必太過於拘泥,心意到了即可。
接了土之後,大家需從棺上走過,撒下泥土。人走在打溼的棺木上易滑倒,顧慮到這個問題,母親讓大家直接將泥土撒在了坑裡。鑼鼓聲響起,開始合墳,道士唸了幾段後,土堆也跟著高高隆起了。一場熊熊火,燃盡那些仙鶴、房子、冥鏹······火光映紅了臉,煙氣隨著風雪升至天空。
送葬完畢,坐船歸來後,已經是中午了。大家都到約定的地方開席。待到宴席結束的時候,阿姨讓我們提前回去的孩子給外婆帶飯,我才恍然她原來不在這裡。我到舅舅家,眼中看到的是一個飢寒交迫的老人,看著讓人心疼。此時的菜已經微涼了,她緩慢地挪動身子,開啟煤氣灶,抄起鍋鏟把菜飯熱一熱,然後,一個人坐在餐桌上默默地吃。這是我看見過的最孤獨的午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