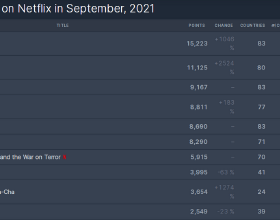在乾淨的院子裡讀你的詩歌。這人間情事
恍惚如突然飛過的麻雀兒
而光陰皎潔。我不適宜肝腸寸斷
如果給你寄一本書,我不會寄給你詩歌
我要給你一本關於植物,關於莊稼的
告訴你稻子和稗子的區別
告訴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膽的
——餘秀華《我愛你》(節選)
1
龐麥郎和餘秀華18杆子也打不著,為這兩位找一個共同點,只能是:“文化”,或再加三個字:“文化從業者”。前者是唱作人,後者是詩人,都可歸入“文化從業者”。既為文化從業者,其作品又是給一般老百姓看——我在內的一般人會忍不住給他們打個分,而其實:之後所有的討論,是以這個分數為基礎的。
比如龐麥郎之“草根上位”、“自不量力”,乃至現在混得亂七八糟,眼看要湮滅下去……對他所從事音樂事業的打分是普遍不高的。很多人在心底不覺得他是個“人物”,甚至看他不上,看他不起。餘秀華的得分高得多了:有《詩刊》的大力推薦、“中國的迪金森”、讀者的高度關注和肯定……總體看來:很多人在談龐麥郎時的預設視角是“俯視”,且憐之且輕蔑之,對他的所謂“欣賞”帶有直接的自我安慰,像魯鎮那些八婆“欣賞”祥林嫂一樣;談餘秀華是“仰視”,且哀之且歎服之,對她的境遇(現在還好,之前很苦)還能抒發一番自己的真情義、好心腸,算是間接地安慰自己。
這背後非常硬的依據是:他們各自的業績,或公眾、媒體對其業績的打分。——無可厚非,人之常情而已。談論一個人,免不了要談論他的“意義”,尤其談公眾人物。那“意義”是由什麼構成的呢?
2
第一當然是業績,上文說了。那這個業績究竟是怎麼評出來的?人是感情動物,只是具備些理性精神。不得不說,很多業績和意義是我們不憑空——但想象出來的。龐麥郎也好、餘秀華也好,歌唱水平、文學水平究竟怎樣?首先很難評估:藝術和文學,不能清楚地給一個高下。其次,很多人根本就沒親自評估,媒體稱讚則跟著媒體講好話,學者批評則跟著學者扮深刻,唱得好怎麼個好法,寫得好是為什麼好,這些在“走紅”或“隕落”面前變得不重要。
但這些,恰恰是真正評價一個人的業績和意義的直接依據。
理性確實起些作用,因為即便深究起來:媒體、專家的說法和大眾的跟從並非沒有道理,得確實是“好”才能從寂寂的民間移入嘵嘵的輿論場。當全社會幾乎動員起來配合一個人躥紅時,這個人的確是有本事的,比如餘秀華。相比之下,配合龐麥郎走紅的勢力小太多了,認真去看他怎麼隕落的也不多,他幾斤幾兩就很清楚。但感性起了更大的作用,甚至大得多的作用,它總能成功異化我們基於理性的判斷。如果餘秀華不是腦癱,對她業績的評價會和現在不一樣。何以至此?
根本上,作品是作品加作者形成的:二者有確實但不確切的互文關係。作品究竟怎麼樣,究竟我們在評價它的高下時能使用多大程度的理性,有賴作者本人附加上去多少東西。如果時間隔得足夠久,作者的經歷被沖淡了,我們可以較理性地評判作品。比如我們今天讀愛倫•坡、熱內、海明威,甚至多多、顧城,會不太在意他們本人的問題,淡化“這是個什麼樣的人寫出來的東西”的意識,而更專注作品本身。
龐麥郎、餘秀華之所以不能被這麼冷靜地談論,在於他們仍然是很大程度上的新聞物件,不是純粹的研究物件或閱讀物件。她們的作品附著上太多作者的東西,以致我們聽歌、讀詩是在幾乎純然地聆聽歌者、閱讀作者。換言之,現在不是談論作品的時候,因為作者被嚴重談論了。那些嚴肅的批評家完全不用為藝術本身焦慮,不用惆悵民眾何其不知好歹。時間會把作者削弱下去,他們都最終退向作品背後,由新聞物件而成研究物件。天道公平是大公平,不拘一城一池的偏見存在。
3
小結上文:意義首先由業績構建,沒什麼可爭。業績又同時被理性、感性評估。二者此消彼長,只有在大時間、大世界框架內,才有最終的和諧。當然,理性並不是“正確”,它只是對待問題的一種方式。之所以比較信賴它處理出的結果,也是相對感性而言。
我們繼續:構成意義的第二種東西是業績和時代的均衡狀態,這種均衡產生道德考量。問一個人有多大的意義,必須看放在什麼時代背景下在問。比如偃武修文的治世,文人雅客、絲竹管絃的意義就更大;而鶴怨猿啼、戎馬劻勷,時代大戲的主角就只能出將入相。我有時想:象棋是純粹的戰爭遊戲,但如果增加幾顆棋子,比如“伶官”,規定:開局的時候替“相”用,結局之前替“卒”,則戰爭遊戲會變成政治遊戲,繼而整部國史的縮影。
我們能夠在今天熱熱鬧鬧地談論龐麥郎、餘秀華或別的文化從業者,正是中國人平均地身處棋局伊始,把“伶官”當成丞相——“國之重器”——在用。敵國們鬧事試試?壞人們鼓唇試試?或再幹掉兩打“查理”,再失蹤八架飛機?這些文化從業者的意義便沒這麼大了吧。國之將興,文化開府,這還好理解——值得思考的是:國之殃禍,文化也興。而其實:就像我設想的那盤棋——到最後,伶官可以當卒子用。卒子也是相當能拱的。
4
意義一定是由人談論的,人皆是時代中人。如果時代不參與進去,實在說不通。我能想到的構成“意義”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一個人本身的貢獻和他的貢獻被放在哪種時代之下。那什麼是“意義”的意義呢?第一層,即談論某一“意義”的必要,亦即究竟此人、此事值不值得被談論。第二層,即我們以上分析的:意義的構成。此人、此事既然被認為值得談論,如何談論呢?看看他做得怎麼樣,是在及是在什麼情況下做的。
根本上,還是在於人本身的侷限。上文說了,人是天生的感情動物,合為大眾——更只是向本賦討到幾分理性。當我在使用感情而你進入理智模式,或我冷靜看問題而你渾身打雞血,誰看誰都看不過去。所謂人本身的侷限,除了一人之內感性與理性的犬牙交錯,還在人與人之間這兩種狀態無法對應——而且時常是擰著的。記者這一職業在當今的巨大困境可能是:職業理性發展緩慢,人的理性無力發揮,人的情感被隨時綁架、裹挾。
囉嗦這麼多,無非一同複習下:人可能是怎麼回事。
原稿寫於2015年1月18日星期日,@諾丁漢Raleigh Park
改定於2021年12月17日星期五,@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