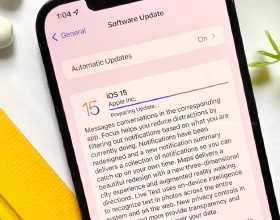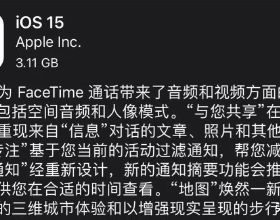宮崎駿《千與千尋》,電影,2001年

時隔數年,人們的視野從極簡主義再次轉向極繁主義(Maximalism)。這種繁雜、華麗甚至具有戲劇感的設計煥發出強悍的生命力,並再次風靡藝術界。極繁主義如何跨界時尚?又與極簡主義有何關係?今天,時尚芭莎藝術帶你瞭解。
溯源極繁
動畫世界便常出現極繁主義的場景。從宮崎駿執導的《哈爾的移動城堡》《千與千尋》,到今敏創作的《紅辣椒》,無不以繁多的裝飾風格創造出一個異想的世界。濃烈豔麗的紋理與物品將影片畫面每一處空隙填滿,令觀者挪不開眼,不自覺地步入情境間。
宮崎駿《哈爾的移動城堡》,電影,2004年
今敏《紅辣椒》,電影,2006年
這便是極繁主義。它包含著“過度”的意味,但卻是精心策劃的風格混合;它提倡重複、圖案和大膽飽和的調色盤,又兼有種種獨一無二的元素。事實上,極繁主義正以一種過剩和冗餘的美學持續地奪人眼球。
在藝術界,批評家羅伯特·威滕(Robert Pincus-Witten)便曾以“極繁主義”來描述朱利安·施納貝爾、大衛·薩利等在新表現主義初期活躍的藝術家。尤其朱利安·施納貝爾獨創的“盤子畫”,即利用碎瓷片貼上在木板上作畫,使畫面凹凸不平,再施以厚重粗野的顏料,所見之處皆濃墨重彩,密集的情緒狀態撲面而來。

朱利安·施納貝爾(Julian Schnabel)《Pandora "Jacqueline as an Etruscan"》,木板油畫,182.9×152.4×20.2cm,1986年

朱利安·施納貝爾(Julian Schnabel)《Number 1 "Van Gogh, Self Portrait with Bandaged Ear, Willem"》,木板油畫,2018年

大衛·薩利(David Salle)《Mingus in Mexico》,布面丙烯、油畫,241.5×311cm,2019年
如若追根溯源,極繁主義在藝術界並非“誕生”,而是“迴歸”。這種風格在巴洛克(Baroque)和洛可可(Rococo)時期便有跡可循。17、18世紀的法國與義大利一反文藝復興時期嚴肅均衡的藝術風格,將“俗麗凌亂”之風帶入藝術領域;而後的洛可可時代更是熱衷於無序與不對稱。此時,人們開始在藝術品中體會到差異感,從而引申出情感表達,使之成為承載思想的媒介。

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對無辜者的屠殺》(The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198.5×302.2cm,木板油畫,1638年

讓·奧諾雷·弗拉戈納爾(Jean-Honoré Fragonard)《鞦韆》(The Swing),布面油畫,81×64.2cm,1767年
再者,在幾乎同時期的藝術界,室內肖像畫成風。畫家如人肉相機般記錄下歐洲歷史黃金時代的博物館、畫廊或精英階層的收藏與日常起居。如作品《熱爾桑的畫店》中,為彰顯熱爾桑收藏,讓·安東尼·華多詳細地繪製了畫店內部日常。諸多名畫高低懸掛於牆面,一幅畫作遂成為了傑作總和。元素眾多、野心勃勃,極繁主義在此亦表現得淋漓盡致。

讓·安東尼·華多(Jean-Antoine Watteau)《熱爾桑的畫店》(The Signboard of Gersaint),182×306cm,布面油畫,1720年
談及極繁,《Kult》雜誌主編Steve Lawle曾說:“我十分欣賞那些凌亂卻又飽含張力的極繁主義藝術家,因為這些特質很難被模仿。”正因其充滿感性以及難以模仿的特質,極繁主義逐漸滲入各領域。
風靡時尚
時尚是一個充滿極端的世界。2019年,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慈善舞會(Met Gala)“坎普:時尚筆記”中(Camp: Notes on Fashion),極繁主義在Katy Perry、Cardi B等人的造型中可見一斑。正如美國作家、哲學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對坎普的諸多概括所言,“建立在某種東西‘太多’的內在感覺之上”“一個女人穿著一條有三百萬支羽毛的裙子”。華麗與野性充斥在這場上東區的宴會中。
極繁主義可被理解為坎普的一種現代性解讀:華麗、繁冗、誇張——且看川久保玲(Comme des Garçons)同樣以坎普為靈感的作品。模特們在秀場上身著華麗、印花豐富的衣服蝸牛般蹣跚而行,哪怕行走時如一座座移動的雕塑,人們仍甘之如飴地回味著其中充滿戲劇性的美感。
極繁主義亦勾起了人們對“奢華”本源般的慾望,這種專享權原屬於奢靡皇室與貴族的美學被接受、熱愛再推崇。因此,極繁主義在時尚界也漸有壓倒極簡之勢。設計師亞力山卓·米開理(Alessandro Michele)執掌古馳(Gucci)後,便顛覆品牌陳舊樣貌,將奢靡、復古、隨性等風格語言注入其中。而後,古馳甚至推出了家居系列(Gucci Décor),極繁主義也透過該品牌走入室內設計領域。
此外,Louis Vuitton在今年也回顧了洛可可藝術,其秀場選址盧浮宮黎塞留長廊(Passage Richelieu),寬大的裙撐回應著數百年前的時尚,古典且雍容華貴……這無不昭示著極繁主義在時尚界開始引領風潮,成為業內風向標。
繁簡之爭
八大山人作品,紙本水墨,明末清初
其實任何風格歷久彌新都是難事,且在大肆風行後難免落得“審美疲勞”的評價,此時也正是新興思潮“破土”的一刻。長久以來,風格更替,大抵皆如此。極繁主義與極簡主義便如同一朵雙生花:一面是繁複絢麗的凌亂生命力;一面是返璞歸真的強大力量。二者在設計領域一直此消彼長、搖擺不定。
極繁主義與極簡主義的“較量”並非一時興起。中國畫就善以“留白”來協調畫面、摒棄冗餘,洗練的筆法描山繪水,方寸畫布顯天地宏寬。八大山人尊崇“惜墨如金”的倪瓚,他便曾在畫冊上提贊曰:“倪迂(倪瓚)作畫,如天駿騰空,白雲出岫,無半點塵俗氣,餘以暇日寫此。”
而縱覽古今,極繁主義早在歷史舞臺留下了璀璨一筆。北宋張擇端繪製的《清明上河圖》便採用散點透視構圖法,事無鉅細地記錄了汴河兩岸市井風光。如此繁多的內容,在歷代古畫中屬罕見。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區域性,絹本設色,24.8×528cm,北宋
再者,乾隆時期一改雍正的“極簡”審美,轉而偏愛華麗精美之風格。曾在《國家寶藏》中一展風華的各種釉彩大瓶便是“極繁主義”的代表。該瓶瓶身集十多種高低溫釉、彩於一身,工藝之複雜、風格之獨特令其彌足珍貴。因此,各種釉彩大瓶也被稱為“瓷母”。
不僅極繁、極簡在古代藝術領域迴圈交替,由東及西,建築界也有類似之爭。人們熟知的“Less is more”(少即是多)便是出自德國建築師密斯·凡·德·羅。此理念可類比極簡主義,是以古典式的平衡和極端簡潔為美學宗旨,欲將建築物剝離至只餘筋與骨的建築哲學。這三個詞如同三個嚴厲的音節,指導了現代主義運動,亦深刻影響了一代建築師。


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設計的範斯沃斯住宅
而被譽為“後現代主義之父”的羅伯特·文丘裡則在上世紀60年代提出了“Less is a bore”(少即是無聊),旋即成為這一代建築運動的口號。在該理念引領下的城市風格景觀比20世紀現代主義的“嚴肅紀念碑”更為幽默與謙遜。正如文丘裡所言:“我喜歡混合元素而非純粹、妥協而非清晰、扭曲而非直截了當的元素。我贊成凌亂的活力,而不是明顯的統一。”

羅伯特·文丘裡(Robert Venturi)設計的休斯頓兒童博物館(Children's Museum of Houston),1992年
雖然“Less is more”和“Less is a bore”不能完全與極繁、極簡劃等號,但如今利用“Less is a bore”來撼動現代主義與極簡主義已成風潮。2019年,波士頓當代藝術美術館(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Boston)便舉辦了展覽“少即是無聊:極繁藝術與設計”(Less is a bore: Maximalist Art & Design)。

Joyce Kozloff《If I am a Astronomer: Boston》,混合媒介,94×139.7cm,2015年,於展覽“少即是無聊:極繁藝術與設計”上,2019年
借文丘裡之言,多元文化與風格彙集該舞臺,這也恰好證明了極繁如一簇對理性進行反叛的野生能量已然嵌入至時代靈魂之中。人們的視覺再難被單調、冷淡的事物所吸引,每一根毛孔都渴望著刺激——這是時代的寫照,只因追求之物有如一面鏡子映襯著人們的內心。

Virgil Marti的裝置,於展覽“少即是無聊:極繁藝術與設計”上,2019年
然而,極繁主義的哲學也是樂觀的:它是眾多風格的混雜,更是一種入世的態度。或許這種美學正有著李白“人生得意須盡歡”般的豪邁在內。因此,欣賞它往往如同步入一場充滿生命力的藝術盛宴,如聲般高亢激昂,如意般縱情歡樂。於是,在這種充滿感性的浪潮中亦有生生不息的力量蔓延開來。你偏愛極繁還是極簡?歡迎留言分享看法。
本文由《時尚芭莎》藝術部原創,未經許可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