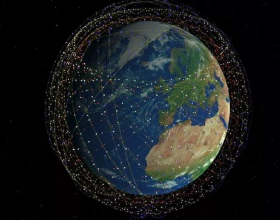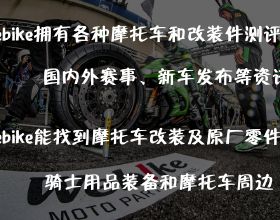魏晉風度,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範。當時士人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風流的人生觀與審美觀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留下了一道瑰麗的人文景觀。
01
魏晉風度與人物品鑑
魏晉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獨特時期,其時上接東漢,下開六朝。魏晉風度,是指發生在這一時期中的文化現象,風度是指人物言行所表現出來的儀表風範和態度,魏晉是歷史階段,歷史階段不可能具有儀表風範,因此,魏晉風度實際上是指魏晉時期的人物所表現出來的風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風度,只有當時名士不同於流俗的言行才能稱為風度。魏晉風度,其實是指魏晉名士的言行表現出來的風度。
魏晉名士,為大家所熟悉的如“竹林七賢”,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嵇康、阮籍。他們表現出來的風度,與世俗不同,如阮籍的青白眼故事、嵇康鍛鐵不理睬鍾會的故事等,廣為人們所樂道。後世的人因將魏晉時期的名士按照時代先後分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江左名士。其實,竹林名士和正始名士活動的時間差不多同時,都是正始年間事。但正始之音主要是指王弼、何晏所建立的玄學理論。
竹林名士給後人的影響,主要是指他們的活動。雖然嵇、阮都是著名的玄學理論家,也是著名的文學家,但後人所理解的竹林之遊,還是指他們與山濤、王戎、向秀、劉伶、阮咸等人的活動。後人景仰魏晉名士的言行,緬懷而稱之為魏晉風度。後人最為景仰的,還是魏晉名士超出凡俗的曠達、放逸、不以俗物縈懷的言行,從這一點說,東晉名士最能體現也最能代表這種風度。
與前代名士相比,江左名士在玄學理論上沒有什麼建樹,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表現出的玄學態度,形成了令後人景仰的名士風範。唐代大詩人杜牧說:“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東晉名士的風流就在於他們處理人與外物關係的兩相得態度上,以及在兩相得狀態中表露出的真情性。
後人每論晉人具有令人著迷的煙水雲氣,其實也主要指東晉名士。因此,風度,其實是名士們言行的自然流露,是真名士自風流,如果是假名士,當然就談不上風度和風流了。魏晉名士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他們的風流的身影,當然,這種風流,在他們本人來說,並不都是很愉快的事。比如大家都傳嵇康臨終前就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何等地風流,但那卻是嵇康被殺之前的事,於嵇康卻是十足的悲劇。但嵇康能夠面臨死亡,不嘆自己生命將逝,而嘆《廣陵散》從此絕世,這便是與俗人不同的名士風度了。
當然,魏晉名士的風度,大多表現得風流瀟灑,但也有許多是在死亡面前以及悲憤的心態下體現出來的,如東晉名士王濛,生病將逝,臨死前在燈下轉麈尾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那是怎樣的一種傷感,又是怎樣的一種對生命的留戀。他面對死亡,當然也是無奈,也是悲傷,但他沒有陷於不可自拔的痛苦,而是就其談玄常用的麈尾發出這樣的感嘆,這樣對生命的悲感,便具有了深情和哲理,其感人之深,是後世人所不具有的。
再如阮籍,他有許多令人景仰的故事,也都具有感人的風度,但他內心的悲憤、無奈、憂傷,卻是這些表面上看狂狷不羈行為的出發點。史書記他常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這是多麼深的悲憤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方式啊!
因此,我們要深入地瞭解魏晉人的風度,就要深入地瞭解那個時代,那些人具有怎樣的思想、怎樣的生活。魏晉是一個時間概念,事實上,據最集中記載魏晉名士言行的《世說新語》,這一時代名士們的活動,是從東漢末年就開始了。而時人對這些名士們也都充滿了景仰,因而在民間流傳著很多有關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不僅在雜史中有記載,就如《後漢書》《晉書》這些正史中也都有記載。
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都很關注自己的言行,一舉一動,都特別具有不同的意味。當然,名士並非不分等次的,因此東漢以來,有關這些名士的表現,便有許多評議。東漢時的人物清議,有許多涉及這方面的內容。他們對這些名士的風度,進行不同的品評,總起來多以“風”字品評,如風格、風度、風貌、風氣、風標、風神、風韻等等,這些以“風”為基本概念的品評術語,都有具體的不同含義,高下之分是不一樣的。
風,本指空氣流動所造成的現象,風動有力,故可以撼物,故人因之以此自然現象觀察社會,故上之教化亦可以用風,稱為風化。風化,《詩序》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曰風。”此論風化教育,能夠風化,起到上下溝通的作用,這個作用便以“風”來形容。“風”亦可用在人身上,人稟自然之氣,形成不同個性,因而有不同氣度、表現,有與“風”相通的地方,段注《說文》便解釋這個風說:“故凡無形而致者皆曰風”。風在人體之內,其為無形,但卻可以表現為不同氣度,不同的狀態,這就是最基本的“風”。但每個人的稟性不同,修養不同,格局不同,因而表現出的狀態也不一樣,於是便以“風”為基本詞,而根據不同的表現,再賦以不同的狀詞,於是便出現了一大批以“風”冠名的品題詞語。如:風操、風止、風格、風貌、風儀、風采、風情、風鑑、風流、風骨、風尚、風姿、風望、風味、風力、風美、風軌、風範、風穎、風德、風期、風氣、風韻、風色、風志、風表、風度、風容、風烈、風猷、風裁、風趣、風懷、風觀等等。
這麼多的品目,並非不可區分,大致可以看出這不同的品題,有的指人物的外貌,有的指人物的精神,有的指氣象,有的指神韻。比如風止指人物的風儀態度,風色指風神顏色,風尚指風姿儀態,風味喻人品高雅,風采指文采風姿,風流則指放逸灑脫,風軌猶言風操、風範、風格,指人物的方正,風神則指人物的風采精神,風骨指人物的高奇有氣,風氣指人的風度與氣概,風雅指人物的風流儒雅,如此等等。
最早把風與人聯絡起來的,始於孟子。《孟子·萬章》說:“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當然這裡的“風”與東漢以後的“風”不同。孟子強調的是伯夷的行事所具有的教化作用,重在事上,後世的風則作為一種抽象的品題術語,是對人物內在與外表以及他對別人造成印象的總體概括。“風”的評語有高低,但能得到“風”的品目,首先都須是名士,如魏晉人物裴秀、裴楷、王衍、樂廣、王戎、嵇康、何晏、謝安、王羲之等等。
《世說新語·品藻》記:“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嶠也是東晉名士,但當時的品評僅置於第二流中,然其心頗為在意,故對未能入第一流耿耿於懷。《晉書》記溫嶠“風儀秀整,美於談論”,可見其風儀不一般。《世說新語·任誕》“溫太真位未高時”條引《中興書目》曰:“嶠有俊朗之目,而不拘細行。”能得俊朗之目,自非一般名士。《世說新語》又記王敦欲廢明帝,時人不敢忤敦,唯溫嶠不屈,可見其風骨,但這樣的人在東晉名士中只列為第二流。
02
玄學薰染下的名士風流
東漢應該是“名士風流”發端的時期,主要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士人砥礪名節,以與汙濁的現實生活對抗。魏晉以降,人物品評因玄學思潮的影響,漸由就人物在社會現實中的態度之評,轉為對人物的內在精神、氣質等的品評了,因此產生的評語便多種多樣。如嵇康,自是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時人稱其“風姿特秀”,據《世說新語》引《嵇康別傳》說:“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晉書》本傳則記為:“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風姿”一詞主要形容人物的外形,然謂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則是論其內在精神了。
再如王羲之,《世說新語·賞譽》說:“殷中軍道,右軍清鑑貴要。”注引《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又注引《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王羲之是東晉名士的代表人物,所謂高爽有風氣、風骨清舉,皆謂其人與世俗人不同,故當時有人說他“飄如遊雲,矯若驚龍”(《世說新語·容止》),《晉書》則說是時人論其勢,蓋書如其人,書亦是人品的體現,此八字合王羲之其人,亦合其書。
魏晉名士以其超然物外的言行,在中國歷史上建立了獨一無二的風度,這種風度的形成,其實也有一個發展的歷程,也是與魏晉間的思想發展相適應的。東漢時期的名士品格,多與社會現實有關,東漢名士以砥礪名節樹立了名士風範,魏晉以降,則隨著玄學的發生發展,魏晉名士往往討論更多的是與玄學相關的玄理,因此,魏晉名士風度,往往與玄談有關。魏晉初期的人物品評,往往與人物的外貌相結合,所以這個時候的對外貌俊朗的人物,好評甚多。
大家熟悉的故事如曹操因為對自己的外貌沒有信心,於是便在見匈奴使者時,請崔琰來扮充自己,自己則扮捉刀的人。當然,這故事的可信性有待質疑,但的確反映了時代的風氣。比如王粲,亦其貌不揚,就受到劉表的輕視。何晏是美男子,他為了更顯美麗,專門在夏天的時候吃熱湯餅,大汗出,然後再用紅衣拭汗,於是“色轉皎然”。再如潘岳,姿容甚美,常與另一美男子夏侯湛並出,時人謂之連璧。但到西晉以後,對人物賞評,已不僅止於外貌,還有人物的內在精神和氣度。因此,我們看魏晉早期的評語,多是風貌、風格、風姿等,至於後期,除了這些外貌的評語外,如風神、風氣、風骨、風韻等等評語,用得就比較多了。這也反映出魏晉名士風流的逐漸成熟,人物的外在與內在並重,因此,魏晉風度最迷人的,應是東晉時期,由東晉名士表現出的曠達自然、物我合一的境界。
03
不同流俗的魏晉名士
魏晉風度,就是指魏晉名士的言行所表現的風範和態度,這種表現是不同流俗的,所以具有恆久的感染人的力量。我曾在《魏晉風度》一書中將魏晉名士的風度概括為五個方面:一、處驚不變,鎮靜自若;二、曠達傲世,任率自然;三、風神瀟灑,不滯於物;四、超入玄心,表裡澄澈;五、一往深情,天然風流。
第一種,處驚不變、鎮靜自若。如謝安,《世說新語》記:“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如此鎮定,故是非凡之量。
第二種,曠達傲世、任率自然,反映晉人崇尚任率自然。著名的如王羲之東床坦腹,是後人樂於傳誦的故事。而王徽之雪夜訪戴,亦讓人認識到晉人的“乘興”和“盡興”,是何等地灑脫自然!
第三種,風神瀟灑、不滯於物,可以看出晉人對“神”的看重。這已經從東漢末以來,由注重人物外貌發展為注重內在精神了。但得此品題的,多是大名士,如東晉的謝安等人。謝安是東晉名士領袖,時人譽為“弘雅有氣,風神調暢”,被稱為風流名相,其流風餘韻所及,即成風氣。又如周顗,別人說他“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東晉著名的和尚支遁長相很醜,但他以淵博的知識、瀟灑的風神在東晉士林中擁有極高的聲譽,當時稱他為“支公”,王羲之更品他是“器朗神俊”。有趣的是,支遁不僅自己神俊,於生活中也欣賞有神俊的事物。他喜歡馬,也養了幾匹。有人說和尚養馬不風雅,支遁說:“我是看重馬具有的神俊。”從馬的身上體會其抖擻的精神,這是支遁養馬的原因。
第四種,超入玄心、表裡澄澈,則反映了晉人內心的明靜,這明靜卻是與其具有玄心相關的。魏晉名士基於對玄學的深入體會,對世界、人生都能自覺地以哲學,尤其是美學觀去審視,這就是他們超入玄心,而表現出一片晶瑩剔透的精神世界的根本原因。魏晉名土本著玄心的體會,充滿美感地審視這世界,他們內心澄澈,也追求著同樣澄澈的外物。
王胡之到吳興印渚觀看後,嘆道:“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對“日月清朗”的太白世界的欣賞,正是東晉人內心澄澈的外化。他們喜愛這世界,擁有這世界,與這世界融為一體,建立了一個空靈的藝術世界。人與大自然,本身就是最高的藝術!這裡,自然不再是孤立無情的純客觀,它與人相通,相通點就是玄心。因此,東晉人不獨自己珍惜、欣賞這種境界,而且往往因此而思念友人,如王徽之在皎潔的大雪之夜思念戴逵即是。另一名士劉惔則這樣說道:“清風朗月,輒思玄度。”玄度是許詢,當時被公認為有高情遠致的人。劉惔在清風朗月之時自然地想起了許詢,說明二者之間有相通的地方,這就是清風朗月澄明的世界與許詢玄遠的心懷相同相通。
東晉名士賞物所使用的名言雋語,更具有詩一樣的情韻。如顧愷之稱會稽的山川之美是“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又如王獻之形容山陰道上的風景說:“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壞(懷)。”王獻之另有《雜帖),對會稽山水的描寫更為詳備,他說:“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東晉名士將清談玄理的語言一轉而用於文學語言,這對於中國山水文學的發展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像這種清疏簡麗的描寫,以及語言的富於音樂性,以前的文學界是沒有過的。
東晉名士依據於玄心,對山水自然風光便有獨到的體會,又能用雋永的語言把這種體會準確地表達出來。山水美的鑑賞本身也就是人物美的表露,從東晉名士這種清泠如詩的語言裡,我們正可窺見他們那藝術心靈。東晉詩人郭璞有兩句詩特別為名士們所欣賞:“林無靜樹,川無停留。”阮孚說它的好處是“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郭璞的詩具有深遠的哲學意味,只有懷有玄心的人才能體會得出,而感到神超形越。超然物外,正是藝術的美感所在。
第五種,一往深情、天然風流,反映了魏晉名士特有的風度,與他們具有深情緊密相關。這種一往深情,帶有感動人的藝術美感。如《世說新語·言語》記桓溫北伐,見其當年手植柳條已長成大樹,不禁攀枝掉淚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這一嘆息所具有的藝術感染力是超過建安諸子所寫的《柳賦》的。東晉名士對情的表達,更富於個性和人情味。《世說新語》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桓子野(伊)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所謂清歌,恐怕就是魏晉時期流行的清商曲,曲調以其清越哀傷特別能打動人,也特別受文人的喜愛,這也就是桓伊每聽之後,輒喚奈何的原因。謝安認為一首歌就能讓桓伊那麼感動,可見他是一往深情的人。
魏晉名士是深於情的人,他們非常珍惜人世間的情誼,親朋好友的每一次分離,都給他們帶來哀傷,並且為之難過好幾天。謝安告訴王羲之說:“人到中年以後,特別傷於哀樂。每次與親友分別,總要難過好幾天。”王羲之安慰他說:“到了晚年,自然會如此,所以靠絲絃竹管來陶冶性情。但總怕兒孫輩察覺,有損這種歡樂的趣味。”王羲之勸謝安以絲竹陶冶自己,因為他也是具有深情的人,深知“情”對人的折磨。謝安晚年的不廢妓樂,其原因正在於此。觀謝安與王羲之的對話,這樣自然、親切,相互間的理解、體貼又是這樣地令人感動,其思想基礎正在於同具深情。
東晉人重情、傷情,不僅是生離與死別,國家的前途,個人的遭遇,都是觸發點。袁宏做安南將軍謝奉的司馬,京都人送他至瀨鄉,分別之際,不覺悽惘,袁宏嘆道:“江山寥落,居然有萬里之勢。”這是對東晉偏安江左一隅的感慨,既有對國家的擔憂,也寓個人的辛酸,出語雖名雋,卻充滿了感傷,令人泣下。著名的新亭對泣,也正是在同樣的山水之中湧起山河破碎的感傷情緒,這是時代造就的敏感的心靈,他們就以這樣的心靈去看待自己和自己周圍的世界。
殷仲文曾為桓玄左衛將軍,很得桓玄器重,桓玄失敗後,殷仲文又投向朝廷,但意懷怏怏。他所在的大司馬府前廳有一株老槐樹,枝葉扶疏,殷仲文一次注視良久,長嘆一聲:“槐樹婆娑,無復生意!”嘆老槐了無生意,固由於他仕途不遇的怏怏不樂所致,但他居然能於扶疏的老槐上體味出人生的失意,還在於他有這樣一顆敏感的藝術心靈。因此東晉名士的重情實與西晉人不同,區別就在於此。東晉人士所表達的人情富於人格之美、人情之美,濃郁而有致。他們的每一個舉動,每一句言語,都是一種成熟的藝術的表現。
因此,東晉人深於情,同時又超於情,他們表現得那般如醉如痴,深摯而執著,但從不拘泥而不可自拔。王濛面臨死亡,不直嘆自己生命的結束,卻在燈下留戀地把玩伴隨自己一生的麈尾:生命將逝,麈尾長存,此一番永別是多麼地令人傷心啊!這裡顯示了怎樣一種偉大的人格力量!馮友蘭先生在《論風流》一文中對東晉人的深情有非常精闢而優美的分析,他說:“真正風流底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雖有情而無我,所以其情都是對於宇宙人生底情感。”以此視魏晉名士,確是真正的風流人物,長令後人緬懷不已!
◎本文原載於《解放日報》(作者傅剛),圖源網路,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