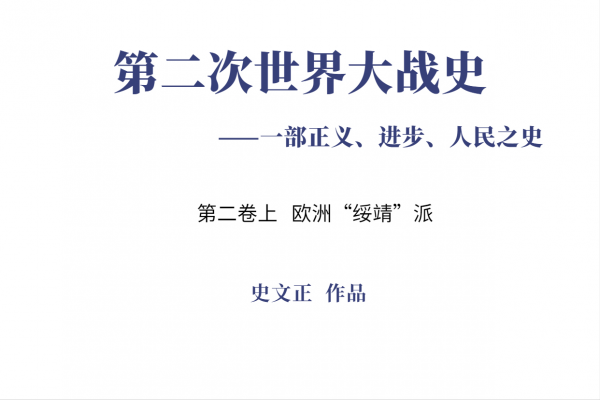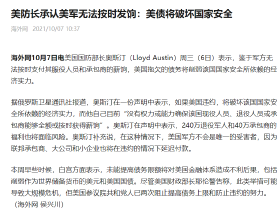第八章“綏靖”政策的新動向
上面我們介紹了德國在“綏靖”派的縱容默許下對奧地利的吞併,其實這一吞併是在更大的背景下進行的,那就是進入1937年以來,法西斯在發生變化的同時,“綏靖”派也在發生變化,兩者是殊途同歸:前者更具有進攻性,後者更具有防禦性——極力維護現狀,拼命地抓住現狀不放。而“綏靖”派這一變化的標誌性事件就是1937年5月英國張伯倫上臺。這個“綏靖”派的“激進分子”走上執政舞臺,預示著“綏靖”政策將出現新動向,將迎來它的巔峰時刻。下面我們有必要回過頭來把這段歷史交代清楚,以為下面的慕尼黑勾結做一鋪墊。
第一節 張伯倫上臺
張伯倫這個徹頭徹尾的“綏靖”分子在其上臺之前就極力鼓吹“綏靖”主義,堅決反對英國擴軍備戰,認為這是“多此一舉”“只會引起恐慌的”。張伯倫宣稱:“我不認為戰爭迫在眉睫,我相信,運用小心謹慎的外交活動可以防止戰爭,也許可以無限期的防止。”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應該同德國在談判桌上坐下來,透過談判達成和解,締結區域性協定,“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確定一個‘綏靖’政策的總計劃”。看來大英帝國選擇張伯倫來推行“綏靖”政策,是再合適不過了。
上臺後,他一改前任“被動”地追求“綏靖”政策的行動方針,不但要在實際行動中追求“綏靖”政策,更要把它上升到國家指導思想的高度,積極、全面、徹底地追求“綏靖”政策。在張伯倫的整個“綏靖”戰略中,關鍵是實現與德意兩個法西斯國家特別是德國的全面“和解合作”,實現歐洲政治和經濟問題的“總解決”。至於使用武力,張伯倫的態度是一以貫之的:那是根本不在考慮範圍內的。甚至連談論武力都不允許,“對這種談論要加以強烈反對,這種談論不但不能有好處,而且肯定會有害;因為那樣勢必干擾外交活動的進行,勢必助長不安全、不穩定的情緒”。
讓一切在“和平寧靜”的氛圍中度過,決不允許破壞這一氛圍,這就是張伯倫式的和平理念的核心所在,這一理念是那個絕對主義和平觀的具體化。為了悉心呵護這一“和平寧靜”的氛圍,積極滿足侵略者的慾望是必須的。希特勒可以“統一德意志民族”,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蘇臺德地區等有德意志民族的地方,希特勒都可以“統一”,只要他承諾以“和平演變的方式”進行,不進一步提出新的領土要求,同意簽訂保障西歐安全的互不侵犯條約即可,是的,一個“承諾”即可。
張伯倫這個大英帝國的“紈絝子弟”自信“對歐洲整個局勢,甚至對整個世界都瞭如指掌”,急切地想在國際舞臺上一顯身手,實現其“綏靖”大業。上臺伊始他熱切地邀請德國外長紐萊特訪英,以全面討論兩國間存在各種“分歧”,不過“遺憾”的是,沒有得到希特勒的回應。張伯倫越急切,我們的納粹元首就越鎮定自若,他很輕鬆地就抓住了這個“紈絝子弟”的軟肋。
等到1937年10月,張伯倫總算是獲得了向納粹元首表明心跡的機會:哈利法克斯受戈林邀請對柏林“非正式訪問”。張伯倫對這次訪問是受寵若驚,不過外交大臣艾登卻表示疑慮,他覺得以這樣的心態去訪問不會取得好結果,儘管最後勉強同意了這一訪問,但同時告誡哈利法克斯不要提及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問題。
然而,這位張伯倫的“綏靖船上的大副”一踏上納粹德國的土地就將艾登的告誡拋之腦後,將張伯倫的底牌和盤托出。但是我們的納粹領導人並沒有“笑納”,更沒有被哈利法克斯伯爵的“誠心”所感動,而是步步緊逼,一定要從大英帝國的身上“榨取”更多的東西。戈林宣稱,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但澤問題能否“和平”解決,不取決於德國,而取決於英國,德國是希望和平的,也希望英國能為這一“和平”作出貢獻。而希特勒則大談德國的“平等權利”和《凡爾賽和約》的“屈辱”,儘管法西斯的“平等權利”早已高於其他國家,《凡爾賽和約》的束縛早已被打破。而哈利法克斯伯爵依然決定用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但澤這些犧牲品撫慰《凡爾賽和約》的“屈辱者”心中的“不平”。
事實清楚地表明,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但澤問題已經不是此次會談的中心問題,法西斯德國進一步把它“進攻的戰線”推進到了殖民地問題。伯爵說這個問題並非不可以討論,但只能作為“全盤解決”一個組成部分看待,以獲致歐洲的和平和安全。看來希特勒的“進攻態勢”只能暫時維持到這裡,而哈利法克斯關於英德兩國進一步談判的一再要求當然也不會得到滿足。
儘管英國的要求沒有被滿足,張伯倫對這次訪問是滿意的,因為他的心跡總算得以表白。我想希特勒也是滿意的,他可以十分肯定地確認向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擴張是毫無風險的。
哈利法克斯訪德清楚地向我們展現了這樣一種景象:有理者是如何掉到了無理者的地位,而無理者是如何站在了有理者的地位上,這可以算得上是慕尼黑勾結的一次預演。
第二節 法國的“曲折”
儘管英國的“綏靖”行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它的同伴法國就沒有這麼“順利”了,出現了一些波瀾。德國入侵奧地利的前一天,懦弱無能的肖當政府沒有向國民議會要求舉行信任投票就主動辭職,大概是不願面對或承擔奧地利危機的責任,於是人民陣線政府又迎來了它的老主人社會黨領袖勃魯姆。
勃魯姆,這位開創人民陣線執政事業但並未把它引向成功的人物,時隔不到一年又回到了執政舞臺。看來第三共和國還不想就此沉淪,還想再掙扎一下,而勃魯姆這個人民陣線振興的招牌還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來改變法國的命運,同時面對再次執政,新的勃魯姆政府也不想不負眾望,而要再次雄心勃勃一把。在上一任期,在國內外各派反動勢力的打壓下,勃魯姆政府在無所事事中結束了自己,此次執政它決心吸取這一教訓,要表現出堅決的態度,奮力把自己的政策推行下去。
在對外政策上,勃魯姆政府準備採取對德意法西斯的強硬政策,繼續援助此時已岌岌可危的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打擊佛朗哥叛軍;它重申對捷克斯洛伐克——此時德國法西斯已經開始染指這個中歐國家——的保證義務,警告德國法西斯不要輕舉妄動。當然,勃魯姆政府的強硬政策是需要軍事實力支撐的,幾個公開宣告是不可能鎮住法西斯的,而它的軟肋正在如此。
法國政府儘管左翼了,恢復了生機,它的軍隊乃至整個社會卻依然在右翼保守勢力的掌控中。當勃魯姆總理和他的外交部長將政府的強硬政策和盤托出時,很快就碰上了來自軍事領導人的一個又一個釘子。軍事領導人們千方百計地向總理“證明”法軍的實力不支援這一強硬政策,如果硬要行動,困難重重,風險太大,前途殊難預料;至於蘇聯和英國的援助,那是不可靠的,讓法國單獨面對強大的法西斯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最好”的選擇是不行動,讓一切在“和平安寧”中度過,在渾渾噩噩中度過。
於是,3月15日的國防會議也在一片悲觀陰鬱的氛圍中度過。會議的唯一成果就是,總理和他的外交部長知道了他們在行動上受到了種種限制,既不能干涉西班牙內戰,也不能使捷克斯洛伐克免遭法西斯的蹂躪,一切都沒有行動的可能性。
在對內政策上,勃魯姆政府繼續其上一任期旨在改善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行動。4月6日,勃魯姆政府向國民議會眾議院正式提出了它的財經改革提案。這個被稱為“自彭加勒以來法國第一次執行的一項大膽而全面的財經復興計劃”,其核心依然是限制資本權力,控制外匯,限制資金外流,增加國內信貸,確保資金用於生產性專案,改善國家財政狀況,重振法國經濟。增加軍費,擴大軍火生產,也被第一次提上了議事日程,其實這是整個財經復興計劃的主導性因素,擴大軍火生產既被視為應對法西斯威脅的措施,也是重振法國經濟的“火車頭”——以擴大軍火生產來刺激整個工業生產。
我們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不愧為一個只講利不講義、只講私不講公的制度,它豈會讓這樣一個具有強烈反“綏靖”色彩、積極追求進步的提案獲得透過。提案在左翼的眾議院以311票對250票通過後,在右翼的參議院遭遇重大挫折。參議院再次著眼於“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直接把目標對準提案人——以214票對47票的絕對多數推翻了勃魯姆政府。上臺不到一個月的勃魯姆新政府就這樣被輕輕鬆鬆地結束了,它似乎有了一些膽識,有了一些勇敢,但依然缺乏或者沒有積極加厚支撐這一膽識和勇敢的根基——人民的力量。伴隨著勃魯姆新政府被推翻而來的也是人民陣線的徹底壽終正寢,看來此次勃魯姆執政與其說是第三共和國的一次振興行動,不如說是它的迴光返照。
愛德華·達拉第,這個曾經率領激進社會黨參加人民陣線並予以積極支援的人,繼勃魯姆之後出任總理。新政府獲得了眾議院514票對8票、參議院290票對0票的絕對多數的信任投票,並獲得了參議院暫時進行法治——實質可以進行獨裁統治——的授權,儘管這一權力參議院一直拒絕授予勃魯姆政府。新政府之所以獲得如此空前的支援,表面上是因為它暫時還打著人民陣線的旗號而實質上是反對這一旗號的,因而獲得了左右翼全部力量的支援,但究其實質是法蘭西帝國終於擺脫了人民陣線的“陰影”,再次回到了“綏靖”的道路上,可以放心大膽地推行“綏靖”政策了。從此以後,達拉第攜其外交部長喬治·博內步張伯倫之後塵,在法國全力以赴地推行“綏靖”政策,而張伯倫也終於在法國覓得了自己的知音,至此通向慕尼黑勾結大門被徹底開啟。